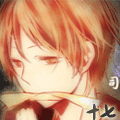—
本帖被 逆° 从 原创小说 移动到本区(2016-03-31)
—
那年,喜轿抬着她缓缓驶出府邸,他拂袖转身不语一言,只是痴愣着望着九曲回肠的亭廊。
礼堂中,她凤冠霞帔,他看不见那张眷恋已久的芙容,只窥得火红盖头下微敛的纤巧下颚。
良久,他茫然垂首,看向指尖错杂的针孔,余光又是不觉掠过那抹刺目的红影,终只得苦笑着一手纳入怀中,攥紧枚藏青色锦囊,暗自低咐:明知恋上终是一世无果,我终究却是恋上了。为你缝制嫁衣,却终为他人作嫁,我甘乱了浮生,却终仍不舍你随我浮沉。罢了。这一世剪不断的至亲血缘。这妄恋,你不知也罢。
那晚,他紧攥着左手,血丝在掌心绽开,没入衣袖之间,而他恍若不觉,只是醉笑着豪饮,任黄酒穿肠。
那一夜,他赤红着双目望着一室的艳红,直至天边泛起白光。
次日,他归家,却是在府中待了不足半月,便又借拜师学艺之名离开。
时日如梭,第五个霜白枝头之时,他终是抱着还在襁褓中啼哭婴孩归来,一袭青白色儒衫衣袂飘飘。
归家不及十日,他便接手了老父掌管的布庄。已将入而立之年的他却是不顾爹娘苦叹哀怨,推却了一门门亲事,整日仿若只晓布庄与那个婴孩。
然恍若只是转瞬,他却已是耳顺之年,爹娘也早已相继仙逝。
冬去春回,花开花谢。布庄在他的接管下早已是闻名遐迩。而这些年来,却依旧不曾见他勾手身旁蝶舞莺飞。
府邸越渐锦华,而主屋斑白的墙头却始终如一,只挂着幅寥寥几笔的画像,画中只依稀见得一女子纤弱的背影。
从无人知晓画中那人是谁,只是府中仆从时常见得温文尔雅的老爷痴望着那画中人,落寞含笑。
堂前燕去,雪落霜白,他研墨欲书,这前尘往事中她的一颦一笑依旧清晰可辨,然这其间时隔多年,他却从未曾见过她。
直至她西归前朝,他才得以到她病榻前。看着那张刻满风霜的脸,再不复记忆里的明艳,却仍有那双眼温润如昔。
他张口轻唤一声:“姐。”此时已是无人应答。
他又看了看病榻中安睡的那人,垂眼间心唤着:青沫,我爱你。却终无人得以听见。
再抬头,她已阖上了那双温润如昔的眼。蓦然,他一滴泪落入床间,了结这生终不成器的痴恋。
隔日,他安睡于被衾之间再没醒来。待仆从发现之时,他手垂搭身侧,手中却尤是攥着一枚近乎看不出成色的锦囊。
仆从慌乱中传报了府中少爷,那个他当年抱回的婴孩,已成丰神俊朗的翩翩男子。
男子看着只若安睡的他,低唤了声:“爹。”再没有人应答,再没有人轻拍着自己的头浅笑看向。
默然间,男子执起那枚锦囊拨开,已是有着些许破旧的锦囊中只有一角红色霞布。男子握着依旧火红的霞布,看了看双眼紧阖的他,侧头看向雕花的朱木窗外依旧清波微漾,亭廊九曲回肠,久久未言一语。
随侍在男子身旁的老仆瞥眉盯着那一角,苦思是曾何处见过,却终已无法忆得。
终是男子见他临终尤是握着这一角,便将霞布同他一并入了黄土。
世事苍茫,已无人记得那袭红衣,那角霞布。而这错恋,便是一辈子成痴。
这情字值得与否,或是只有他知道,却是一切随他终成了一抔黄土,无处辨得。
礼堂中,她凤冠霞帔,他看不见那张眷恋已久的芙容,只窥得火红盖头下微敛的纤巧下颚。
良久,他茫然垂首,看向指尖错杂的针孔,余光又是不觉掠过那抹刺目的红影,终只得苦笑着一手纳入怀中,攥紧枚藏青色锦囊,暗自低咐:明知恋上终是一世无果,我终究却是恋上了。为你缝制嫁衣,却终为他人作嫁,我甘乱了浮生,却终仍不舍你随我浮沉。罢了。这一世剪不断的至亲血缘。这妄恋,你不知也罢。
那晚,他紧攥着左手,血丝在掌心绽开,没入衣袖之间,而他恍若不觉,只是醉笑着豪饮,任黄酒穿肠。
那一夜,他赤红着双目望着一室的艳红,直至天边泛起白光。
次日,他归家,却是在府中待了不足半月,便又借拜师学艺之名离开。
时日如梭,第五个霜白枝头之时,他终是抱着还在襁褓中啼哭婴孩归来,一袭青白色儒衫衣袂飘飘。
归家不及十日,他便接手了老父掌管的布庄。已将入而立之年的他却是不顾爹娘苦叹哀怨,推却了一门门亲事,整日仿若只晓布庄与那个婴孩。
然恍若只是转瞬,他却已是耳顺之年,爹娘也早已相继仙逝。
冬去春回,花开花谢。布庄在他的接管下早已是闻名遐迩。而这些年来,却依旧不曾见他勾手身旁蝶舞莺飞。
府邸越渐锦华,而主屋斑白的墙头却始终如一,只挂着幅寥寥几笔的画像,画中只依稀见得一女子纤弱的背影。
从无人知晓画中那人是谁,只是府中仆从时常见得温文尔雅的老爷痴望着那画中人,落寞含笑。
堂前燕去,雪落霜白,他研墨欲书,这前尘往事中她的一颦一笑依旧清晰可辨,然这其间时隔多年,他却从未曾见过她。
直至她西归前朝,他才得以到她病榻前。看着那张刻满风霜的脸,再不复记忆里的明艳,却仍有那双眼温润如昔。
他张口轻唤一声:“姐。”此时已是无人应答。
他又看了看病榻中安睡的那人,垂眼间心唤着:青沫,我爱你。却终无人得以听见。
再抬头,她已阖上了那双温润如昔的眼。蓦然,他一滴泪落入床间,了结这生终不成器的痴恋。
隔日,他安睡于被衾之间再没醒来。待仆从发现之时,他手垂搭身侧,手中却尤是攥着一枚近乎看不出成色的锦囊。
仆从慌乱中传报了府中少爷,那个他当年抱回的婴孩,已成丰神俊朗的翩翩男子。
男子看着只若安睡的他,低唤了声:“爹。”再没有人应答,再没有人轻拍着自己的头浅笑看向。
默然间,男子执起那枚锦囊拨开,已是有着些许破旧的锦囊中只有一角红色霞布。男子握着依旧火红的霞布,看了看双眼紧阖的他,侧头看向雕花的朱木窗外依旧清波微漾,亭廊九曲回肠,久久未言一语。
随侍在男子身旁的老仆瞥眉盯着那一角,苦思是曾何处见过,却终已无法忆得。
终是男子见他临终尤是握着这一角,便将霞布同他一并入了黄土。
世事苍茫,已无人记得那袭红衣,那角霞布。而这错恋,便是一辈子成痴。
这情字值得与否,或是只有他知道,却是一切随他终成了一抔黄土,无处辨得。



 无果的爱恋却让人永生不得相忘!直
无果的爱恋却让人永生不得相忘!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