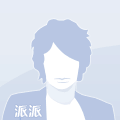【欧洲。罗马帝国 文化生活篇】罗马人的幸福生活
[size=2][color=#ff0000]罗马帝国专题
[url]http://m.paipai.fm/r5888251_u3331904/[/url]
【欧洲。教皇】罗马教皇——集权势与财富于一身
[url]http://m.paipai.fm/r5885858_u3331904/[/url]
【欧洲。罗马帝国 历史篇】见证一个腐败和黩武的文明
[url]http://m.paipai.fm/r5887630_u3331904/[/url]
【欧洲。罗马帝国 军事篇】罗马军团
[url]http://m.paipai.fm/r5885859_u3331904/[/url]
【欧洲。罗马帝国 文化生活篇】罗马人的幸福生活[/color][/size]
[table=80%][tr][td][color=#ff0000][size=2][b]罗马人的幸福生活[/b][/size][/color]
[size=2]货币单位[/size]
[size=2]食品供应[/size]
[size=2]供水[/size]
[size=2]排水[/size]
[size=2]厕所[/size]
[size=2]澡堂[/size]
[size=2]住宅[/size]
[size=2]街道[/size]
[size=2]饮食[/size]
[size=2]服饰[/size]
[size=2]儿童(学校教育)[/size]
[size=2]房 事[/size]
[size=2]赛车[/size]
[size=2]剧院[/size]
[size=2]大竞技场[/size]
[/td][td][color=#ff0000][size=2][b]1楼[/b][/size][/color]
[size=2]1。古罗马币介绍 补充[/size]
[size=2]2。古罗马的烹调宴饮[/size]
[size=2]3。罗马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size]
[size=2]4。罗马戏剧与剧场[/size]
[/td][/tr][tr][td][color=#ff0000][size=2][b]古罗马币介绍[/b][/size][/color][/td][td][color=#ff0000][size=2][b]2楼[/b][/size][/color]
[size=2]1。古罗马的文学艺术----诗歌[/size]
[size=2]2。古罗马帝国的行省管理[/size]
[/td][/tr][/table]
[color=#669900][table=90%][tr][td][size=2]
[b][size=3][color=#000000]罗马人的幸福生活[/color][/size][/b]
[color=#666666]本文翻译自
《The Ancient City - Life in Classical Athens & Rome》作者 Peter Connolly,Hazel Dodge
[ 转自铁血社区 [url]http://bbs.tiexue.net/[/url] ]
《Panorama of the Classical World》作者 Nigel Spivery,Michael Squire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Romans》作者 Harold Whetstone Johnston1[/color]
[color=#ff3366]1、罗马的货币单位[/color]
1奥里斯(aureus)= 25 第纳瑞斯(denarius)= 100 塞斯特瑞斯(sesterces)= 400 阿斯(as)= 1600 夸德伦斯(quadrans).
帝国时期城市内非技术个人的日工资约为1第纳瑞斯,在1世纪为3.8-4克的银币。庞培城出土的一份客栈帐单显示:升葡萄酒加面包-1阿斯其它食品-2阿斯 喂骡子的干草-2阿斯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0][/align]
大约在前6世纪罗马人就修建了城墙,但在前5世纪的某个时候,因为对外战争失败,罗马人被迫把城墙拆除。没了城墙的后果就是,390BC高卢人轻易地攻陷罗马,烧杀一空。高卢人撤走后,罗马人马上重建了塞维安墙(Servian Wall,下图中间那一圈城墙),塞维安墙长11公里,平均厚度3.6米,城门超过12个。
塞维安墙成功地挡住了汉尼拔,此后数百年,罗马的城区慢慢扩到城墙之外,但这时再无外敌能威胁到罗马城,所以一直没有修新城墙。到了3世纪,帝国开始衰落,北方蛮族的威胁日益严重,AD270皇帝奥勒良用三年时间修建了奥勒良墙(Aurelian Wall,上图外面的一圈),墙长20公里,有18个城门和381座塔楼。
就在奥勒良上台的前几年,罗马经历了一场大瘟疫,人口只剩下50万,所以奥勒良墙很可能无法体现出罗马城在鼎盛时期的规模。此后在戴克里先时代,人口又恢复到近百万,但总的来说罗马的地位和人口一直在下降,西罗马灭亡后,5世纪末的罗马大概只有5万居民,AD550剩下了2万5。罗马人在建城之初的几百年,显然没有想到子孙们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城的人口会超过一百万。因此在建设时毫无长远计划,只是简单地由中心向外扩展。到了帝国时期,皇帝们想要好好规划一番时,已经太迟了,市区里挤满了杂乱无章的建筑,要造个规模大点的皇宫都没地方。AD64的那次大火后,才烧出了大片空地,于是尼禄的皇宫,后来的大竞技场、大澡堂都陆续建了起来。不管大火是不是尼录放的,他为灾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私人金库里掏钱清理废墟,安置灾民。尼录还制定了各项法规,保证街道宽度和建筑的可靠性。不过在AD69 争夺罗马城的内战中,又窄又滑的街道给军团的前进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说明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善。到了3世纪末,罗马城共有11个大澡堂、超过1000个喷泉、两个赛车场、两个大竞技场、36座凯旋门和2000所豪宅。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1]
[color=#666666]拥挤的市中心汉化交流空间[/color][/align]
共和时期罗马城有4个区,7BC奥古斯都扩大到十四个区(Region),以罗马数字命名,区长由政府官员担任。每个区又分为更小的街区(vici),只有各街区的主路才有路名和路牌,不在主路上的居民只能自己想法标出房子的位置。例如:某某神龛东边的第五栋房子;某某面包店往下两个门。街区是罗马城最小的行政区划,有自己的神龛、祭坛、活动中心和标志建筑。每年街区内居民选出一到四位街道主任(magistri vici),负责治安、防火、祭祀本街区的守护神、与上级官员联络等 AD6奥古斯都用释放奴隶组成了7个消防大队(vigiles),每个大队负责两个区的巡夜和消防。为了提供这7000人的开销,奥古斯都加征了奴隶买卖税,征收奴隶价格的4%。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2][/align]
帝国后期的罗马城布局,右上角城墙边的是禁卫军营,
[color=#ff3366]2.食品供应 [/color]
由于罗马只统计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所以罗马城有多少人口从没有确切的数字。现代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在2世纪,罗马城人口大约为120万。在古代,供应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是巨大的挑战。罗马城消耗的物资,来自整个地中海区域,各种物资中运量最大的是食品。食品中又以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为主。谷物来自埃及和北非,葡萄酒从坎帕尼亚、高卢和西班牙进口,橄榄油主要来自南西班牙和北非。
帝国时期海运、河运和陆地运输的成本大约是1 : 5 : 30。在奥古斯都时期,埃及每年要向罗马输送1亿8千万公升小麦,1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则宣称阿非利加省的输送量是埃及的两倍,这样大的运输量只能依靠海运。葡萄酒和橄榄油装在双耳瓦罐(amphorae)内,先运到台伯河口,转到小型驳船上,沿台伯河运达罗马城内的河码头。所有的瓦罐在码头上倒空,酒和油储存在一个个巨大的仓库内,大部分空瓦罐直接扔掉。就在台伯河码头旁,有一座人造的小山Monte Testaccio,高34米,周长1公里,就是由丢弃橄榄油瓦罐的碎片堆成。据估算堆成这样一个小山包至少需要五千三百万个瓦罐。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3] [/align]
[align=center][color=#666666]产自地中海各地的瓦罐 [/color][/align]
从共和国后期开始,罗马城内的贫民(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得到低于市场价一半的粮食,58BC后完全免费。奥古斯都将其固定成了一种救济制度。在5BC,有32万个成年男子领取救济,每月发一次供应证,但每个人能领多少及如何发放,没有可靠的资料。我们所知的就是在图拉真时代,不再是每月发一次小麦,而是每天发面包。(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说法,每天每份是3磅面包或可以买3磅面包的钱。不过吉本没有提及数字来源). 从海外运粮的工作由签了合同的私人承包商负责,由于罗马附近没有天然良港,台伯河口的Ostia港也淤积了,无法停靠那些载重量几百吨的海船。在共和国时期运粮船先停在那不勒斯湾的Puteoli港。粮食换乘较小的船只,沿海岸北上到达Ostia港,再换成1百吨以下的河船运到罗马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4] [/align]
这种运输方式效率太低,无法满足罗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1世纪中期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在Ostia港北面3公里,建了一个人工海港Portus。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两条大型防波堤围成一个港湾,在南防波堤的尽头是一座以亚历山大灯塔为原型的灯塔。为了加固灯塔的地基,一艘载重量约1300吨的巨轮被灌满混凝土,沉入海中。新港可以停靠大型海船,但仍会受天气影响,AD62的一次大风暴破坏了港内的200条船。2世纪初,图拉真在海岸后挖了一个六角型的大池子,深5米,面积32公顷,同时挖了一条40米宽的运河直通台伯河。从此罗马城才算有了一个可以全天候、24小时使用的外港。
[color=#ff3366]3.供水[/color]
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的居民还是使用井水、泉水和蓄水池里的雨水。在312BC,罗马人开始修建第一条高架引水渠,到了2世纪初的图拉真时代,罗马人的供水已经完全依靠10条主要的引水渠。19BC,阿格里帕(Agrippa)修建了Aqua Virgo,为他新建的大型公共浴室供水。这是第一条专门用途的引水渠。到了2BC,奥古斯都又建了一条引水渠Aqua Alsietina,专用于为台伯河西岸的一个人工湖供水。这个人工湖主要用来进行海战演习和庆典表演。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5] [/align]
量最大的引水渠是Aqua Claudia和Aqua Anio Novus,完成于AD52,它们实际上共用一个高架。如上图,上层是Aqua Anio Novus, 源自Anio河的河水;下层是Aqua Claudia,源自Anio山谷的泉水。对所有的公共建筑,罗马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引水渠,他们认为埃及人、希腊人建的那些金字塔、陵墓和巨像虽然壮观,但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6] [/align]
水引进城市后,先流入蓄水池,池底的管道为公共设施供水-喷泉、澡堂等等,水池壁上的管道为私人供水,这样的设计保证了在水短缺时,私人用水会被首先切断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7] [/align]
上面是供水管(罗马人的供水管都是铅制品)和下水道的截面图,分支水管直接通到住宅。但大部分的平民住宅没有这样的自来水,必须要去附近的公共喷泉提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8] [/align]
图中就是一个小型的公共喷泉,这张图还体现了罗马城的另外一个特点:住宅楼之间的间隔很小,这个以后再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9][/align]
从3世纪开始,引水渠的水被用来推动水磨,为罗马城提供大量面粉。这是公元4世纪法国南部的水磨,水流被分为两股,共16个直径2米的水轮,每天能生产27吨面粉。
[color=#ff3366]4排水 [/color]
罗马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下水道系统, 各个区域都有它们的主下水道,分别流进台伯河。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Cloaca Maxima(见下图),长900多米,高4.2米,宽3.2米,现在还在部分使用。33BC阿格里帕曾亲自坐着小船,进下水道里视察。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0] [/align]
支线下水道通常建在道路下面,接受来自澡堂、街道和民宅的废水,公共喷泉里溢出的水直接流进下水道,冲刷里面的废物。实际上很少有住宅连到公共下水道,民宅里的废水都流到一个封闭的污水坑里,屋主花钱请人定期来清理,囤积下来的残渣可以卖作肥料。罗马的下水道缺乏阻挡沼气和臭气外泄的过滤装置,而且由于建得太低,台伯河涨水时河水会倒灌进去。
[color=#ff3366]5.厕所 [/color]
据帝国后期的记载,罗马城的公厕有144个,都建在公共澡堂旁边,便于使用澡堂里流出的脏水冲洗。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1] [/align]
这是一座大型公厕的复原图,大概有100个座位。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下水道,座位前用来洗手的水沟,还有罗马人的厕筹-海绵棒(sponge stick)。海绵棒用后就放入中间的水槽。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2] [/align]
现存于Ostia城的公厕,25个座位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私厕,用厨房的脏水冲,污水流进公共下水道或住宅的污水坑。对海格里尼姆城(Herculaneum)的发掘表明,所有的住宅,甚至位于2楼的公寓,都配有厕所。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3] [/align]
海格里尼姆在79AD和著名的庞贝城一起,被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淹没
[color=#ff3366]6.澡堂[/color]
公共澡堂对于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洗澡的地方,还起着社交中心的作用。所以一个完善的公共澡堂,必须配有图书馆、会客室、健身室、餐馆、商店和花园。在33BC罗马城有170个澡堂,5世纪初,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56,其中包括11个大型皇家澡堂(由皇帝自己掏腰包兴建的公共澡堂,并冠以皇帝的名字)。最大的是戴克里先大澡堂,容量3000人。公共澡堂都是由富人捐款修建,作为社会公益,所以收费很低,通常男性收费1quadrans,女性加倍,儿童免费,当然毛巾和香油要自备。(quadrans是罗马最小的硬币,等于1/64第纳瑞斯)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4] [/align]
上图大竞技场(Colosseum)后面这个宫殿般的建筑,是图拉真大澡堂,AD104开始兴建,五年后对外开放。由于角度的关系,澡堂看起来象长方形,其实是近似正方形。从花园的外围建筑算起是340 X 330米,花园里面的主体是190 X 212米,大竞技场也不过188 X 156米。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5] [/align]
这是澡堂前半部分的剖视图,从左到右是大门、露天的冷水浴池、冷室(frigidarium)、温室(tepidarium)、热室(caldarium)。洗澡的过程是先进更衣室,脱下衣服,涂上香油,到练习室运动一会,然后进入温室,在温水池里泡泡。再进入热室,坐在椅子上熏蒸汽,再泡在热水池里,由自己或仆人动手,用金属刮板把全身刮一遍。最后到冷室,跳进冷水池,这才算完成一次标准的罗马式蒸汽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6] [/align]
这是热室内部,可以看到各个热水浴池,下面的火炉和通道。罗马人的热水器主要有两种,下面是这两种的截面图。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7] [/align]
图的上半部是普通民宅用的热水器,公共澡堂用的是第二种。浴池和水箱是连通的,箭头B显示热水上升流进浴池,箭头A显示冷水下沉流回水箱,被再次加热。浴室地板下方是空心的,火炉产生的热气从地板下流过,墙壁内有一排瓦制的管子(见下图),热气沿着管子上升直到屋顶,排出屋外。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8][/align]
这样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得到了加热,将整间屋子变成蒸汽浴室。从上图可以看出地板比墙壁厚得多,免得地板太热,烫脚。罗马人显然知道利用温室效应,温室和热室都开有巨大的窗户,装上双层玻璃
[color=#ff3366]7.住宅[/color]
奥古斯都宣称:“我接手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一座大理石造的罗马城。”他是在吹牛,大理石通常只用来建造豪华住宅、公共建筑的柱子,及在墙上贴一层大理石砖。罗马城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灰石、火山岩、烧制的砖和混凝土罗马的混凝土(opus caementicium)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与现代混凝土不同,它是用火山灰制成的泥浆、碎石或砖混合搅拌而成,按古代的标准算是相当牢靠,而且可以用在水下。当建造拱顶时,混凝土里不放普通的石灰石,而用火山浮石,火山浮石里面有许多空泡,可以大大减轻房子上部的重量。以前,罗马城用的白色大理石全部进口自希腊,彩色大理石来自北非和爱琴海。35BC以后,罗马人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开采白色大理石,奥古斯都能够建造大理石的罗马,建材的本土化降低了运输成本是原因之一。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9] [/align]
上图是罗马房屋的地基,先用木板围上,再一层层地浇上混凝土。地基打好后木架子通常就留在原处。墙的样式主要有三种: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0] [/align]
左起Opus incertum:最早的样式,混凝土表面砌上一层经过粗略磨制的石块。
Opus reticulatum: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后期,混凝土表面砌着同样大小,金字塔状的石子。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1] [/align]
世纪中期起广泛应用,混凝土外面砌上砖。罗马城进入繁荣时期后,面临着于现代大城市一样的问题-人多地少,它的解决办法也和现代人一样,向高处发展。至迟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就出现了两层以上的公寓楼,而且不断加高,三层、四层甚至五、六层的公寓楼陆续出现。住这些公寓的都是穷人,为了降低成本,屋主不但往高里盖,楼与楼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小。很多街道只能过一辆车,有些地方窄到楼上凸出的阳台几乎能碰上对面的公寓楼。 情况越来越恶化,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政府发布命令,公寓楼不得高于21米(六层)。在AD64的罗马大火后,限制降到18米,楼间距不得小于3米。
最初高层公寓楼的建材是Opus craticum(上图),木质框架里灌上碎石和泥浆。这种结构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砌砖头,便宜;最大的坏处是不防火。AD64那场大火据说烧掉近半个个罗马,与这种木质框架颇有关系。大火之后,砖结构成为公寓楼的主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2] [/align]
在罗马城内,富人住的是带花园庭院的平房,穷人只能住公寓。上面是一栋五层公寓楼(insula)的结构图,一楼靠街的屋子都是商铺,其余的住人。楼中间是天井,给中间的屋子提供光照。一楼和二楼有公厕,各有九到十个位子。这样一个公寓大概住40人,根据4世纪中期的普查,罗马城有46602栋房子,大部分是这样的公寓楼。
[color=#ff3366]8.街道 [/color]
在罗马城内,除了几条主路外,居民区内的道路都十分狭窄。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3] [/align]
城内最宽的大路,凯旋式就走这条路。由于街道狭窄和楼上住户直接向楼下倒垃圾,路上行人被砸到的事经常发生。为此罗马人专门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这种受害者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凯撒统治时期,发布了命令,屋主必须清理自己房屋前的区域。还命令营造官(aedile)组织一批人清扫街道。街道狭窄和缺乏人行道还使交通事故频发,凯撒曾下令,除了政府拥有的,所有轮式车辆不得在白天进入罗马城。即使没了车辆,街道仍是拥挤不堪,于是有了第二道命令:禁止在街上摆摊。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4] [/align]
狭窄的街道,房屋外突出的拱廊是为了方便消防队员。与庞培城不同,罗马的街道两边大都没有专门的人行道。
[color=#ff3366]9.饮食 [/color]
有钱人的厨师通常由奴隶充当,穷人的房子则经常没有厨房,所以罗马人的厨房不受重视,远不象现代那样卫生整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5] [/align]
上图是1世纪普通的罗马厨房,炉子下面放柴火、木炭,煮东西都在炉子上面。至今为止,没发现罗马人有在厨房里装烟囱(希腊人的厨房大都有烟囱),厨房的通风靠窗户。为了便于使用供水排水系统,厕所经常与厨房挨得很近,或者干脆装在厨房里。就象上图,炉子旁就是马桶。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6] [/align]
罗马人的烹调方式主要有两种,要么如A,罐子放在三角架上煮;要么将食物放在烧烤架C上烤。即使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厨房,很多住公寓的罗马人也没有,他们必须要下馆子。罗马城里有大量的面包房、酒馆、饭馆,主要顾客都是穷人。面包是罗马人的主食,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一直到174BC,罗马城里都没有面包房。大家都在自己家里做面包。老普林尼还提到了罗马人常吃的面包根据不同的形状和口味,有很多种。面粉如不做成面包,也可以加水煮成类似麦片粥的食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7] [/align]
这是一个面包作坊,磨面粉、和面、烘焙和销售一条龙。罗马人的口味很重,食物经常配有大量的调味品,辛辣和酸甜味的最受欢迎。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放胡椒,连烤小甜饼时都用。调味品中最重要的是盐,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以低价销售;醋由葡萄酿造;罗马人没有糖,用蜂蜜来提供甜味。除了面包作为主食外,蔬菜、水果和肉类也是必不可少的。本土的橄榄、葡萄、苹果、梨、李子,从外面引进的胡桃、杏、桃子、樱桃、石榴和柠檬,在前一世纪,意大利已是遍地果园。蔬菜方面除了西红柿和马铃薯,现代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大都有。
海格里尼姆城壁画上的桃子,这幅画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倒不在桃子,而是旁边的玻璃瓶,说明当时的玻璃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肉类吃得最多的是猪肉,穷人则多吃山羊肉。牛肉属于奢侈品,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只有在祭祀后,才能吃上祭祀用的牛肉,而且内脏要先分给祭司。野味的需求也很大,象鹌鹑、野兔、鹿肉、野猪和雉,最贵的是孔雀,一只至少50第纳瑞斯。家禽如鸡、鸭、鹅和鸽子,水产如鱼、牡蛎、蚌,也吃得不少。
水、奶(羊奶牛奶)和葡萄酒是罗马人的三大饮料。喝葡萄酒时通常要掺上几倍的水,喝纯葡萄酒被认为是蛮族的行为
那些家里有专门饭厅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是半卧着用餐的,上图就是一个小型的晚餐聚会。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8] [/align]
如果空间够大,则摆设如上图,中间的空地摆一张大桌子。用餐者左侧身半卧,左肘撑在榻上。左边的卧榻lectus imus 是主人的位置。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9] [/align]
妇女坐在丈夫的榻旁用餐,小孩则坐在椅子上。
[color=#ff3366]10.衣服 [/color]
罗马人的服装与希腊人的非常类似,没有内裤,束腰外衣(tunic)是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的基本装束。束腰外衣很简单,就是前后俩块方形的羊毛布,在肩部缝上,腰上系根带子,肩膀两侧的布下垂,就形成袖子,有些人会缝上长袖。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0] [/align]
如上图A,劳动人民的外衣一般不过膝,有钱人就长的多。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在外衣上加件外袍(toga),见上图C,但这种外袍比较笨重,有闲阶级才会穿着。高级官员和元老可以穿镶紫边的外袍。请注意上图的B和C,花边是染在tunic,而不是在toga上,说明他们有身份,但还没有达到元老的级别。E是士兵和工人穿的凉鞋(hobnailed sandal),F是靴子。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1] [/align]
这是元老穿的外袍 一直到2世纪初,罗马人都不流行蓄须,后来在哈德良提倡下,才兴起希腊式和亚洲式的胡子。由于罗马的剃刀不锋利,刮胡需要高度的技巧,一个擅长刮胡的奴隶能卖到很高的价钱。人们很少自己刮胡子,而是去理发店,普通罗马人早上出门的第一件事通常是去理发店刮脸(据记载小西庇阿是第一个每天刮脸的罗马人),所以理发店总是人头拥挤,成为市井传言的集散地,理发师用各种软膏(dropax)来剃头刮胡。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2] [/align]
马妇女穿的束腰外衣(stola)很长,通常在胸部下面加系一条带子,以凸出XX,如上图左。上图右的妇女披着长围巾(palla)。除了妓女和犯了通奸罪的女人,罗马妇女不穿toga。妇女一般有穿短内衣(但一样没有内裤)和strophium(软皮革制,起胸罩的作用),见下图。
[align=center] [attachment=11328703]
[color=#666666]女用凉鞋和软皮鞋[/color] [/align]
[color=#ff3366]11.儿童 [/color]
在罗马的所有阶层,婴幼儿死亡率都是很高的。活下来的与现代儿童一样,玩耍和上学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4]
[color=#666666]这是一辆由山羊拉的玩具车 [/color][/align]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5]
[color=#666666]石制棋盘[/color] [/align]
罗马的[color=#ff3366]学校[/color]分三级:初级学校(Primary school),语法学校(Grammar school),技巧学校(Rhetoric School)。只有出身富裕的儿童才能完成二、三级教育。初级学校都是民办的,但政府会提供场地。接受7岁以上的男女孩,教读写和数学。只有出身下层的孩子才会进初级学校。有条件的家庭会请家庭教师给孩子进行初级教育,更富有的家庭则干脆买一个有文化的希腊奴隶当家教记载表明,大部分教师都是奴隶或释放奴隶,工资非常低,有一个著名的语法学家阿普利乌斯任教于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年薪100第纳瑞斯。到了十一岁左右,有条件的孩子可以进入下一级的语法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法,以及音乐与几何,其他孩子开始打工,进入社会。十五岁后可以进入技巧学校,学习演说和写作的技巧。在课堂上,老师会要求学生们想象一个历史场景,例如,作为即将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你将如何对士兵们进行鼓动演说?上完课由学生们自己评判,谁的演讲最有力。技巧学校毕业后,有条件的年轻人会去希腊留学一两年,到雅典、罗德斯岛或小亚细亚,生活在希腊人中间,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6] [/align]
罗马人的书写工具,A 墨水盒 B 芦管笔 C 青铜笔(笔头和现代的钢笔差不多)
生用的书写板和笔。书写板是木制,表面涂蜡,用笔的尖头在蜡上书写,笔尾部是平的,作用同橡皮。
在14-19岁之间一个适当的日子,通常在每年的3月17日,罗马的少年可以到神庙举行他的成人礼,换上成人的toga,然后上统计部门登记注册,从此就算一个完全的公民了。
[color=#ff3366]12.房 事[/color]
罗马人生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是模仿希腊,但在性关系上,有两点主要不同。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color=#ff3366]男同性恋很流行[/color],被认为是青少年成长的必经之路。罗马就没有这个风俗,同性恋受到歧视。恺撒年轻时有过同性恋的嫌疑,此后一辈子恺撒的政敌都以此攻击他;安东尼也曾指责屋大维与恺撒搞不正当关系。帝国时期男同性恋现象有所增加,但仍不被主流社会接受。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7] [/align]
古希腊的男恋人们在亲热汉化交流空间。另一点不同是罗马人性行为的半公开化。前4世纪,一个希腊作家访问了意大利中部的伊特拉斯坎,对当地人如此评价:他们的性关系混乱,不分时间地点地乱搞,如果一个人走进一间房子,经常能看到屋里的人在毫不感到羞耻地进行某些行为。' 罗马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相当开放。当然开放归开放,有些事还是不能看,有些话还是不能说。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AD8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公开罪名是写淫秽诗篇,但舆论普遍认为奥维德获罪,是因为他看到了奥古斯都外孙女的某些私人行为,而且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8] [/align]
罗马的风铃,作为吉祥物公开挂在住宅和商店的门口。罗马人认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能带来好运,因此在大门、客厅和护身符上都经常刻有此类形状的东西。在庞培城废墟里发现了大量壁画,卧室里的壁画大都是下面这个类型。
壁画上的姿势千姿百态,最常用的还是女上 位,因此欧洲人有时把女上位成为罗马式。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9] [/align]
庞培城的一所澡堂的壁画,右起:女上位、侧后位、女对男口交、男对女口交。罗马城的妓院数量没有统计,但1万2千人口的庞培城有34所妓院,从高档到低档为各层次的顾客服务。其中一所为穷人和奴隶服务的妓院有10间房,分两层。墙上的广告上标明,一次口交服务只需几个阿斯
[color=#ff3366]13.赛车 [/color]
看过《宾虚》的人对罗马的赛车都会有深刻的印象,罗马城的赛车场好几处,最宏伟著名的是大赛车场Circus Maximus。大赛车场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后来不断扩建,最后图拉真将它建到了最大规模,全长600米,宽200米,最大容量估计可达200000人。赛车手要绕着赛场的中心岛(长344米),逆时针跑7圈,近6公里。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0] [/align]
公元4世纪初图片底部是13个拱门carceres,这里是赛车的出发点,最多可以12辆赛车同场竞技(中间的门不用)。请注意中心岛中央最高的花岗岩方尖碑(高24米),这是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所建(公元前13世纪),10BC奥古斯都把它运到了罗马。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1] [/align]
这是起跑门,门外插着插销,插销上连着绳子,经过一个滑轮,通向门上方。比赛开始后,操作员拉起开关,触发扭力弹簧,所有起跑门上的插销都被同时拉开。(注意到门两边的雕像了吗?)
门轴上也装着扭力弹簧,插销打开后,两扇门向外弹开,赛车冲出。 在帝国时代,赛车已经变得非常专业化。所有的车手都属于车队,每个车队都有自己的颜色,从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城内通常有四个车队:白色的Albata;红色的Russata;蓝色的Veneta;绿色的Prasina(后来在图密善时又加了两支:金色和紫色)。每个车队都是一个经济实体,化巨资进口马匹,有自己的训练员、铁匠、兽医和马夫。政府或私人请车队出赛都要付出场费。皇帝们都有自己支持的车队,例如伟大的卡里古拉就支持绿队,经常在绿队的马房里吃饭过夜。与角斗士一样,赛车手都出身社会下层,或是奴隶和释放奴隶(freedman)。同样与角斗士一样,胜利者将成为万众崇拜的偶像,有不少奴隶靠比赛的奖金为自己买得了自由。一个西班牙赛车手Diocles在24年内参加了4257场比赛,赢得1462场,总奖金9百万第纳斯。现存的最高胜利记录是Pompeius Muscosus的3559场。同时赛车手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车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据记载有一个赛车明星Scorpus,在赢得2048场胜利后,于27岁撞车身亡。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2] [/align]
在绿色车手后面的红架子上有七颗金蛋,车手每跑完一圈,金蛋就放倒一颗,赛道的另一端有七个金色海豚,起同样作用。比赛日开始,车手们列队进入赛场,观众开始欢呼和下注。一声号角后,主持比赛的官员扔出手里的餐巾,比赛正式开始。一个完整的赛日有24场赛马,赛马日之外,赛车场里也会有一些新奇的表演。例如十匹马拉的赛车、马术、赛跑和接力。赛日最后是给胜利者发奖-象征胜利的棕榈叶、花冠和金链子
[color=#ff3366]14.剧院 [/color]
Colosseum经常被译成圆形大剧场,其实它不是演戏的剧场,罗马人的剧场也不是圆形的。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3] [/align]
罗马人的剧场与希腊人的一样都是半圆形,上图是两个剧场,上面的是马尔塞鲁斯剧场(Theatre of Marcellus),是奥古斯都为了纪念死于23BC的外甥和女婿马尔塞鲁斯修建的,直径150米,座14000。下面的是Theatre of Balbus。戏剧是罗马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碰上公办私办的庆典都要大演几天甚至一二十天。但在共和时期,元老院禁止在罗马城修建永久剧场,认为天天看戏会使公民们颓废。所有的剧场都是临时搭建的木结构,庆典后拆除。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自然史》里描述了58BC的一个豪华临时剧场,舞台后的布景有三层,共360个柱子,第一层是铺大理石,第二层铺玻璃,第三层镀金的木板。整个剧场的装饰用了3千个雕像,可以容纳8万人。
55BC庞培修建了罗马城的第一个永久剧场(上图),直径160米,27000个座位,剧场后还附带了一个大花园。为了绕过元老院的禁令,庞培宣称这是献给维纳斯女神的(据说这个剧场是庞培的老婆、凯撒的女儿朱莉亚提议修建的,她还亲自参与了设计。由于罗马人都认为凯撒出身的朱利乌斯家族是维纳斯的后裔,所以庞培提出了这样一个建剧院的借口)。
剧场的弧边是阶梯状排列的座位,直边是舞台、背景建筑和后台。戏剧中演员的服装基本上和现实生活中一样,标准服饰是束腰外衣加一件袍子。由于一个演员常常要在一部戏里演不同的角色,面具是必备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4] [/align]
悲剧里英雄和女英雄的面具
喜剧用的面具:左起,老人、年轻人和奴隶古希腊流行的戏剧主要是悲剧和喜剧,流传下来的剧本都是些有深刻内涵的作品。罗马人的戏剧要大众化的多,除了从希腊人那学来的喜剧和悲剧,平民化的闹剧、滑稽剧、哑剧和歌舞剧都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公元前1世纪,大批无业贫民涌进罗马后,完全改变了罗马观众的口味,戏剧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粗俗化。哑剧(Pantomime)是最有罗马特色的剧种,戴面具的演员们用舞蹈和各种动作来演绎剧情,合唱团和乐队伴奏。高雅的希腊人不承认这是戏剧,称其为“Italian dance”,丝毫不顾哑剧是由两个希腊人首创的事实。
[color=#ff3366]15.大竞技场 [/color]
早期罗马人相信,人的鲜血能抚慰死者的灵魂。于是他们在葬礼上杀战俘和奴隶献祭,后来演变为葬礼上的角斗表演,再后来角斗成了一项纯粹的娱乐。角斗表演分三种:猎兽(venationes);用野兽处决犯人;角斗士的格斗表演。前两种总是以一方的死亡告终,后一种则不一定要打到死。在一个演出日,通常上午是猎兽表演,午饭时间处决犯人,下午角斗士表演。在专门的竞技场修建以前,角斗表演经常在赛车场、广场(Forum)和临时搭盖的木头剧场举行。罗马城内最早的石头竞技场建于奥古斯都时代。AD67犹太人起兵反抗罗马,尼禄派韦伯芗平叛,最后在AD70韦伯芗的儿子提图斯攻陷耶路撒冷,洗劫并烧毁了所罗门神庙。这时已是皇帝的韦伯芗决定用从犹太人那抢来的财富修一座大竞技场,AD79韦伯芗病死,提图斯继任,并在AD80主持了这座宏伟建筑的落成仪式,庆典举行了100天,最盛时一天杀了5000只野兽。八卦:尼禄统治时期,在东方各行省盛传一个预言,一个从犹太土地上走出的人将统治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很可能是***徒编的,但犹太人信以为真,于是起兵造反,以为能够推翻罗马的统治。赋闲在家的韦伯芗被授予大军,前往巴勒斯坦,并依靠这支军队在AD69赢得罗马内战,当上罗马帝国的皇帝,预言应验了。这真是典型的蝴蝶效应,一个谣言最终导致了犹太人流落四方,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东。对罗马人来说,本没有希望的韦伯芗当上皇帝,改变了帝国的走向,并给后人留下了大竞技场和无穷的话题。大竞技场为椭圆形,188 X 156米,高45米,地基是厚12米的混凝土,地基上的80根石灰岩承重墩构成主体框架。墙的建材是混凝土外砌方砖或火山浮岩。
这是根据古罗马工程师Vitruvius的描述绘制的滑轮组起重机,用了两个定滑轮和一个动滑轮。有古籍宣称这种起重机是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发明的。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5] [/align]
座位区分为好几层,最下层(Level 1)的是元老席,从C点进入,只要爬一小段台阶。最上层(Level 5)座位是木制的,总共得爬138级台阶。从奥古斯都时代起,所有剧院马场的坐席都划分为不同区域留给不同阶层的观众,这是奥古斯都重建社会秩序计划的一部分。最下层最靠近演出区的位置永远是留给元老和高级官员的,社会地位越低,座位越靠上,妇女的位子在最上方(神庙的童贞女可以坐在元老席)。在座位的上方可以看到一根根木桅杆,这不是旗杆,而是用来系绳索和巨大的帆布遮阳篷。总共有240根桅杆,需要1000人来收起和拉上遮阳篷。汉
观众席的入口,除最高层外座位都是大理石,高44厘米,宽61厘米。总共有45000到55000个座位。
上图为场地中央,在元老席上有个包厢,是皇帝的专座。场地下另有一番天地。
场地上有大量的活门和升降梯,由绞盘操作。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6] [/align]
猛兽的笼子和出入的通道。在右上角可以看到元老席的台阶很宽,可以放下椅子,不用坐在冰冷的大理石上。
上图的猎手如果披上红袍,那只身上插着两根标熗的豹子换成公牛,就和现代的斗牛士差不了多少。但实际上,古罗马猎兽表演中的猎手(venatores)即使在角斗士眼中,也是卑贱的。他们不穿铠甲,只穿短外衣或裸体。
一个犯人被绑在小车上,推向一只猛兽,不少早期犯法的基督徒就是如此处决的。下面是被铁链栓在一起的熊和公牛,以确保它们不会临阵脱逃。最初的角斗士来源于被判死刑的战俘和奴隶,到了帝国时期,自愿参加的自由民和被宣判有罪的犯人也可以加入。2世纪中哈德良皇帝曾禁止角斗表演,几十年后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就是电影《角斗士》开头那个老皇帝)把斗兽表演也禁了,不过这些皇帝一死禁令就撤销了。罗马的历史上共出现过大约20种角斗士,每一种都使用不同的装备,用不同的方式战斗,如高卢式、不列颠式(架着轻型战车),但具体细节流传下来的很少。角斗士一般不用本名,而是起一个响亮的艺名,用传说中的英雄如帕修斯(Perseus)、阿甲克斯(Ajax)等等,或者以自己的特长起名,如Ursius(如熊一般)、Callidromus(迅捷)。所以如果史书中提到一个高卢角斗士Deathclaw,那他不一定是个高卢人,更可能是一个高卢式的角斗士,艺名叫死亡爪。 八卦:基于角斗士的以上两个特点,澳大利亚一个写历史小说的女作家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所谓色雷斯人斯巴达克,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人,艺名叫斯巴达克,按色雷斯风格训练的角斗士。罗马人并不知道的他真实身份,以讹传讹,传到一二百年后的普鲁塔克和阿庇安手上,就成了色雷斯人斯巴达克。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7] [/align]
色雷斯式角斗士的头盔 B 萨姆耐特式头盔
最早的两种角斗士是萨姆耐特(Samnite)式和高卢式。这两个民族是罗马人早期的死敌,罗马人用他们的战斗方式来训练角斗士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萨姆耐特:最初的萨姆耐特角斗士是轻装,然后装备越来越重。带面罩、羽毛的头盔,左脚有高过膝盖的护胫甲,与军团士兵同样的塔盾和短剑。高卢:最初也是轻装,不带头盔,配长盾。到了共和后期,加上了不带面罩的头盔和六角长盾。色雷斯: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势力扩张到色雷斯,于是色雷斯式角斗士合乎清理地出现了。配小圆盾,弯刀,两脚都有长护胫甲。网民:Retiarius(Net man),最常见的角斗士,用渔民的渔网和三叉戟,加一把匕首。他的防护就是左臂上的腕甲和环甲,有时左肩上加个肩盾(galerus)。有些人认为按照字面意思,只有用剑的才算角斗士,因为英文中的角斗士(gladiator)一词源于拉丁文gladius,原意是短剑。
剑士(Secutor):装备军团式的塔盾(Scutum)和短剑,护臂环甲(Manica),由于在角斗场上剑士通常是与网民捉对厮杀,他的头盔上没有长帽檐,以免被网勾住(上图)。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9][/align]
上图左起,受伤的网民,鱼叉已被击落,正伸出手指向观众和裁判恳求结束战斗;剑士;两个不知道类型的重装角斗士;色雷斯角斗士拿着圆盾长矛;色雷斯人的对手,像是个萨姆耐特角斗士,盾牌掉在地上,向裁判伸出手指;裁判兼角斗士教练(lanista)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的角斗士学校,公办私办的都有。一个新入学的角斗士叫做Tiro,学校的教学方式基本与军团的新兵训练一致,或者应该说军团的训练方式与角斗士一致。 公元前2世纪末,执政官Publius Rutilius,从角斗士学校雇来一批教练(lanistae),用训练角斗士的方法来训练新兵,效果很好,这套方式迅速被推广(在《凯撒3》里,建角斗士学校能提高军团战斗力,就是这个道理)。Tiro只能使用木剑和柳条盾(木剑和盾都是加厚的,比真正的武器重),练习刺木桩。等他的动作完全规范后才能真刀真熗地与真人对打,这时他升格为armatura。角斗士通过全部训练后称为pali(stake木桩),再根据成绩分为Primi pali、Secundi pali和Tertii pali(第一木桩、第二木桩和第三木桩)三个等级。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8] [/align]
根据庞贝城壁画复原的角斗场景,剑士与网民正在搏斗,网民的网已撒出,但显然没有效果,他配有肩盾作为没有头盔的补偿。一旁是裁判拿着棍子,场地边是伴奏的管风琴乐队,后面的黑衣人是一个政府官员,打扮成Charon(罗马神话中冥界渡口的船夫),他负责用烙铁确认角斗士是否真的死了。然后尸体就从左边的小门拖走,地上的血迹则用沙子盖上。
[size=3][color=#000000][b]古罗马币介绍[/b][/color][/size]
中国史书使用“西域”这个词时有狭广意之分。狭义上指现在的新疆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了更远的中亚、西亚乃至丝绸之路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本贴就介绍下广义西域币里的古罗马币。
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人们眼里的西域充满神秘,张褰使西域十三年,最远到了安息(今伊朗一代),对大秦(罗马帝国)却汪洋兴叹,当地人说要坐船半年才能到达,现在看这话水分太大,很可能是因为安息与罗马为敌,且控制着丝路贸易,不愿意让汉朝与罗马直接沟通。
罗马城本是希腊世界的一个小的城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改为实行共和制,称共和国。其后开始扩张,公元前146年灭迦太基控制北非,公元前168年打败马其顿控制希腊半岛,后又东占叙利亚和埃及,北占高卢。随着军事扩张,其军事首领的权利日大,议会不得不退让。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议会冠以奥古斯都,有了类似于汉代的皇帝的权力,史家称为罗马帝国的开始。公元后的两百年间达到全胜,这是中国的东汉时期。
中国在经历了黄巾三国的内乱,和五胡十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终于稳定下来,在公元600多年进入了盛唐。在此期间,罗马的风云变换有过之而无不及,内部帝位纷争,皇帝死于谋杀者十有八九,外部有日耳曼等蛮族(当时的日耳曼人连文字都没有)的威胁和渗透,到了公元4世纪,戴克里先(Dioclitian)意识到罗马帝国的问题已经太多,一个人皇帝难以管理,建立了四主共治的制度,罗马帝国开始分裂。人心理上喜欢大,喜欢统一,喜欢稳定,但有时候只有分裂,变化才能生存。
君士坦丁一世登上皇位后,为了罗马的生存开始在东部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要地修建新都。330年新都建成,定名新罗马(Nova Roma),就是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死后,罗马帝国永久的分裂为两个国家。西罗马继续遭受日耳曼族的攻击和渗透,在公元486年其皇帝被日耳曼族的将领夺位,史家定为西罗马的覆灭。东罗马则经过变革而生存下来,加强了皇帝的权力,立基督为国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使罗马帝国延续了一千年,直到1453年亡于奥斯曼帝国。“拜占庭”一词是“罗马”的希腊语音译,因此拜占庭就是罗马。古罗马币和拜占庭币是一个连续体,把分界点选在哪里全在人为。
钱币学上一般不把395年作为拜占庭币的开始,而是把安纳斯塔一世(公元491-518)作为罗马币与拜占庭币的分界。原因在于安纳斯塔一世最先在币上使用希腊铭文,以前都是用罗马字的。而拜占庭文化的特点就是希腊化了的罗马帝国。
古罗马币从公元前6世纪出现粗铜铸币开始,到491年安纳斯塔一世币制改革为止,罗马币经历了多次改革。下面选重要的几次略作展开。
和希腊人最早用金银不同,罗马人最早是用称量铜块作货币的,最早的叫粗铜(aes rude),后来形状更规则并加上印记,叫印记铜(aes signatum)。这种粗铜币是铸造的而非打制的,这点和中国比较象。铜比银镕点低而硬度高,因此更适合铸造。这两种都是称量货币,每次买东西要带着秤的,因此叫钱币有些勉强。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种罗马钱币是公元前289出现的重铜阿斯(aes grave)。重量为1罗马磅(324克),每1罗马磅等于12盎司(uncia)。这种圆形铜铸币,正面均铸有两面神等神像,背面均为高昂的船首。当时罗马已经开始了海上扩张。
下图为重铜阿斯,图片取自(CNG):
图案就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两面神Janus是罗马神话中掌管门户的神,一面代表开始,一面代表结束。拉丁文和英语中的一月就是从Janus来的,因为一月January是一年的开始。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0] [/align]
罗马最早的银币采用希腊重量标准-德拉克马。到公元前211年发行第一枚第纳尔(denarius)银币,这种银币作为罗马的主币从共和时代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中期公元200多年。共和早期1个第纳尔银币值10个阿斯铜币,后来阿斯币慢慢变小,1个第纳尔值16个阿斯。 共和时期的钱币上不印人的头像,只有神像.
下图为共和时期第纳尔银币:
公元前85年发行的第纳尔银币,直径19.6mm,厚2.03mm,重4.03克.面是戴桂冠的阿波罗头像,背是小爱神丘比特骑着公羊,上面是代表Dioscuri兄弟的柱状物,脚下横线下面是代表能量的雷电球,整个图案被月桂环环绕。Dioscuri兄弟是希腊主神宙斯和Leda所生的双胞胎儿子,特洛伊美女海伦的哥哥。他们是互信合作的象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1] [/align]
再补充三个罗马共和时期第纳尔银币,本贴所发图片如非注明均是本人藏品或售出品:
下面这枚币发行于公元前151年,直径16.2-17.8mm,厚2.3mm,重4.2克.面是戴花冠的女神像,背面是飞马从台上跃起。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2] [/align]
这枚币发行于公元前128年,面:罗马女神,脑后麦穗.背:胜利女神驾马车,下有勇士斗狮,3.9g,直径18.61-20.89mm,厚2.07mm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3] [/align]
这枚币发行于公元前119年,面是雅努斯神(两面神),背:罗马女神举起战利品.重3.8g,18.5mmx2mm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4] [/align]
罗马金币使用的更晚,起初只在政府实在缺钱打仗时发行,到凯撒时代仗打得太多了,开始常规发行,规格为5.4克的奥雷金币(aureas)。罗马的金币成色重量相当稳定,几百年基本不变,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0多年才被轻1克左右的索利多(solidus)金币取代。而引入索利多也不是因为奥雷金币本身的问题,而是为了与其他材质币换算方便。
第一图为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奥雷金币(图片取自CNG):
第二图为哈德良的奥雷金币(图片取自CNG),重7.2克,公元134-138年打制。这枚是纪念哈德良巡查非洲行省而打制的,背面是戴大象头盔的非洲女神和狮子。
第三图为公元310年君士坦丁大帝改革币制后的索利多金币,重4.5克左右
第四图为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之后,公元527-565年拜占庭时期,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发行的索利多金币
面:皇帝头像,背:天使执十字架,此时币面上开始出现基督教标志,要到更晚些时候耶稣的头像才出现在币面上.
重4.33g,直径19.13-20.01mm,厚1.1mm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5]
[attachment=11328726] [/align]
下面就继续说金币。在三种币材中,金币的成色和重量比银铜币稳定,减重最慢,改革也就最少。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因为金币价值太高,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罗马拜占庭的金币一般不用来发工资和购买柴米油盐等日常用品。根据Sayles的Ancient Coins Collecting II一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金银比价约为1:13至1:15(中国古代缺银,比价低些)。一个技术工人的工资约为每天一个第纳尔银币,一个金币就是近一个月的工资。就算发个金币给工人他也要换成银铜币才能花。因此金币多用于大额交易,军费,储存财富等功能,流通速度比银铜币要慢。一个佐证就是出土的金币中有很多基本未流通的,好品的比例比银铜币都大。
金币价值高,使用又不频繁,接收的人一定小心检验其成色和重量,再加上使用的人主要是政府所依赖的贵族富人,因此政府在金币上做手脚遇到的阻力比较大,成色和重量就降低的最慢。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7][/align]
到了拜占庭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罗马后期和拜占庭前期的主要对手是东方的波斯萨珊王朝。萨珊以银为主要货币,拜占庭的白银因为岁供贸易等原因,大量东流。可能拜占庭银矿产量也不大,总之流传下来的拜占庭银币银币似乎比金币还少。缺银了,金币参与日常流通的机会就多了。它在拜占庭时期的变化就加快了。
索利多金币在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56年)时开始出现减重现象。查士丁尼是一代雄主,东方大败萨珊,西方夺回了意大利本土,使拜占庭的疆域达到了最大。但打仗是要花钱的,查士丁尼在首都也大兴土木,财政不紧张才怪,此时金币减重似乎也是大势使然。
到了公元960多年,福鲁斯二世在位期间,拜占庭金币减重更甚,形制上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薄片型的希斯塔梅隆金币。个人觉得这种改变适应了快速流通的需要。首先分割方便了,其次可以更有效的防止减边?感觉查士丁尼以后的金币经常被剪边,导致比标准重量轻0.2-0.5克。希斯塔梅隆金币钱体变大了,中心图案占的比例就大,剪边就更容易被看出来。
在此后的100来年,厚型足重的索利多金币逐渐消失了。希斯塔梅隆金币很快又演变成一面凹一面凸的碟型金币。这种币打制工艺要复杂一些,因为币胚要先要打成碟型,然后才能用印花。拜占庭金币为什么从平面的演化为碟型的至今是个谜。怀疑也跟防止偷金有关系,偷金的人在剪边以后可以锤打边缘以掩盖。弧线型的币身不易锤碟延展,减边就容易被发现。
希斯塔梅隆金币成色远不如奥雷金币和索利多稳定,成色不断降低,个人觉得跟更广泛的参与日常支付有关。货币一旦被平民使用,政府就可以比较顺利的降低成色以牟利。而且拜占庭后期国衰多难,银币铜币利润太小,也别无良策了。
第一枚为拜占庭/迈克尔七世/希斯塔梅隆碟型金币
面:绕光环的耶稣头像
背:皇帝持拉布兰和十字架
公元1071-1078年发行, 重4.43g,直径26.33mm-27.88mm,厚2.4mm,这种币成色约为80%左右,比索里多金币低,容易产生一种橘红色的包浆。
希斯塔梅隆碟型金币图案多有弱打,且币身容易变形,凸面容易磨损,因此好品的难找。
第二枚是清理过包浆的迈克尔七世金币,经过NGC评级为极美: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8]
[attachment=11328729][/align]
[/size][/td][/tr][/table][/color]
[url]http://m.paipai.fm/r5888251_u3331904/[/url]
【欧洲。教皇】罗马教皇——集权势与财富于一身
[url]http://m.paipai.fm/r5885858_u3331904/[/url]
【欧洲。罗马帝国 历史篇】见证一个腐败和黩武的文明
[url]http://m.paipai.fm/r5887630_u3331904/[/url]
【欧洲。罗马帝国 军事篇】罗马军团
[url]http://m.paipai.fm/r5885859_u3331904/[/url]
【欧洲。罗马帝国 文化生活篇】罗马人的幸福生活[/color][/size]
[table=80%][tr][td][color=#ff0000][size=2][b]罗马人的幸福生活[/b][/size][/color]
[size=2]货币单位[/size]
[size=2]食品供应[/size]
[size=2]供水[/size]
[size=2]排水[/size]
[size=2]厕所[/size]
[size=2]澡堂[/size]
[size=2]住宅[/size]
[size=2]街道[/size]
[size=2]饮食[/size]
[size=2]服饰[/size]
[size=2]儿童(学校教育)[/size]
[size=2]房 事[/size]
[size=2]赛车[/size]
[size=2]剧院[/size]
[size=2]大竞技场[/size]
[/td][td][color=#ff0000][size=2][b]1楼[/b][/size][/color]
[size=2]1。古罗马币介绍 补充[/size]
[size=2]2。古罗马的烹调宴饮[/size]
[size=2]3。罗马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size]
[size=2]4。罗马戏剧与剧场[/size]
[/td][/tr][tr][td][color=#ff0000][size=2][b]古罗马币介绍[/b][/size][/color][/td][td][color=#ff0000][size=2][b]2楼[/b][/size][/color]
[size=2]1。古罗马的文学艺术----诗歌[/size]
[size=2]2。古罗马帝国的行省管理[/size]
[/td][/tr][/table]
[color=#669900][table=90%][tr][td][size=2]
[b][size=3][color=#000000]罗马人的幸福生活[/color][/size][/b]
[color=#666666]本文翻译自
《The Ancient City - Life in Classical Athens & Rome》作者 Peter Connolly,Hazel Dodge
[ 转自铁血社区 [url]http://bbs.tiexue.net/[/url] ]
《Panorama of the Classical World》作者 Nigel Spivery,Michael Squire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Romans》作者 Harold Whetstone Johnston1[/color]
[color=#ff3366]1、罗马的货币单位[/color]
1奥里斯(aureus)= 25 第纳瑞斯(denarius)= 100 塞斯特瑞斯(sesterces)= 400 阿斯(as)= 1600 夸德伦斯(quadrans).
帝国时期城市内非技术个人的日工资约为1第纳瑞斯,在1世纪为3.8-4克的银币。庞培城出土的一份客栈帐单显示:升葡萄酒加面包-1阿斯其它食品-2阿斯 喂骡子的干草-2阿斯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0][/align]
大约在前6世纪罗马人就修建了城墙,但在前5世纪的某个时候,因为对外战争失败,罗马人被迫把城墙拆除。没了城墙的后果就是,390BC高卢人轻易地攻陷罗马,烧杀一空。高卢人撤走后,罗马人马上重建了塞维安墙(Servian Wall,下图中间那一圈城墙),塞维安墙长11公里,平均厚度3.6米,城门超过12个。
塞维安墙成功地挡住了汉尼拔,此后数百年,罗马的城区慢慢扩到城墙之外,但这时再无外敌能威胁到罗马城,所以一直没有修新城墙。到了3世纪,帝国开始衰落,北方蛮族的威胁日益严重,AD270皇帝奥勒良用三年时间修建了奥勒良墙(Aurelian Wall,上图外面的一圈),墙长20公里,有18个城门和381座塔楼。
就在奥勒良上台的前几年,罗马经历了一场大瘟疫,人口只剩下50万,所以奥勒良墙很可能无法体现出罗马城在鼎盛时期的规模。此后在戴克里先时代,人口又恢复到近百万,但总的来说罗马的地位和人口一直在下降,西罗马灭亡后,5世纪末的罗马大概只有5万居民,AD550剩下了2万5。罗马人在建城之初的几百年,显然没有想到子孙们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城的人口会超过一百万。因此在建设时毫无长远计划,只是简单地由中心向外扩展。到了帝国时期,皇帝们想要好好规划一番时,已经太迟了,市区里挤满了杂乱无章的建筑,要造个规模大点的皇宫都没地方。AD64的那次大火后,才烧出了大片空地,于是尼禄的皇宫,后来的大竞技场、大澡堂都陆续建了起来。不管大火是不是尼录放的,他为灾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私人金库里掏钱清理废墟,安置灾民。尼录还制定了各项法规,保证街道宽度和建筑的可靠性。不过在AD69 争夺罗马城的内战中,又窄又滑的街道给军团的前进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说明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善。到了3世纪末,罗马城共有11个大澡堂、超过1000个喷泉、两个赛车场、两个大竞技场、36座凯旋门和2000所豪宅。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1]
[color=#666666]拥挤的市中心汉化交流空间[/color][/align]
共和时期罗马城有4个区,7BC奥古斯都扩大到十四个区(Region),以罗马数字命名,区长由政府官员担任。每个区又分为更小的街区(vici),只有各街区的主路才有路名和路牌,不在主路上的居民只能自己想法标出房子的位置。例如:某某神龛东边的第五栋房子;某某面包店往下两个门。街区是罗马城最小的行政区划,有自己的神龛、祭坛、活动中心和标志建筑。每年街区内居民选出一到四位街道主任(magistri vici),负责治安、防火、祭祀本街区的守护神、与上级官员联络等 AD6奥古斯都用释放奴隶组成了7个消防大队(vigiles),每个大队负责两个区的巡夜和消防。为了提供这7000人的开销,奥古斯都加征了奴隶买卖税,征收奴隶价格的4%。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2][/align]
帝国后期的罗马城布局,右上角城墙边的是禁卫军营,
[color=#ff3366]2.食品供应 [/color]
由于罗马只统计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所以罗马城有多少人口从没有确切的数字。现代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在2世纪,罗马城人口大约为120万。在古代,供应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是巨大的挑战。罗马城消耗的物资,来自整个地中海区域,各种物资中运量最大的是食品。食品中又以谷物、葡萄酒和橄榄油为主。谷物来自埃及和北非,葡萄酒从坎帕尼亚、高卢和西班牙进口,橄榄油主要来自南西班牙和北非。
帝国时期海运、河运和陆地运输的成本大约是1 : 5 : 30。在奥古斯都时期,埃及每年要向罗马输送1亿8千万公升小麦,1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则宣称阿非利加省的输送量是埃及的两倍,这样大的运输量只能依靠海运。葡萄酒和橄榄油装在双耳瓦罐(amphorae)内,先运到台伯河口,转到小型驳船上,沿台伯河运达罗马城内的河码头。所有的瓦罐在码头上倒空,酒和油储存在一个个巨大的仓库内,大部分空瓦罐直接扔掉。就在台伯河码头旁,有一座人造的小山Monte Testaccio,高34米,周长1公里,就是由丢弃橄榄油瓦罐的碎片堆成。据估算堆成这样一个小山包至少需要五千三百万个瓦罐。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3] [/align]
[align=center][color=#666666]产自地中海各地的瓦罐 [/color][/align]
从共和国后期开始,罗马城内的贫民(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得到低于市场价一半的粮食,58BC后完全免费。奥古斯都将其固定成了一种救济制度。在5BC,有32万个成年男子领取救济,每月发一次供应证,但每个人能领多少及如何发放,没有可靠的资料。我们所知的就是在图拉真时代,不再是每月发一次小麦,而是每天发面包。(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说法,每天每份是3磅面包或可以买3磅面包的钱。不过吉本没有提及数字来源). 从海外运粮的工作由签了合同的私人承包商负责,由于罗马附近没有天然良港,台伯河口的Ostia港也淤积了,无法停靠那些载重量几百吨的海船。在共和国时期运粮船先停在那不勒斯湾的Puteoli港。粮食换乘较小的船只,沿海岸北上到达Ostia港,再换成1百吨以下的河船运到罗马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4] [/align]
这种运输方式效率太低,无法满足罗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1世纪中期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在Ostia港北面3公里,建了一个人工海港Portus。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两条大型防波堤围成一个港湾,在南防波堤的尽头是一座以亚历山大灯塔为原型的灯塔。为了加固灯塔的地基,一艘载重量约1300吨的巨轮被灌满混凝土,沉入海中。新港可以停靠大型海船,但仍会受天气影响,AD62的一次大风暴破坏了港内的200条船。2世纪初,图拉真在海岸后挖了一个六角型的大池子,深5米,面积32公顷,同时挖了一条40米宽的运河直通台伯河。从此罗马城才算有了一个可以全天候、24小时使用的外港。
[color=#ff3366]3.供水[/color]
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的居民还是使用井水、泉水和蓄水池里的雨水。在312BC,罗马人开始修建第一条高架引水渠,到了2世纪初的图拉真时代,罗马人的供水已经完全依靠10条主要的引水渠。19BC,阿格里帕(Agrippa)修建了Aqua Virgo,为他新建的大型公共浴室供水。这是第一条专门用途的引水渠。到了2BC,奥古斯都又建了一条引水渠Aqua Alsietina,专用于为台伯河西岸的一个人工湖供水。这个人工湖主要用来进行海战演习和庆典表演。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5] [/align]
量最大的引水渠是Aqua Claudia和Aqua Anio Novus,完成于AD52,它们实际上共用一个高架。如上图,上层是Aqua Anio Novus, 源自Anio河的河水;下层是Aqua Claudia,源自Anio山谷的泉水。对所有的公共建筑,罗马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引水渠,他们认为埃及人、希腊人建的那些金字塔、陵墓和巨像虽然壮观,但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6] [/align]
水引进城市后,先流入蓄水池,池底的管道为公共设施供水-喷泉、澡堂等等,水池壁上的管道为私人供水,这样的设计保证了在水短缺时,私人用水会被首先切断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7] [/align]
上面是供水管(罗马人的供水管都是铅制品)和下水道的截面图,分支水管直接通到住宅。但大部分的平民住宅没有这样的自来水,必须要去附近的公共喷泉提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8] [/align]
图中就是一个小型的公共喷泉,这张图还体现了罗马城的另外一个特点:住宅楼之间的间隔很小,这个以后再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79][/align]
从3世纪开始,引水渠的水被用来推动水磨,为罗马城提供大量面粉。这是公元4世纪法国南部的水磨,水流被分为两股,共16个直径2米的水轮,每天能生产27吨面粉。
[color=#ff3366]4排水 [/color]
罗马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下水道系统, 各个区域都有它们的主下水道,分别流进台伯河。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Cloaca Maxima(见下图),长900多米,高4.2米,宽3.2米,现在还在部分使用。33BC阿格里帕曾亲自坐着小船,进下水道里视察。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0] [/align]
支线下水道通常建在道路下面,接受来自澡堂、街道和民宅的废水,公共喷泉里溢出的水直接流进下水道,冲刷里面的废物。实际上很少有住宅连到公共下水道,民宅里的废水都流到一个封闭的污水坑里,屋主花钱请人定期来清理,囤积下来的残渣可以卖作肥料。罗马的下水道缺乏阻挡沼气和臭气外泄的过滤装置,而且由于建得太低,台伯河涨水时河水会倒灌进去。
[color=#ff3366]5.厕所 [/color]
据帝国后期的记载,罗马城的公厕有144个,都建在公共澡堂旁边,便于使用澡堂里流出的脏水冲洗。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1] [/align]
这是一座大型公厕的复原图,大概有100个座位。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下水道,座位前用来洗手的水沟,还有罗马人的厕筹-海绵棒(sponge stick)。海绵棒用后就放入中间的水槽。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2] [/align]
现存于Ostia城的公厕,25个座位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私厕,用厨房的脏水冲,污水流进公共下水道或住宅的污水坑。对海格里尼姆城(Herculaneum)的发掘表明,所有的住宅,甚至位于2楼的公寓,都配有厕所。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3] [/align]
海格里尼姆在79AD和著名的庞贝城一起,被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淹没
[color=#ff3366]6.澡堂[/color]
公共澡堂对于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洗澡的地方,还起着社交中心的作用。所以一个完善的公共澡堂,必须配有图书馆、会客室、健身室、餐馆、商店和花园。在33BC罗马城有170个澡堂,5世纪初,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56,其中包括11个大型皇家澡堂(由皇帝自己掏腰包兴建的公共澡堂,并冠以皇帝的名字)。最大的是戴克里先大澡堂,容量3000人。公共澡堂都是由富人捐款修建,作为社会公益,所以收费很低,通常男性收费1quadrans,女性加倍,儿童免费,当然毛巾和香油要自备。(quadrans是罗马最小的硬币,等于1/64第纳瑞斯)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4] [/align]
上图大竞技场(Colosseum)后面这个宫殿般的建筑,是图拉真大澡堂,AD104开始兴建,五年后对外开放。由于角度的关系,澡堂看起来象长方形,其实是近似正方形。从花园的外围建筑算起是340 X 330米,花园里面的主体是190 X 212米,大竞技场也不过188 X 156米。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5] [/align]
这是澡堂前半部分的剖视图,从左到右是大门、露天的冷水浴池、冷室(frigidarium)、温室(tepidarium)、热室(caldarium)。洗澡的过程是先进更衣室,脱下衣服,涂上香油,到练习室运动一会,然后进入温室,在温水池里泡泡。再进入热室,坐在椅子上熏蒸汽,再泡在热水池里,由自己或仆人动手,用金属刮板把全身刮一遍。最后到冷室,跳进冷水池,这才算完成一次标准的罗马式蒸汽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6] [/align]
这是热室内部,可以看到各个热水浴池,下面的火炉和通道。罗马人的热水器主要有两种,下面是这两种的截面图。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7] [/align]
图的上半部是普通民宅用的热水器,公共澡堂用的是第二种。浴池和水箱是连通的,箭头B显示热水上升流进浴池,箭头A显示冷水下沉流回水箱,被再次加热。浴室地板下方是空心的,火炉产生的热气从地板下流过,墙壁内有一排瓦制的管子(见下图),热气沿着管子上升直到屋顶,排出屋外。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8][/align]
这样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得到了加热,将整间屋子变成蒸汽浴室。从上图可以看出地板比墙壁厚得多,免得地板太热,烫脚。罗马人显然知道利用温室效应,温室和热室都开有巨大的窗户,装上双层玻璃
[color=#ff3366]7.住宅[/color]
奥古斯都宣称:“我接手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一座大理石造的罗马城。”他是在吹牛,大理石通常只用来建造豪华住宅、公共建筑的柱子,及在墙上贴一层大理石砖。罗马城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灰石、火山岩、烧制的砖和混凝土罗马的混凝土(opus caementicium)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与现代混凝土不同,它是用火山灰制成的泥浆、碎石或砖混合搅拌而成,按古代的标准算是相当牢靠,而且可以用在水下。当建造拱顶时,混凝土里不放普通的石灰石,而用火山浮石,火山浮石里面有许多空泡,可以大大减轻房子上部的重量。以前,罗马城用的白色大理石全部进口自希腊,彩色大理石来自北非和爱琴海。35BC以后,罗马人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开采白色大理石,奥古斯都能够建造大理石的罗马,建材的本土化降低了运输成本是原因之一。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89] [/align]
上图是罗马房屋的地基,先用木板围上,再一层层地浇上混凝土。地基打好后木架子通常就留在原处。墙的样式主要有三种: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0] [/align]
左起Opus incertum:最早的样式,混凝土表面砌上一层经过粗略磨制的石块。
Opus reticulatum: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后期,混凝土表面砌着同样大小,金字塔状的石子。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1] [/align]
世纪中期起广泛应用,混凝土外面砌上砖。罗马城进入繁荣时期后,面临着于现代大城市一样的问题-人多地少,它的解决办法也和现代人一样,向高处发展。至迟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就出现了两层以上的公寓楼,而且不断加高,三层、四层甚至五、六层的公寓楼陆续出现。住这些公寓的都是穷人,为了降低成本,屋主不但往高里盖,楼与楼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小。很多街道只能过一辆车,有些地方窄到楼上凸出的阳台几乎能碰上对面的公寓楼。 情况越来越恶化,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政府发布命令,公寓楼不得高于21米(六层)。在AD64的罗马大火后,限制降到18米,楼间距不得小于3米。
最初高层公寓楼的建材是Opus craticum(上图),木质框架里灌上碎石和泥浆。这种结构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砌砖头,便宜;最大的坏处是不防火。AD64那场大火据说烧掉近半个个罗马,与这种木质框架颇有关系。大火之后,砖结构成为公寓楼的主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2] [/align]
在罗马城内,富人住的是带花园庭院的平房,穷人只能住公寓。上面是一栋五层公寓楼(insula)的结构图,一楼靠街的屋子都是商铺,其余的住人。楼中间是天井,给中间的屋子提供光照。一楼和二楼有公厕,各有九到十个位子。这样一个公寓大概住40人,根据4世纪中期的普查,罗马城有46602栋房子,大部分是这样的公寓楼。
[color=#ff3366]8.街道 [/color]
在罗马城内,除了几条主路外,居民区内的道路都十分狭窄。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3] [/align]
城内最宽的大路,凯旋式就走这条路。由于街道狭窄和楼上住户直接向楼下倒垃圾,路上行人被砸到的事经常发生。为此罗马人专门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这种受害者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凯撒统治时期,发布了命令,屋主必须清理自己房屋前的区域。还命令营造官(aedile)组织一批人清扫街道。街道狭窄和缺乏人行道还使交通事故频发,凯撒曾下令,除了政府拥有的,所有轮式车辆不得在白天进入罗马城。即使没了车辆,街道仍是拥挤不堪,于是有了第二道命令:禁止在街上摆摊。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4] [/align]
狭窄的街道,房屋外突出的拱廊是为了方便消防队员。与庞培城不同,罗马的街道两边大都没有专门的人行道。
[color=#ff3366]9.饮食 [/color]
有钱人的厨师通常由奴隶充当,穷人的房子则经常没有厨房,所以罗马人的厨房不受重视,远不象现代那样卫生整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5] [/align]
上图是1世纪普通的罗马厨房,炉子下面放柴火、木炭,煮东西都在炉子上面。至今为止,没发现罗马人有在厨房里装烟囱(希腊人的厨房大都有烟囱),厨房的通风靠窗户。为了便于使用供水排水系统,厕所经常与厨房挨得很近,或者干脆装在厨房里。就象上图,炉子旁就是马桶。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6] [/align]
罗马人的烹调方式主要有两种,要么如A,罐子放在三角架上煮;要么将食物放在烧烤架C上烤。即使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厨房,很多住公寓的罗马人也没有,他们必须要下馆子。罗马城里有大量的面包房、酒馆、饭馆,主要顾客都是穷人。面包是罗马人的主食,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一直到174BC,罗马城里都没有面包房。大家都在自己家里做面包。老普林尼还提到了罗马人常吃的面包根据不同的形状和口味,有很多种。面粉如不做成面包,也可以加水煮成类似麦片粥的食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7] [/align]
这是一个面包作坊,磨面粉、和面、烘焙和销售一条龙。罗马人的口味很重,食物经常配有大量的调味品,辛辣和酸甜味的最受欢迎。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放胡椒,连烤小甜饼时都用。调味品中最重要的是盐,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以低价销售;醋由葡萄酿造;罗马人没有糖,用蜂蜜来提供甜味。除了面包作为主食外,蔬菜、水果和肉类也是必不可少的。本土的橄榄、葡萄、苹果、梨、李子,从外面引进的胡桃、杏、桃子、樱桃、石榴和柠檬,在前一世纪,意大利已是遍地果园。蔬菜方面除了西红柿和马铃薯,现代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大都有。
海格里尼姆城壁画上的桃子,这幅画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倒不在桃子,而是旁边的玻璃瓶,说明当时的玻璃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肉类吃得最多的是猪肉,穷人则多吃山羊肉。牛肉属于奢侈品,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只有在祭祀后,才能吃上祭祀用的牛肉,而且内脏要先分给祭司。野味的需求也很大,象鹌鹑、野兔、鹿肉、野猪和雉,最贵的是孔雀,一只至少50第纳瑞斯。家禽如鸡、鸭、鹅和鸽子,水产如鱼、牡蛎、蚌,也吃得不少。
水、奶(羊奶牛奶)和葡萄酒是罗马人的三大饮料。喝葡萄酒时通常要掺上几倍的水,喝纯葡萄酒被认为是蛮族的行为
那些家里有专门饭厅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是半卧着用餐的,上图就是一个小型的晚餐聚会。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8] [/align]
如果空间够大,则摆设如上图,中间的空地摆一张大桌子。用餐者左侧身半卧,左肘撑在榻上。左边的卧榻lectus imus 是主人的位置。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699] [/align]
妇女坐在丈夫的榻旁用餐,小孩则坐在椅子上。
[color=#ff3366]10.衣服 [/color]
罗马人的服装与希腊人的非常类似,没有内裤,束腰外衣(tunic)是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的基本装束。束腰外衣很简单,就是前后俩块方形的羊毛布,在肩部缝上,腰上系根带子,肩膀两侧的布下垂,就形成袖子,有些人会缝上长袖。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0] [/align]
如上图A,劳动人民的外衣一般不过膝,有钱人就长的多。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在外衣上加件外袍(toga),见上图C,但这种外袍比较笨重,有闲阶级才会穿着。高级官员和元老可以穿镶紫边的外袍。请注意上图的B和C,花边是染在tunic,而不是在toga上,说明他们有身份,但还没有达到元老的级别。E是士兵和工人穿的凉鞋(hobnailed sandal),F是靴子。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1] [/align]
这是元老穿的外袍 一直到2世纪初,罗马人都不流行蓄须,后来在哈德良提倡下,才兴起希腊式和亚洲式的胡子。由于罗马的剃刀不锋利,刮胡需要高度的技巧,一个擅长刮胡的奴隶能卖到很高的价钱。人们很少自己刮胡子,而是去理发店,普通罗马人早上出门的第一件事通常是去理发店刮脸(据记载小西庇阿是第一个每天刮脸的罗马人),所以理发店总是人头拥挤,成为市井传言的集散地,理发师用各种软膏(dropax)来剃头刮胡。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2] [/align]
马妇女穿的束腰外衣(stola)很长,通常在胸部下面加系一条带子,以凸出XX,如上图左。上图右的妇女披着长围巾(palla)。除了妓女和犯了通奸罪的女人,罗马妇女不穿toga。妇女一般有穿短内衣(但一样没有内裤)和strophium(软皮革制,起胸罩的作用),见下图。
[align=center] [attachment=11328703]
[color=#666666]女用凉鞋和软皮鞋[/color] [/align]
[color=#ff3366]11.儿童 [/color]
在罗马的所有阶层,婴幼儿死亡率都是很高的。活下来的与现代儿童一样,玩耍和上学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4]
[color=#666666]这是一辆由山羊拉的玩具车 [/color][/align]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5]
[color=#666666]石制棋盘[/color] [/align]
罗马的[color=#ff3366]学校[/color]分三级:初级学校(Primary school),语法学校(Grammar school),技巧学校(Rhetoric School)。只有出身富裕的儿童才能完成二、三级教育。初级学校都是民办的,但政府会提供场地。接受7岁以上的男女孩,教读写和数学。只有出身下层的孩子才会进初级学校。有条件的家庭会请家庭教师给孩子进行初级教育,更富有的家庭则干脆买一个有文化的希腊奴隶当家教记载表明,大部分教师都是奴隶或释放奴隶,工资非常低,有一个著名的语法学家阿普利乌斯任教于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年薪100第纳瑞斯。到了十一岁左右,有条件的孩子可以进入下一级的语法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法,以及音乐与几何,其他孩子开始打工,进入社会。十五岁后可以进入技巧学校,学习演说和写作的技巧。在课堂上,老师会要求学生们想象一个历史场景,例如,作为即将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你将如何对士兵们进行鼓动演说?上完课由学生们自己评判,谁的演讲最有力。技巧学校毕业后,有条件的年轻人会去希腊留学一两年,到雅典、罗德斯岛或小亚细亚,生活在希腊人中间,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6] [/align]
罗马人的书写工具,A 墨水盒 B 芦管笔 C 青铜笔(笔头和现代的钢笔差不多)
生用的书写板和笔。书写板是木制,表面涂蜡,用笔的尖头在蜡上书写,笔尾部是平的,作用同橡皮。
在14-19岁之间一个适当的日子,通常在每年的3月17日,罗马的少年可以到神庙举行他的成人礼,换上成人的toga,然后上统计部门登记注册,从此就算一个完全的公民了。
[color=#ff3366]12.房 事[/color]
罗马人生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是模仿希腊,但在性关系上,有两点主要不同。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color=#ff3366]男同性恋很流行[/color],被认为是青少年成长的必经之路。罗马就没有这个风俗,同性恋受到歧视。恺撒年轻时有过同性恋的嫌疑,此后一辈子恺撒的政敌都以此攻击他;安东尼也曾指责屋大维与恺撒搞不正当关系。帝国时期男同性恋现象有所增加,但仍不被主流社会接受。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7] [/align]
古希腊的男恋人们在亲热汉化交流空间。另一点不同是罗马人性行为的半公开化。前4世纪,一个希腊作家访问了意大利中部的伊特拉斯坎,对当地人如此评价:他们的性关系混乱,不分时间地点地乱搞,如果一个人走进一间房子,经常能看到屋里的人在毫不感到羞耻地进行某些行为。' 罗马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相当开放。当然开放归开放,有些事还是不能看,有些话还是不能说。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AD8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公开罪名是写淫秽诗篇,但舆论普遍认为奥维德获罪,是因为他看到了奥古斯都外孙女的某些私人行为,而且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8] [/align]
罗马的风铃,作为吉祥物公开挂在住宅和商店的门口。罗马人认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能带来好运,因此在大门、客厅和护身符上都经常刻有此类形状的东西。在庞培城废墟里发现了大量壁画,卧室里的壁画大都是下面这个类型。
壁画上的姿势千姿百态,最常用的还是女上 位,因此欧洲人有时把女上位成为罗马式。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09] [/align]
庞培城的一所澡堂的壁画,右起:女上位、侧后位、女对男口交、男对女口交。罗马城的妓院数量没有统计,但1万2千人口的庞培城有34所妓院,从高档到低档为各层次的顾客服务。其中一所为穷人和奴隶服务的妓院有10间房,分两层。墙上的广告上标明,一次口交服务只需几个阿斯
[color=#ff3366]13.赛车 [/color]
看过《宾虚》的人对罗马的赛车都会有深刻的印象,罗马城的赛车场好几处,最宏伟著名的是大赛车场Circus Maximus。大赛车场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后来不断扩建,最后图拉真将它建到了最大规模,全长600米,宽200米,最大容量估计可达200000人。赛车手要绕着赛场的中心岛(长344米),逆时针跑7圈,近6公里。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0] [/align]
公元4世纪初图片底部是13个拱门carceres,这里是赛车的出发点,最多可以12辆赛车同场竞技(中间的门不用)。请注意中心岛中央最高的花岗岩方尖碑(高24米),这是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所建(公元前13世纪),10BC奥古斯都把它运到了罗马。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1] [/align]
这是起跑门,门外插着插销,插销上连着绳子,经过一个滑轮,通向门上方。比赛开始后,操作员拉起开关,触发扭力弹簧,所有起跑门上的插销都被同时拉开。(注意到门两边的雕像了吗?)
门轴上也装着扭力弹簧,插销打开后,两扇门向外弹开,赛车冲出。 在帝国时代,赛车已经变得非常专业化。所有的车手都属于车队,每个车队都有自己的颜色,从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城内通常有四个车队:白色的Albata;红色的Russata;蓝色的Veneta;绿色的Prasina(后来在图密善时又加了两支:金色和紫色)。每个车队都是一个经济实体,化巨资进口马匹,有自己的训练员、铁匠、兽医和马夫。政府或私人请车队出赛都要付出场费。皇帝们都有自己支持的车队,例如伟大的卡里古拉就支持绿队,经常在绿队的马房里吃饭过夜。与角斗士一样,赛车手都出身社会下层,或是奴隶和释放奴隶(freedman)。同样与角斗士一样,胜利者将成为万众崇拜的偶像,有不少奴隶靠比赛的奖金为自己买得了自由。一个西班牙赛车手Diocles在24年内参加了4257场比赛,赢得1462场,总奖金9百万第纳斯。现存的最高胜利记录是Pompeius Muscosus的3559场。同时赛车手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车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据记载有一个赛车明星Scorpus,在赢得2048场胜利后,于27岁撞车身亡。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2] [/align]
在绿色车手后面的红架子上有七颗金蛋,车手每跑完一圈,金蛋就放倒一颗,赛道的另一端有七个金色海豚,起同样作用。比赛日开始,车手们列队进入赛场,观众开始欢呼和下注。一声号角后,主持比赛的官员扔出手里的餐巾,比赛正式开始。一个完整的赛日有24场赛马,赛马日之外,赛车场里也会有一些新奇的表演。例如十匹马拉的赛车、马术、赛跑和接力。赛日最后是给胜利者发奖-象征胜利的棕榈叶、花冠和金链子
[color=#ff3366]14.剧院 [/color]
Colosseum经常被译成圆形大剧场,其实它不是演戏的剧场,罗马人的剧场也不是圆形的。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3] [/align]
罗马人的剧场与希腊人的一样都是半圆形,上图是两个剧场,上面的是马尔塞鲁斯剧场(Theatre of Marcellus),是奥古斯都为了纪念死于23BC的外甥和女婿马尔塞鲁斯修建的,直径150米,座14000。下面的是Theatre of Balbus。戏剧是罗马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碰上公办私办的庆典都要大演几天甚至一二十天。但在共和时期,元老院禁止在罗马城修建永久剧场,认为天天看戏会使公民们颓废。所有的剧场都是临时搭建的木结构,庆典后拆除。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自然史》里描述了58BC的一个豪华临时剧场,舞台后的布景有三层,共360个柱子,第一层是铺大理石,第二层铺玻璃,第三层镀金的木板。整个剧场的装饰用了3千个雕像,可以容纳8万人。
55BC庞培修建了罗马城的第一个永久剧场(上图),直径160米,27000个座位,剧场后还附带了一个大花园。为了绕过元老院的禁令,庞培宣称这是献给维纳斯女神的(据说这个剧场是庞培的老婆、凯撒的女儿朱莉亚提议修建的,她还亲自参与了设计。由于罗马人都认为凯撒出身的朱利乌斯家族是维纳斯的后裔,所以庞培提出了这样一个建剧院的借口)。
剧场的弧边是阶梯状排列的座位,直边是舞台、背景建筑和后台。戏剧中演员的服装基本上和现实生活中一样,标准服饰是束腰外衣加一件袍子。由于一个演员常常要在一部戏里演不同的角色,面具是必备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4] [/align]
悲剧里英雄和女英雄的面具
喜剧用的面具:左起,老人、年轻人和奴隶古希腊流行的戏剧主要是悲剧和喜剧,流传下来的剧本都是些有深刻内涵的作品。罗马人的戏剧要大众化的多,除了从希腊人那学来的喜剧和悲剧,平民化的闹剧、滑稽剧、哑剧和歌舞剧都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公元前1世纪,大批无业贫民涌进罗马后,完全改变了罗马观众的口味,戏剧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粗俗化。哑剧(Pantomime)是最有罗马特色的剧种,戴面具的演员们用舞蹈和各种动作来演绎剧情,合唱团和乐队伴奏。高雅的希腊人不承认这是戏剧,称其为“Italian dance”,丝毫不顾哑剧是由两个希腊人首创的事实。
[color=#ff3366]15.大竞技场 [/color]
早期罗马人相信,人的鲜血能抚慰死者的灵魂。于是他们在葬礼上杀战俘和奴隶献祭,后来演变为葬礼上的角斗表演,再后来角斗成了一项纯粹的娱乐。角斗表演分三种:猎兽(venationes);用野兽处决犯人;角斗士的格斗表演。前两种总是以一方的死亡告终,后一种则不一定要打到死。在一个演出日,通常上午是猎兽表演,午饭时间处决犯人,下午角斗士表演。在专门的竞技场修建以前,角斗表演经常在赛车场、广场(Forum)和临时搭盖的木头剧场举行。罗马城内最早的石头竞技场建于奥古斯都时代。AD67犹太人起兵反抗罗马,尼禄派韦伯芗平叛,最后在AD70韦伯芗的儿子提图斯攻陷耶路撒冷,洗劫并烧毁了所罗门神庙。这时已是皇帝的韦伯芗决定用从犹太人那抢来的财富修一座大竞技场,AD79韦伯芗病死,提图斯继任,并在AD80主持了这座宏伟建筑的落成仪式,庆典举行了100天,最盛时一天杀了5000只野兽。八卦:尼禄统治时期,在东方各行省盛传一个预言,一个从犹太土地上走出的人将统治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很可能是***徒编的,但犹太人信以为真,于是起兵造反,以为能够推翻罗马的统治。赋闲在家的韦伯芗被授予大军,前往巴勒斯坦,并依靠这支军队在AD69赢得罗马内战,当上罗马帝国的皇帝,预言应验了。这真是典型的蝴蝶效应,一个谣言最终导致了犹太人流落四方,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东。对罗马人来说,本没有希望的韦伯芗当上皇帝,改变了帝国的走向,并给后人留下了大竞技场和无穷的话题。大竞技场为椭圆形,188 X 156米,高45米,地基是厚12米的混凝土,地基上的80根石灰岩承重墩构成主体框架。墙的建材是混凝土外砌方砖或火山浮岩。
这是根据古罗马工程师Vitruvius的描述绘制的滑轮组起重机,用了两个定滑轮和一个动滑轮。有古籍宣称这种起重机是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发明的。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5] [/align]
座位区分为好几层,最下层(Level 1)的是元老席,从C点进入,只要爬一小段台阶。最上层(Level 5)座位是木制的,总共得爬138级台阶。从奥古斯都时代起,所有剧院马场的坐席都划分为不同区域留给不同阶层的观众,这是奥古斯都重建社会秩序计划的一部分。最下层最靠近演出区的位置永远是留给元老和高级官员的,社会地位越低,座位越靠上,妇女的位子在最上方(神庙的童贞女可以坐在元老席)。在座位的上方可以看到一根根木桅杆,这不是旗杆,而是用来系绳索和巨大的帆布遮阳篷。总共有240根桅杆,需要1000人来收起和拉上遮阳篷。汉
观众席的入口,除最高层外座位都是大理石,高44厘米,宽61厘米。总共有45000到55000个座位。
上图为场地中央,在元老席上有个包厢,是皇帝的专座。场地下另有一番天地。
场地上有大量的活门和升降梯,由绞盘操作。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6] [/align]
猛兽的笼子和出入的通道。在右上角可以看到元老席的台阶很宽,可以放下椅子,不用坐在冰冷的大理石上。
上图的猎手如果披上红袍,那只身上插着两根标熗的豹子换成公牛,就和现代的斗牛士差不了多少。但实际上,古罗马猎兽表演中的猎手(venatores)即使在角斗士眼中,也是卑贱的。他们不穿铠甲,只穿短外衣或裸体。
一个犯人被绑在小车上,推向一只猛兽,不少早期犯法的基督徒就是如此处决的。下面是被铁链栓在一起的熊和公牛,以确保它们不会临阵脱逃。最初的角斗士来源于被判死刑的战俘和奴隶,到了帝国时期,自愿参加的自由民和被宣判有罪的犯人也可以加入。2世纪中哈德良皇帝曾禁止角斗表演,几十年后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就是电影《角斗士》开头那个老皇帝)把斗兽表演也禁了,不过这些皇帝一死禁令就撤销了。罗马的历史上共出现过大约20种角斗士,每一种都使用不同的装备,用不同的方式战斗,如高卢式、不列颠式(架着轻型战车),但具体细节流传下来的很少。角斗士一般不用本名,而是起一个响亮的艺名,用传说中的英雄如帕修斯(Perseus)、阿甲克斯(Ajax)等等,或者以自己的特长起名,如Ursius(如熊一般)、Callidromus(迅捷)。所以如果史书中提到一个高卢角斗士Deathclaw,那他不一定是个高卢人,更可能是一个高卢式的角斗士,艺名叫死亡爪。 八卦:基于角斗士的以上两个特点,澳大利亚一个写历史小说的女作家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所谓色雷斯人斯巴达克,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人,艺名叫斯巴达克,按色雷斯风格训练的角斗士。罗马人并不知道的他真实身份,以讹传讹,传到一二百年后的普鲁塔克和阿庇安手上,就成了色雷斯人斯巴达克。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7] [/align]
色雷斯式角斗士的头盔 B 萨姆耐特式头盔
最早的两种角斗士是萨姆耐特(Samnite)式和高卢式。这两个民族是罗马人早期的死敌,罗马人用他们的战斗方式来训练角斗士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萨姆耐特:最初的萨姆耐特角斗士是轻装,然后装备越来越重。带面罩、羽毛的头盔,左脚有高过膝盖的护胫甲,与军团士兵同样的塔盾和短剑。高卢:最初也是轻装,不带头盔,配长盾。到了共和后期,加上了不带面罩的头盔和六角长盾。色雷斯: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势力扩张到色雷斯,于是色雷斯式角斗士合乎清理地出现了。配小圆盾,弯刀,两脚都有长护胫甲。网民:Retiarius(Net man),最常见的角斗士,用渔民的渔网和三叉戟,加一把匕首。他的防护就是左臂上的腕甲和环甲,有时左肩上加个肩盾(galerus)。有些人认为按照字面意思,只有用剑的才算角斗士,因为英文中的角斗士(gladiator)一词源于拉丁文gladius,原意是短剑。
剑士(Secutor):装备军团式的塔盾(Scutum)和短剑,护臂环甲(Manica),由于在角斗场上剑士通常是与网民捉对厮杀,他的头盔上没有长帽檐,以免被网勾住(上图)。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9][/align]
上图左起,受伤的网民,鱼叉已被击落,正伸出手指向观众和裁判恳求结束战斗;剑士;两个不知道类型的重装角斗士;色雷斯角斗士拿着圆盾长矛;色雷斯人的对手,像是个萨姆耐特角斗士,盾牌掉在地上,向裁判伸出手指;裁判兼角斗士教练(lanista)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的角斗士学校,公办私办的都有。一个新入学的角斗士叫做Tiro,学校的教学方式基本与军团的新兵训练一致,或者应该说军团的训练方式与角斗士一致。 公元前2世纪末,执政官Publius Rutilius,从角斗士学校雇来一批教练(lanistae),用训练角斗士的方法来训练新兵,效果很好,这套方式迅速被推广(在《凯撒3》里,建角斗士学校能提高军团战斗力,就是这个道理)。Tiro只能使用木剑和柳条盾(木剑和盾都是加厚的,比真正的武器重),练习刺木桩。等他的动作完全规范后才能真刀真熗地与真人对打,这时他升格为armatura。角斗士通过全部训练后称为pali(stake木桩),再根据成绩分为Primi pali、Secundi pali和Tertii pali(第一木桩、第二木桩和第三木桩)三个等级。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18] [/align]
根据庞贝城壁画复原的角斗场景,剑士与网民正在搏斗,网民的网已撒出,但显然没有效果,他配有肩盾作为没有头盔的补偿。一旁是裁判拿着棍子,场地边是伴奏的管风琴乐队,后面的黑衣人是一个政府官员,打扮成Charon(罗马神话中冥界渡口的船夫),他负责用烙铁确认角斗士是否真的死了。然后尸体就从左边的小门拖走,地上的血迹则用沙子盖上。
[size=3][color=#000000][b]古罗马币介绍[/b][/color][/size]
中国史书使用“西域”这个词时有狭广意之分。狭义上指现在的新疆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了更远的中亚、西亚乃至丝绸之路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本贴就介绍下广义西域币里的古罗马币。
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人们眼里的西域充满神秘,张褰使西域十三年,最远到了安息(今伊朗一代),对大秦(罗马帝国)却汪洋兴叹,当地人说要坐船半年才能到达,现在看这话水分太大,很可能是因为安息与罗马为敌,且控制着丝路贸易,不愿意让汉朝与罗马直接沟通。
罗马城本是希腊世界的一个小的城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改为实行共和制,称共和国。其后开始扩张,公元前146年灭迦太基控制北非,公元前168年打败马其顿控制希腊半岛,后又东占叙利亚和埃及,北占高卢。随着军事扩张,其军事首领的权利日大,议会不得不退让。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议会冠以奥古斯都,有了类似于汉代的皇帝的权力,史家称为罗马帝国的开始。公元后的两百年间达到全胜,这是中国的东汉时期。
中国在经历了黄巾三国的内乱,和五胡十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终于稳定下来,在公元600多年进入了盛唐。在此期间,罗马的风云变换有过之而无不及,内部帝位纷争,皇帝死于谋杀者十有八九,外部有日耳曼等蛮族(当时的日耳曼人连文字都没有)的威胁和渗透,到了公元4世纪,戴克里先(Dioclitian)意识到罗马帝国的问题已经太多,一个人皇帝难以管理,建立了四主共治的制度,罗马帝国开始分裂。人心理上喜欢大,喜欢统一,喜欢稳定,但有时候只有分裂,变化才能生存。
君士坦丁一世登上皇位后,为了罗马的生存开始在东部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要地修建新都。330年新都建成,定名新罗马(Nova Roma),就是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死后,罗马帝国永久的分裂为两个国家。西罗马继续遭受日耳曼族的攻击和渗透,在公元486年其皇帝被日耳曼族的将领夺位,史家定为西罗马的覆灭。东罗马则经过变革而生存下来,加强了皇帝的权力,立基督为国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使罗马帝国延续了一千年,直到1453年亡于奥斯曼帝国。“拜占庭”一词是“罗马”的希腊语音译,因此拜占庭就是罗马。古罗马币和拜占庭币是一个连续体,把分界点选在哪里全在人为。
钱币学上一般不把395年作为拜占庭币的开始,而是把安纳斯塔一世(公元491-518)作为罗马币与拜占庭币的分界。原因在于安纳斯塔一世最先在币上使用希腊铭文,以前都是用罗马字的。而拜占庭文化的特点就是希腊化了的罗马帝国。
古罗马币从公元前6世纪出现粗铜铸币开始,到491年安纳斯塔一世币制改革为止,罗马币经历了多次改革。下面选重要的几次略作展开。
和希腊人最早用金银不同,罗马人最早是用称量铜块作货币的,最早的叫粗铜(aes rude),后来形状更规则并加上印记,叫印记铜(aes signatum)。这种粗铜币是铸造的而非打制的,这点和中国比较象。铜比银镕点低而硬度高,因此更适合铸造。这两种都是称量货币,每次买东西要带着秤的,因此叫钱币有些勉强。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种罗马钱币是公元前289出现的重铜阿斯(aes grave)。重量为1罗马磅(324克),每1罗马磅等于12盎司(uncia)。这种圆形铜铸币,正面均铸有两面神等神像,背面均为高昂的船首。当时罗马已经开始了海上扩张。
下图为重铜阿斯,图片取自(CNG):
图案就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两面神Janus是罗马神话中掌管门户的神,一面代表开始,一面代表结束。拉丁文和英语中的一月就是从Janus来的,因为一月January是一年的开始。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0] [/align]
罗马最早的银币采用希腊重量标准-德拉克马。到公元前211年发行第一枚第纳尔(denarius)银币,这种银币作为罗马的主币从共和时代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中期公元200多年。共和早期1个第纳尔银币值10个阿斯铜币,后来阿斯币慢慢变小,1个第纳尔值16个阿斯。 共和时期的钱币上不印人的头像,只有神像.
下图为共和时期第纳尔银币:
公元前85年发行的第纳尔银币,直径19.6mm,厚2.03mm,重4.03克.面是戴桂冠的阿波罗头像,背是小爱神丘比特骑着公羊,上面是代表Dioscuri兄弟的柱状物,脚下横线下面是代表能量的雷电球,整个图案被月桂环环绕。Dioscuri兄弟是希腊主神宙斯和Leda所生的双胞胎儿子,特洛伊美女海伦的哥哥。他们是互信合作的象征。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1] [/align]
再补充三个罗马共和时期第纳尔银币,本贴所发图片如非注明均是本人藏品或售出品:
下面这枚币发行于公元前151年,直径16.2-17.8mm,厚2.3mm,重4.2克.面是戴花冠的女神像,背面是飞马从台上跃起。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2] [/align]
这枚币发行于公元前128年,面:罗马女神,脑后麦穗.背:胜利女神驾马车,下有勇士斗狮,3.9g,直径18.61-20.89mm,厚2.07mm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3] [/align]
这枚币发行于公元前119年,面是雅努斯神(两面神),背:罗马女神举起战利品.重3.8g,18.5mmx2mm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4] [/align]
罗马金币使用的更晚,起初只在政府实在缺钱打仗时发行,到凯撒时代仗打得太多了,开始常规发行,规格为5.4克的奥雷金币(aureas)。罗马的金币成色重量相当稳定,几百年基本不变,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0多年才被轻1克左右的索利多(solidus)金币取代。而引入索利多也不是因为奥雷金币本身的问题,而是为了与其他材质币换算方便。
第一图为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奥雷金币(图片取自CNG):
第二图为哈德良的奥雷金币(图片取自CNG),重7.2克,公元134-138年打制。这枚是纪念哈德良巡查非洲行省而打制的,背面是戴大象头盔的非洲女神和狮子。
第三图为公元310年君士坦丁大帝改革币制后的索利多金币,重4.5克左右
第四图为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之后,公元527-565年拜占庭时期,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发行的索利多金币
面:皇帝头像,背:天使执十字架,此时币面上开始出现基督教标志,要到更晚些时候耶稣的头像才出现在币面上.
重4.33g,直径19.13-20.01mm,厚1.1mm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5]
[attachment=11328726] [/align]
下面就继续说金币。在三种币材中,金币的成色和重量比银铜币稳定,减重最慢,改革也就最少。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因为金币价值太高,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罗马拜占庭的金币一般不用来发工资和购买柴米油盐等日常用品。根据Sayles的Ancient Coins Collecting II一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金银比价约为1:13至1:15(中国古代缺银,比价低些)。一个技术工人的工资约为每天一个第纳尔银币,一个金币就是近一个月的工资。就算发个金币给工人他也要换成银铜币才能花。因此金币多用于大额交易,军费,储存财富等功能,流通速度比银铜币要慢。一个佐证就是出土的金币中有很多基本未流通的,好品的比例比银铜币都大。
金币价值高,使用又不频繁,接收的人一定小心检验其成色和重量,再加上使用的人主要是政府所依赖的贵族富人,因此政府在金币上做手脚遇到的阻力比较大,成色和重量就降低的最慢。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7][/align]
到了拜占庭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罗马后期和拜占庭前期的主要对手是东方的波斯萨珊王朝。萨珊以银为主要货币,拜占庭的白银因为岁供贸易等原因,大量东流。可能拜占庭银矿产量也不大,总之流传下来的拜占庭银币银币似乎比金币还少。缺银了,金币参与日常流通的机会就多了。它在拜占庭时期的变化就加快了。
索利多金币在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56年)时开始出现减重现象。查士丁尼是一代雄主,东方大败萨珊,西方夺回了意大利本土,使拜占庭的疆域达到了最大。但打仗是要花钱的,查士丁尼在首都也大兴土木,财政不紧张才怪,此时金币减重似乎也是大势使然。
到了公元960多年,福鲁斯二世在位期间,拜占庭金币减重更甚,形制上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薄片型的希斯塔梅隆金币。个人觉得这种改变适应了快速流通的需要。首先分割方便了,其次可以更有效的防止减边?感觉查士丁尼以后的金币经常被剪边,导致比标准重量轻0.2-0.5克。希斯塔梅隆金币钱体变大了,中心图案占的比例就大,剪边就更容易被看出来。
在此后的100来年,厚型足重的索利多金币逐渐消失了。希斯塔梅隆金币很快又演变成一面凹一面凸的碟型金币。这种币打制工艺要复杂一些,因为币胚要先要打成碟型,然后才能用印花。拜占庭金币为什么从平面的演化为碟型的至今是个谜。怀疑也跟防止偷金有关系,偷金的人在剪边以后可以锤打边缘以掩盖。弧线型的币身不易锤碟延展,减边就容易被发现。
希斯塔梅隆金币成色远不如奥雷金币和索利多稳定,成色不断降低,个人觉得跟更广泛的参与日常支付有关。货币一旦被平民使用,政府就可以比较顺利的降低成色以牟利。而且拜占庭后期国衰多难,银币铜币利润太小,也别无良策了。
第一枚为拜占庭/迈克尔七世/希斯塔梅隆碟型金币
面:绕光环的耶稣头像
背:皇帝持拉布兰和十字架
公元1071-1078年发行, 重4.43g,直径26.33mm-27.88mm,厚2.4mm,这种币成色约为80%左右,比索里多金币低,容易产生一种橘红色的包浆。
希斯塔梅隆碟型金币图案多有弱打,且币身容易变形,凸面容易磨损,因此好品的难找。
第二枚是清理过包浆的迈克尔七世金币,经过NGC评级为极美: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8728]
[attachment=11328729][/align]
[/size][/td][/tr][/table][/color]
[ 此贴被mylord在2010-10-22 17:11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