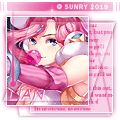—
本帖被 乱舞殇女 执行加亮操作(2011-10-02)
—
你站在老树下,像是看破红尘一样地闭着眼,任缕云如帆照在你额角的那个方向,盖敝住了你沉默的阴影。
突然你睁开眼,看见带毛的青虫耸着它笨拙的躯体,蜿蜒爬过你的阴影,你看着他,笑着对你身旁的老树说,你好,忧愁。而后抬脚,轻轻踩在它的身上,用力碾了几下。你看着它的整个身体被踩扁了,黄色浆状物与青色混合在一起,面目全非。
你想到面目全非的时候,笑了一下,很淡,很温柔,又是很看破红尘的样子。甚至低下头,屈膝轻抚了霞温软的花草,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柔抚那有生命却无意识的灵物,像恋人之间的暧昧与旖旎。你知道了,那是忧愁。
这种很古老的情感仿佛是绵延几千里那么久的,你恰认识它的时候,它便像带爪的老树根,久久盘踞在了你的心口,很揪心——你很开心地咧了下嘴角,很明显的动作,这次你笑了,是因为你终于想到了一个很合适的词,来形容你此刻矫情的心境,揪心。揪心这个词确实是造作而又矫情的。它作为言情小说里出现频率最多的恶俗心理描写,长久地盘踞在一个不可攀登的高度。
你想要坐下,踌躇了一会儿,决定只是斜靠着老树好了。老树的树皮真的有点老了,很干,并在逐步剥落着,像是你们班教政治的的那个老顽固的头顶,总是稀稀疏疏地紧贴着几根毛。事实上,你像是恶作剧般的看到老树开始脱皮,想靠又靠不得。老树总是这样要让人扫兴很久,凝望很久,沉思很久,怀念很久的。
你一直觉得自己自己开始成为了老树了。从里到外,从肉到皮,使一段零碎的历史沧桑起来,忧愁的人总是这样揪心的,老树亦然。
很久以后,你已经真的闭上眼的的时候,你听到了一阵乌鸦的叫声,很凄惨,却也很高调。它们结成群从你的头顶飞过,你甚至担心了一下它们飞过的时候有没有排泄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来。你想,你开始在意现实里的事物了,开始放弃忧愁了。
原来是夕阳西下了。
你又咧开嘴笑了一下。
在自然面前,内心再强大的恸创,无论如何也是抵不过的。你看了眼老树,看了眼失去生命的青虫,看了眼脚下温软的细草和头顶飞过的群鸦,抬脚往回走。
你想你要走到母亲的灵位前,为她上下葬前的三炷香。大家都在等你,等你回来,看母亲入土。
突然你睁开眼,看见带毛的青虫耸着它笨拙的躯体,蜿蜒爬过你的阴影,你看着他,笑着对你身旁的老树说,你好,忧愁。而后抬脚,轻轻踩在它的身上,用力碾了几下。你看着它的整个身体被踩扁了,黄色浆状物与青色混合在一起,面目全非。
你想到面目全非的时候,笑了一下,很淡,很温柔,又是很看破红尘的样子。甚至低下头,屈膝轻抚了霞温软的花草,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柔抚那有生命却无意识的灵物,像恋人之间的暧昧与旖旎。你知道了,那是忧愁。
这种很古老的情感仿佛是绵延几千里那么久的,你恰认识它的时候,它便像带爪的老树根,久久盘踞在了你的心口,很揪心——你很开心地咧了下嘴角,很明显的动作,这次你笑了,是因为你终于想到了一个很合适的词,来形容你此刻矫情的心境,揪心。揪心这个词确实是造作而又矫情的。它作为言情小说里出现频率最多的恶俗心理描写,长久地盘踞在一个不可攀登的高度。
你想要坐下,踌躇了一会儿,决定只是斜靠着老树好了。老树的树皮真的有点老了,很干,并在逐步剥落着,像是你们班教政治的的那个老顽固的头顶,总是稀稀疏疏地紧贴着几根毛。事实上,你像是恶作剧般的看到老树开始脱皮,想靠又靠不得。老树总是这样要让人扫兴很久,凝望很久,沉思很久,怀念很久的。
你一直觉得自己自己开始成为了老树了。从里到外,从肉到皮,使一段零碎的历史沧桑起来,忧愁的人总是这样揪心的,老树亦然。
很久以后,你已经真的闭上眼的的时候,你听到了一阵乌鸦的叫声,很凄惨,却也很高调。它们结成群从你的头顶飞过,你甚至担心了一下它们飞过的时候有没有排泄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来。你想,你开始在意现实里的事物了,开始放弃忧愁了。
原来是夕阳西下了。
你又咧开嘴笑了一下。
在自然面前,内心再强大的恸创,无论如何也是抵不过的。你看了眼老树,看了眼失去生命的青虫,看了眼脚下温软的细草和头顶飞过的群鸦,抬脚往回走。
你想你要走到母亲的灵位前,为她上下葬前的三炷香。大家都在等你,等你回来,看母亲入土。
[ 此帖被他的天下在2011-09-07 11:49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