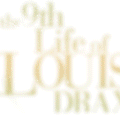迷雾
醒来的时候,便被这样一团朦胧的雾气所笼罩。放眼望去,触目所及的地方尽是一片迷蒙,看不清任何东西,只
有氤氲的仿佛蒸馏的水汽一般的迷雾,缓慢地摩挲着我的皮肤。
浓稠的像牛奶一样的白色,从指缝中流淌而过。时间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仿佛它已经不是地球上科学所定
义的某种维度,而是,一个遥远的已经停摆了的时钟。
一种茫然失措的情绪仿佛一只瘦骨嶙峋的枯手,狠狠地揪痛了我的心脏。脚下的步伐开始凌乱,无法在层层叠叠
的白色中找到一个出路。
左转,或是右转。
依然是浓重的雾气,以及不明方向的白。
忽而有风,从背后袭来。
恍若一把利剑,快意地从我的胸口中掠过。
微微的凉,然后是刺骨的冷。
我甚至能听见风声,从胸口那处的空洞中呼啸而过。却没有一滴血。只是原本那颗跳动的心脏,就寥无踪迹了。
奇怪的是,并没有疼痛的感觉,仿佛胸口处那个空洞自我出生时便有,一直一直存在,伴随我长大。
风呜咽着穿透我的身体,就像穿透一张蜘蛛网。我还记得某个夏天,雨后阳光下的蜘蛛网,闪烁着晶莹的水滴,而一阵风过后,只剩下勉强支撑的网络,而水滴,早已不复存在了。
自嘲地笑了笑,孑然一身的我,哪怕风再强,再大,又能够从我身上带走什么呢?
可渐行渐远的风声之中又隐约传来了人们的嬉笑声,似乎是孩子们的笑声,又似乎是歌声。
我像个盲人一般,摸索着前行,却只能徒劳地在虚空中挥着手。
步伐或许比蜗牛更加缓慢,也许是一支雪茄燃尽的时间之后,那声音消失了...
落水者好容易看到水中央有根浮木,拼命地扑腾过去后才发现居然是一段树皮。
无奈、哭笑不得都已经不足以说明我的心情。万分沮丧地,我蹲下身,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体,让医师脱离这付躯壳,慢慢地,慢慢地,沉下去。
雾气很快没过了我,好像母亲子宫内的羊水一般,温暖、安全。
我已经放弃抵抗和挣扎,放任那些似有生命般的雾气缠绕、束紧。
然后,就是猛地一沉...
黑暗——
心还在因为刚才的梦境狂跳,呼吸也还没有恢复平缓。
我从床上爬起来,猛地拉开窗帘向外张望——
迷雾,还在夜色中蔓延。
有氤氲的仿佛蒸馏的水汽一般的迷雾,缓慢地摩挲着我的皮肤。
浓稠的像牛奶一样的白色,从指缝中流淌而过。时间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仿佛它已经不是地球上科学所定
义的某种维度,而是,一个遥远的已经停摆了的时钟。
一种茫然失措的情绪仿佛一只瘦骨嶙峋的枯手,狠狠地揪痛了我的心脏。脚下的步伐开始凌乱,无法在层层叠叠
的白色中找到一个出路。
左转,或是右转。
依然是浓重的雾气,以及不明方向的白。
忽而有风,从背后袭来。
恍若一把利剑,快意地从我的胸口中掠过。
微微的凉,然后是刺骨的冷。
我甚至能听见风声,从胸口那处的空洞中呼啸而过。却没有一滴血。只是原本那颗跳动的心脏,就寥无踪迹了。
奇怪的是,并没有疼痛的感觉,仿佛胸口处那个空洞自我出生时便有,一直一直存在,伴随我长大。
风呜咽着穿透我的身体,就像穿透一张蜘蛛网。我还记得某个夏天,雨后阳光下的蜘蛛网,闪烁着晶莹的水滴,而一阵风过后,只剩下勉强支撑的网络,而水滴,早已不复存在了。
自嘲地笑了笑,孑然一身的我,哪怕风再强,再大,又能够从我身上带走什么呢?
可渐行渐远的风声之中又隐约传来了人们的嬉笑声,似乎是孩子们的笑声,又似乎是歌声。
我像个盲人一般,摸索着前行,却只能徒劳地在虚空中挥着手。
步伐或许比蜗牛更加缓慢,也许是一支雪茄燃尽的时间之后,那声音消失了...
落水者好容易看到水中央有根浮木,拼命地扑腾过去后才发现居然是一段树皮。
无奈、哭笑不得都已经不足以说明我的心情。万分沮丧地,我蹲下身,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体,让医师脱离这付躯壳,慢慢地,慢慢地,沉下去。
雾气很快没过了我,好像母亲子宫内的羊水一般,温暖、安全。
我已经放弃抵抗和挣扎,放任那些似有生命般的雾气缠绕、束紧。
然后,就是猛地一沉...
黑暗——
心还在因为刚才的梦境狂跳,呼吸也还没有恢复平缓。
我从床上爬起来,猛地拉开窗帘向外张望——
迷雾,还在夜色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