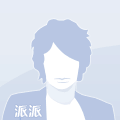—
本帖被 °○丶唐无语 从 品书评文 移动到本区(2013-03-18)
—
终于看完了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在书中援引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理论来解释轻与重:宇宙被一个个对立的二元分割着——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一极为正,另一极为负。我们的生命,就是悬挂在这正、负之间的无穷,一半在天,一半在地;一半在现实,一半在虚拟;一半在坟墓,一半在记忆;一半在远方,一半在心里;一半在梦外,一半在梦里。
读一本小说,感受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轻,在你、我,还有他的想象空间里,在灵魂与肉体背离的苦痛里,我们都一样,无论是书里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在我们的阅读时间中,我们也都在渐渐老去。我们穿越国界,在不同的斗争中,似无可奈何却又似冥冥注定般、顺其自然地一步步地发展,顺其自然地一步步地背离、迷失。再醒悟。再背离,再迷失……
人类的生活,常常是有担子的,有的人被沉重的生活压的很痛苦却能坚持,因为他们有信仰或精神支柱,有所要为之而活着的事物,此系生命之重,在沉重中体味本身的存在。所以,重,才是存在和不朽。而轻,是生命最不能承受的重。
轻与重,孰轻孰重?
花非花,雾非雾,世界至此,轻已非轻飘的轻,重已非沉重的重。
在人性光明与阴暗之间,思维在现实与想像、期望之间轮转,每个人,都在放大试图隐藏的弱点。有的时候,又在极力隐瞒。
人生背负着巨大的重压,受着种种难以改变的牵制,仿佛是蒲公英的根扎在土壤中,拼了命也无法移动。
可是当它足够轻,轻得足够抛弃根茎而飘起来,人生真若如此,不知道会不会同样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想起小说中的一句话:世界是如此丑陋,没有人愿意死而复生。已如此,那是怎么样的世界呢?
关于轮回与永恒,并非每一个人都乐意。
而“形而上”实在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哲学符号。
政治之中,爱情之上,灵肉之间,形而上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呢?
托马斯与特蕾莎那种奇妙的爱情与牵连,是政治、国家、工作的现实连同幻想、追求、梦境这些虚无,在命运画布上一并留下的轨迹。
托马斯追回了出走的特蕾莎,这个时候,因为托马斯的追,才显得特蕾莎的出走有了意义,才显出了特蕾莎之人、之爱情在托马斯灵魂上的重。
而特蕾莎,之前她对托马斯不忠的恐惧是那么强烈,而她,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有可能会永远失去托马斯,正因为这种对未来无所知、却又断然出走的行为,特蕾莎在小说中才有血有肉,才步步更显得真实存在。她对摄影的热爱,与对托马斯的灵与肉共同的爱,齐头并进,交织不断。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作者对人生与生活的观点呢?
不相信,或者说是不信任前世与来生,只信此生此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活在当下”?
大概吧。没有人给我答案。
在那样的时代与国家,在那样的政治氛围,在那样的选择与放弃之中,托马斯匆匆地老去。
人生,总要有始有终。从平静中来,再从平静中去。旁边的那么些个种种,毕竟还是掩不住时间与生命的步伐。
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我们已经被抛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
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
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读一本小说,感受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轻,在你、我,还有他的想象空间里,在灵魂与肉体背离的苦痛里,我们都一样,无论是书里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在我们的阅读时间中,我们也都在渐渐老去。我们穿越国界,在不同的斗争中,似无可奈何却又似冥冥注定般、顺其自然地一步步地发展,顺其自然地一步步地背离、迷失。再醒悟。再背离,再迷失……
人类的生活,常常是有担子的,有的人被沉重的生活压的很痛苦却能坚持,因为他们有信仰或精神支柱,有所要为之而活着的事物,此系生命之重,在沉重中体味本身的存在。所以,重,才是存在和不朽。而轻,是生命最不能承受的重。
轻与重,孰轻孰重?
花非花,雾非雾,世界至此,轻已非轻飘的轻,重已非沉重的重。
在人性光明与阴暗之间,思维在现实与想像、期望之间轮转,每个人,都在放大试图隐藏的弱点。有的时候,又在极力隐瞒。
人生背负着巨大的重压,受着种种难以改变的牵制,仿佛是蒲公英的根扎在土壤中,拼了命也无法移动。
可是当它足够轻,轻得足够抛弃根茎而飘起来,人生真若如此,不知道会不会同样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想起小说中的一句话:世界是如此丑陋,没有人愿意死而复生。已如此,那是怎么样的世界呢?
关于轮回与永恒,并非每一个人都乐意。
而“形而上”实在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哲学符号。
政治之中,爱情之上,灵肉之间,形而上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呢?
托马斯与特蕾莎那种奇妙的爱情与牵连,是政治、国家、工作的现实连同幻想、追求、梦境这些虚无,在命运画布上一并留下的轨迹。
托马斯追回了出走的特蕾莎,这个时候,因为托马斯的追,才显得特蕾莎的出走有了意义,才显出了特蕾莎之人、之爱情在托马斯灵魂上的重。
而特蕾莎,之前她对托马斯不忠的恐惧是那么强烈,而她,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有可能会永远失去托马斯,正因为这种对未来无所知、却又断然出走的行为,特蕾莎在小说中才有血有肉,才步步更显得真实存在。她对摄影的热爱,与对托马斯的灵与肉共同的爱,齐头并进,交织不断。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作者对人生与生活的观点呢?
不相信,或者说是不信任前世与来生,只信此生此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活在当下”?
大概吧。没有人给我答案。
在那样的时代与国家,在那样的政治氛围,在那样的选择与放弃之中,托马斯匆匆地老去。
人生,总要有始有终。从平静中来,再从平静中去。旁边的那么些个种种,毕竟还是掩不住时间与生命的步伐。
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我们已经被抛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
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
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