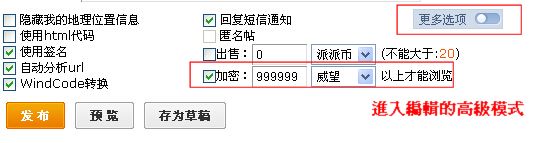读——吴祖光《风雪夜归人》(话剧本小说)
富家苏弘基的后花园,两个小毛孩儿被寒冬腊月刺骨的风雪逼退在假山后,点火取暖。从券门后传来颤颤悠悠,犹如鬼魂般的声音,"我在找我的影子.找我的脚印子..",疯癫痴傻着在寻找自己影子的老乞丐,单薄的身形在风中摇曳舞动,落下的雪花是它冷清的舞伴。偌大的动静引来了主人家的临窗 斥骂,老乞丐硬挺挺地倒在雪堆里,手中一柄折扇脱手而去。拳头里紧紧握着的金手镯也被当成了稀罕物,让两个小毛孩摸了去。
老北平的梨园旧梦,那是戏台上姿态曼妙的花旦魏莲生魏老板;戏台下妆容后是仗义疏财,菩萨心肠,扶危济困,为救邻居马大婶家稀里糊涂进了局子的二傻子,疏通人情不在话下。和以走私鸦片起家的法院院长苏弘基周旋着,魏莲生与苏弘基家青楼出身的四姨太玉春一见钟情,在这被红尘浸染透了的俗世里,他,魏莲生也不过是一个为感情羁绊误了一生的普通百姓魏三,不再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亦不是《思凡》里的小尼姑。
四角的北京城里,少了《游龙戏凤》那般的的浪漫,遍地的九流人物,戏子biao子作死的令人看不起的下等人,‘biao子无情,戏子无义’是当时所谓的上等人口中,对于这类人的不懈讽刺。可他们骨子带了多少的苦水,知道的人不知道的人,都默不作声。而正正是同病相怜,让他们惺惺相惜,懂得彼此的苦楚,海棠花是见证爱情的最佳信物,依偎是最妙人儿的情话。远走高飞这样的痴梦,更是被玉春提上案头,从古至今这样宛如乌托邦世界观美好的愿望,在无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为之津津乐道,人们不曾一刻中断对它的追逐。戏剧中,更是惨无人道的赋予这类美好愿望不止一次的打击,造成强烈的剧情逆差,令读者‘泥足深陷’剧情中,不停叹息,不断愤愤,戏里戏外,这都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技法。
那个年代能轻而易举拆散一对“鸳鸯”的不是棍棒,而是人心。青楼出身的玉春,有着那个圈子里的姑娘所没有的单纯,不禁令我联想到阎连科先生笔下《艺妓芙蓉》里的萍,后者是为戏痴迷的女子,前者是为情痴迷的女子,都是渴望着自由,不愿被束缚,有着超前的思想,每每不禁令人掩卷长叹,这世间,道是多些这样的奇女子才好呀。玉春的‘新思想’触动了莲生,让他对自己现有的生活,产生了质疑,而李蓉生不足以外人道的悲惨往事,与寄托在他身上的期许,像千斤石一般压在莲生喘不过气。难以抉择的两难的境地尚未来得及发酵,乌云已经盖顶。
二人的感情被苏弘基家的管事王新贵发现,忘恩负义,出卖发小,讨好主人的戏码是一贯的奸角的套路,苏弘基知晓事情后,令王新贵带着打手到魏莲生家中捉拿玉春,并顺道让魏莲生有多远滚多远,名角魏莲生迫此,带着玉春交予的“大大的好用”的金镯子远走他乡。玉春则被苏弘基当作‘人情’送给徐辅成当使唤丫头,借此为自己的鸦片事业添砖加瓦。
远走他乡二十载,我们只能通过王新贵向着苏弘基狗腿的嘴里,知道昔日红冠北平的名伶魏莲生的凄惨处境,戏痴是戒不掉的瘾,骨子里正义感更是不能抹去的印迹,相助的不挂名登台唱戏也是一句话儿的事。纵是年华老去,大风掀顶。带着没有影子的残躯,带着对玉春无限的思念,魏三游园惊梦,梦醒魂断。在1949年由吴祖光先生亲自导演的同名电影,为莲生在凄惨的人生落幕时,安排了一段他与玉春的相逢戏,似乎有了这么一点‘人情味’,也让最后,过于哀伤而不忍直视的结局有了一丝的宽怀。‘荣归故里’的徐奶奶玉春跟着徐辅成回到了北平,探望潜心修佛的苏弘基。昔日富商的虚假的慈悲,满口仁义道德的伪清廉贪恋的美色,一介俗世里污浊的凡人,到如今,既是一身上等人的派头,不也在岁月的泥河里沉淀出一副下等人的面孔,骨子的尽是烂透了汁水。
玉春在徐辅成先行离去探望苏弘基后,便悄然离去,不见了踪影。消失在漫天飞雪中。穷困潦倒,一身伤病的莲生在被戏棚子砸伤后,倒毙在苏府后花园,雪夜落不尽的,是莲生不肯离去的念想,天幕上那宛似一轮圆月的券门中,一袭红衣的俊逸少年郎舞尽桃花扇底风,那是魏三对世事的控诉。
[ 此帖被zy32593在2015-02-24 23:10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