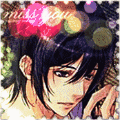倒也记得:——
我又怎会不知你是不是他,否则,怎会不让你拔剑?可是在你的琴声里,你就是他呀……
寻找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永远都在茫茫人海里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就连下一步该迈向何方都不知晓。不停地拦住路人,不停地提问,然后不停地收获白眼与嘲弄。
「我只想歇一歇,就歇那么一会儿……我知道他不是善类,却还是忍不住跑来这里听琴……至少在琴声里,我已经找到他,可以不用那么累了了。」
「死在琴声里又怎样?至少……可以不会做恶梦,不必再找人。所以,我不恨他。我感谢他。」
这几段已经为本传《降魔塔》埋下了伏笔。寻人的故事,通常是虐到心脾的。而公子欢喜又是出了名的淡淡一刀,淡淡的叙述淡淡的回忆淡淡的温情淡淡的纠结淡淡的感动,让所有的读者都不能淡淡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过是一个痴情的别扭的小道士和暴躁的更别扭的烂神仙的故事。
不过是一个爱人爱得入了魔的小道士和悔恨悔得入了魔的烂神仙的故事。
不过是一个两情相悦却无人表明心迹各自纠结的故事。
不过是一个刻意的玩笑铸成了日后的剜骨钻心的故事。
不过是一个人在前面走一个人在后头跟却假装无所谓的故事。
不过是一个人在痴痴地寻一个人在不断阻拦却不知自己寻的人就是他的故事。
不过是一双人在各自的安全范围内黯然神伤地爱着对方,自伤三分再去伤人七分,在错落的时光里兜兜转转直到精疲力竭直到执念成魔都不愿明说,一个念念不忘轮回之后依旧坚持抱着长剑四处寻找,一个明知是痴妄却仍拿般若花维持他的一丝灵识不愿放手的故事。
一句:“我以为他是你。”一句:“你以为我是他。”
成了两人的魔障,生生地在两人间劈出一道鸿沟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思念,却还要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可纵使时光打马而去,纵使前尘往事我已不记得,你还是于千千万中得见你一人,道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最完满不过。
可纵使他细致周到体贴入微,在风里挽我的鬓发,在雨里揽我的肩头,长街上不着痕迹护在我左右,危难处一声不吭挡在我身前,不刁难我,不责骂我,不强迫我,总是坐在那儿静静侧着耳听,哪怕我说得再荒谬再离奇再可笑,亦当做金玉良言天帝的谕旨,用那般憨厚良善的笑容包容着谦让着甚至是赞成着;纵使你不憨厚、良善、温柔,总是伸过手来强自箍住我的手腕,不容拒绝不容退让不容半点挣扎,要我看着你,要我听你说,要我对你笑,刁难我,叱责我,强迫我,不知不觉就伤了我,看我泛红的手腕惨败的脸色又懊悔,扭过脸去硬邦邦扔一句:“你瞎了?你聋了?你哑巴了?”重重哼一声,昂着头拂袖而去。你还是你,从始至终也不过是你一人而已,还好最后你我皆了悟,最完满不过。
温柔不温柔,憨厚不憨厚,甚至良善不良善,这些都没关系,你不必有春水般眼眸春风般笑容,只凭那一纸短笺,只凭这百年孤寂岁月,只凭这塔这城,就足够了,什么都够了。
一开始是道士与敖钦。
敖钦问他,“他是你什么人?”
道士便答,“重要的人。”
“重过于性命?”
“重过于众生。”
最后也是在这百年来永远是暮春节气的城里,敖逦拾角眨八驼饷粗匾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