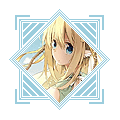苏维埃变脸:对华"甜言蜜语"背后藏掠夺心
一个远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自成一体,安然富足;另一个横亘于西欧与亚洲蛮族之间,坚韧而烂漫。这便是中国和俄罗斯,除了共同的集体主义哲学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的趋同,似乎找不出更多的共同点来将两族归于同类。然而这唯一的一点相同之处,就足够两个民族走到一起,并演绎出一出时分时和的悲喜剧。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中俄两国同时迎来命运的巨变。孔子的后人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羁绊开始痛苦求索,彼得大帝的传人坚定的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设想出的道路。原本安然富足的中国人此前已饱受俄国人的欺凌,而选择了新式道路的俄国人却向东方抛来橄榄枝——我愿归还昔日抢走的领土,我愿放弃赔款,我愿放弃特权,我愿……我愿……
这是梦幻?是骗局?还是一个把话说得太过,另一个却太过当真?
是否当真不要紧,只是国与国之间千万不能天真。
“红色维基解密”
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过程相当于一种信息控制,亦即对权力的攫取。“维基解密”首脑阿桑奇被认为用部分“重量级”秘密文件来自保,各国解密档案也都遵循着不破坏当下政治秩序的原则来进行,斯大林死后其生前隐秘即遭曝光的先例更显示出权力与信息控制的紧密相关。
所以,当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他们几乎将完全的信息控制权掌握在了手中的时候,打一场信息战便是势所必然。虽在彼得格勒取得成功,但俄国全境尚为未定之地,其他帝国正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在英国担任军需大臣的丘吉尔更是扬言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新政权必须使出全力自保。此一背景下,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带着一位年仅24岁的水兵马尔金径直冲向了旧俄外交部大楼。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那里保存着沙皇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肮脏且不可告人。托洛茨基留下一句话:“我的工作很简单:公布一切秘密条约,然后关了那个小地方!”
这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用一个颇具蔑视意味的词语指代沙皇俄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正因此,他将年轻的马尔金带在身边,不仅因为他有足够的学识和政治觉悟,更因为他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他必须在几周的时间内将帝俄外交部中保存的档案材料统统整理出来,择重要部分结集公布。这一极端耗费体力与脑力的工作被列宁看做是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树立形象进而争取盟友的重要步骤。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圆柱大厅,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法令》,“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亮点,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样,旧俄秘密条约的整理与公布就成为重要的后续手段,摆在马尔金面前的任务相当沉重。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马尔金带着一众水兵与赤卫队员没日没夜的在旧俄外交部内阅读、研究、归类。一位赤卫队员后来称,马尔金几乎一直没动地方,吃住在档案室的一个角落里。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他们还专门送来了一个防火的柜子,专门用来保存整理好的文件。
两位领袖心里十分清楚,新政权没有大量任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人员,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前更是与旧俄政权无涉,所以揭露的力度完全不必有所保留。
1917年12月,100多份秘密档案整理完毕,《真理报》和《消息报》将全部文件公诸于众,国际媒体疯狂转载。1892年法俄军事秘密协定、1905年俄德军事条约、1907年英俄瓜分伊朗、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秘密协定统统大白于天下。诸如英法俄商定瓜分奥斯曼土耳其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让阿拉伯人单独建国的协议内容给伦敦造成了不小的国际压力。讨伐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袭来,列强应接不暇,布尔什维克人的信息战初战告捷。列宁为新生的政权营造了一个崭新的形象。
山雨欲来
列宁因此而被挪威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但以西方对红色政权的敌视,他的提名很自然的被驳回了,理由是“已经错过了提名时间”。诺奖委员会补充称,如果列宁及其政府可以在国内停止战争、确立和平,委员会不反对在未来授予其和平奖。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说辞。1918年1月3日,对苏俄的《和平法令》反应敏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与英国大使赖斯会谈时说:“如果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吁继续得不到答复,如果丝毫不去抵抗它,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扩大。”5天后,这位学者出身的总统向国会托出了自己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两年后,以它为基础的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成立。
平心而论,初生的布尔什维克身处险境,所以它在这场信息战中自保的成分居多,但客观上确实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战场上推动了和平进程的前进,仅此一项想必便当得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法令》和“红色维基解密”固然起到了树立形象的作用,但也在更大程度上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不到一个月之后,日本的军舰就强行进入了海参崴港,英美军舰也随后抵达。第二年,被困苏俄的捷克军团起事造反,得到西方多国的支持。8月,多国干涉军进入俄国,加上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等各地的残余势力借势加紧进攻,新生苏维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当中。事实证明,若不是多国干涉军貌合神离,苏维埃政权恐怕真的会如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所说的那样被“用铁丝勒死”。作战期间,日美两国矛盾连连,若不是日方在关键时刻做出部分撤军决定,两国或许就将刀兵相向。
当此危急之时,类似对德《布勒斯特和约》这种委曲求全的买卖已是在所难免。在经历了数轮内部争论之后列宁坚持与德国缔结了这一割让大部分利益的和约。若在中国语境下,此约绝对可称得上“丧权辱国”。
强敌环伺,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列宁先前提出的《和平法令》的精神,苏维埃俄国都必须联手众多被列强欺凌的小国与弱国。一系列废除沙俄旧约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宣言与行动被频频祭出。在日本军舰出现在海参崴仅一天后,布尔什维克便宣布承认已被沙俄兼并了100多年的芬兰的独立地位。半年后,波兰也从列宁口中讨得独立地位,尽管它历史上曾数次被德、奥、俄三国瓜分。紧接着《告俄罗斯及全体东方穆斯林人民书》、《土耳其、亚美尼亚独立法令》先后出炉,而在对中国这个东方最为重要的潜在盟国身上,布尔什维克们更是寄予厚望,一份《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向中国人民许以重利,以求中国撤回自己的干涉军、肃清境内帝俄残余势力并成为阻挡日本西侵的重要屏障。按照这份宣言,苏俄政府将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
这一切听起来当然是相当诱人的,但这世界上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吗?真有不计利益得失的国家吗?更何况,那是俄国人。
横空出世的《对华宣言》
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亚大陆东端的封贡体系便已开始动摇。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努尔哈赤在满洲坐大,两人共同奏响了中国“去帝国化”的历史强音。在经历了满清所奉献的最后一个盛世之后,中国几乎彻底万劫不复。列强的撕咬痛彻心扉,近邻的啃噬更加刻骨铭心。历怀不臣之心的日本已是骑在睡狮头上的豺狼,但直到遇上俄国的东侵,中国人才知远甚豺狼的熊虎之怖。相比于日本的不甘居岛国一隅,俄国人对陆地空间和天然海港的狂热几乎是深入血液骨髓的原始本能。列强围噬之下,中国之贫弱显露无疑,俄国之贪婪更显疯狂,一跃成为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
近百年来的国人记忆是被一刀刀劈砍出来的,北方近邻留下的伤痕最深。
所以,毫不奇怪,俄帝国代之以斧头镰刀之后从北国传出的第一声问候到达中国的历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通过数个渠道,《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回了国内,但并未被中国民众所知晓。张斯麟便是几个传递者中的一个。1919年7月25日,这份宣言正式问世。半年后,身为中华民国驻哈尔滨边防处的张斯麟将宣言传递至北京。
及至1919年,苏俄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在美国干涉军于1918年撤回菲律宾之后,多国部队也都先后回国,只剩下从一开始就抱定吞噬远东领土之心的日本。曾经被列强遵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次在日本人身上不灵了,华盛顿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一意孤行的日本人用种种借口占据远东、侵占中俄领土并扶植傀儡,在承诺将追随美军撤军后却最终赖在当地。
就这样,先后击败了高尔察克等帝俄遗留将领以及其他干涉军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猛然发现西部因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并击败干涉军而局面大大缓解之后,东部反倒面临着日本人的威逼。如此,东方大国中国成为苏俄必须牵手的伙伴,以期借此缓解日本的压力。更何况,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也包括发表了《进军海参崴宣言》的中国北洋政府,苏俄更需早日将中国军队“劝”回国内。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权的北洋政府丝毫不为苏俄提出的诱人条件所打动。唯协约国马首是瞻的他们再胆大也不敢擅自同红色苏维埃接触,哪怕他们只求中国的外交承认。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后鼎沸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竟对苏俄十分青睐,街头要求承认苏俄的声势日盛。扛不住压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回行事,派人赴俄与苏俄接触,只是一切均低调从事,恪守非官方接触的原则。至于赴俄的人选,正是第一批传回苏俄《对华宣言》之一的张斯麟。
艰难转圜
这可称是中俄交往史中罕见一景,因为就在张斯麟以非官方身份远赴莫斯科时,远东共和国(为抵御日本压力而由莫斯科在远东成立的缓冲国,服从莫斯科领导)外交代表优林也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两人相对而行,但却同样都未实现进行外交照会。这罕见一景实际上道出一点,中俄是如此的需要进行接触。
两个民族在非常时期派出的两位外交官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张斯麟由于缺少照会而在远东遭到冷遇。远东共和国向北京发来问询,却得不到答复。困于远东的张斯麟不得已只得亲自向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发去电报。契切林接报后向中方进行询问,结果得到的却是北洋政府语焉不详的答复。至于后者为何如此行事,毫无疑问,是怕协约国据此将此次访问看做是官方行动。结果,搞得张斯麟进退失踞,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而不远之外的优林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样由于没有外交照会,他被阻在中国远东共和国边境动弹不得。数次向北京发出的申请如石沉大海。原因是一样的,北洋政府万万不敢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如果协约国列强不点头的话。
情急之下,张斯麟独辟蹊径,向莫斯科当地侨领发去电报,望后者提供协助。幸运的是,接报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与列宁颇有私交,甚至持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在他的周旋之下,列宁亲自首肯了张斯麟的访问,并表示正急着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命令传至远东共和国,张斯麟转眼间又成了上宾,待遇即刻升格。几天后即出发前往莫斯科。当然,在这之前他没有忘记为尚困在边境的优林助一臂之力。他电告北京,优林为商谈中俄外交之事而来,但并非官方代表,可予以放行并予以接待。这样,优林才最终踏上了中国土地。
不过,优林的访问并未能取得进展,北洋政府只与其就边境贸易进行了简要商谈。相比之下,张斯麟的访问收获颇丰。他直接见到了列宁,并将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起草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也带回了国内。列宁与张斯麟相谈甚欢,苏方对这位首位来自中国的使者极为看重,甚至也将与刘绍周所持有的相同的克里姆林宫通行证给了他。列宁向张斯麟表达了希望尽快与中国建交的愿望。通过交流,张斯麟明白,列宁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中国不能在未来成为帝俄残部从事反苏活动的基地。此外,苏方愿意与中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以及边界问题展开谈判。
而在《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中,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有关中东铁路的条款已经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而在列宁口中,交还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也成了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
无论怎样,张斯麟确实打开了中苏之间的大门。接着,仍是在汹涌民意的推动下以及已有列强作为开路先锋的背景下,北洋政府下决心与苏俄正式接触。
归国的张斯麟偶然碰到了即将赴任驻莫斯科总领事的陈广平和著名报人瞿秋白。张斯麟向两人大倒苦水,抱怨北洋政府的裹足不前,因为他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举通关,促成两国正式建交。
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由这些探路者和列强们规定了轨道,俄国外交官越飞以及两次《对华宣言》的作者加拉罕先后访华。并最终在加拉罕与中方的斗智斗勇后双方签署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两国建交画上了句号。
这个句号可没有《对华宣言》中声称的那么美,中国最为在意的外蒙古问题,苏方并未承诺撤军,只是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双方承诺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可由中国赎回,而不是《对华宣言》中所称的无条件归还,分文不取。而且,俄罗斯还通过人员调配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
北洋政府曾因无法接受苏方的苛刻条件而让谈判破裂,但却因无法应付国内学生的“无条件与苏建交”的压力而被迫回到谈判桌上。
笔者无法像专业学者那样掌握最为详细的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信息,但却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加拉罕曾于1923年12月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此举当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似乎中方的不满并未取得什么效果。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在其与人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曾评价,加拉罕在此间的表现是坚强又成功的。
我相信,此言不虚。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内心总有些沉重,不愿再读下去。中国雄鸡“鸡冠”上的那大片的土地一直被国人算做应该由俄国人归还的行列。但毫无疑问,列强混战的“帝国时代”已然远去,能够生活在国际法具有一定效力的时代是一种幸福,只是遗憾是难免的,要想向北边的邻居讨回那片土地或者让他们兑现昔日的诺言已经愈发不可能。
每每谈及此段历史,我也总会想起几年前在俄留学时的场景。历史课堂上,俄罗斯老师像我小学时的中国历史老师一样,将自己国家的历史描述的无比悲情。谈及康熙时期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更是强调其对俄罗斯的不公平,全然不在意下面坐着的是一群中国学生。更过分的是,毕业论文选定题目时,一位导师居然为我的同学推荐了一个《大连——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城市》的题目。
愤怒之余,我会冷静地思考,并非是这些老师挑衅,我相信这只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历史教育。
如果这些老师是这样的,那么当年“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就不是这样吗?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同样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从策划那场信息战到与众多小国交好,再到对中国施展“甜言蜜语”,站在背后的无不是民族主义思维。待到真正与中国人走上谈判桌时,苏俄的境遇已经大为改观,自然无需再做太多让步。
这本是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不变规律,那些走上街头鼓噪“无条件承认苏联”的师生们,难道当时他们都忘了这些了?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中俄两国同时迎来命运的巨变。孔子的后人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羁绊开始痛苦求索,彼得大帝的传人坚定的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设想出的道路。原本安然富足的中国人此前已饱受俄国人的欺凌,而选择了新式道路的俄国人却向东方抛来橄榄枝——我愿归还昔日抢走的领土,我愿放弃赔款,我愿放弃特权,我愿……我愿……
这是梦幻?是骗局?还是一个把话说得太过,另一个却太过当真?
是否当真不要紧,只是国与国之间千万不能天真。
“红色维基解密”
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过程相当于一种信息控制,亦即对权力的攫取。“维基解密”首脑阿桑奇被认为用部分“重量级”秘密文件来自保,各国解密档案也都遵循着不破坏当下政治秩序的原则来进行,斯大林死后其生前隐秘即遭曝光的先例更显示出权力与信息控制的紧密相关。
所以,当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他们几乎将完全的信息控制权掌握在了手中的时候,打一场信息战便是势所必然。虽在彼得格勒取得成功,但俄国全境尚为未定之地,其他帝国正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在英国担任军需大臣的丘吉尔更是扬言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新政权必须使出全力自保。此一背景下,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带着一位年仅24岁的水兵马尔金径直冲向了旧俄外交部大楼。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那里保存着沙皇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肮脏且不可告人。托洛茨基留下一句话:“我的工作很简单:公布一切秘密条约,然后关了那个小地方!”
这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用一个颇具蔑视意味的词语指代沙皇俄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正因此,他将年轻的马尔金带在身边,不仅因为他有足够的学识和政治觉悟,更因为他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他必须在几周的时间内将帝俄外交部中保存的档案材料统统整理出来,择重要部分结集公布。这一极端耗费体力与脑力的工作被列宁看做是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树立形象进而争取盟友的重要步骤。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圆柱大厅,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法令》,“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亮点,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样,旧俄秘密条约的整理与公布就成为重要的后续手段,摆在马尔金面前的任务相当沉重。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马尔金带着一众水兵与赤卫队员没日没夜的在旧俄外交部内阅读、研究、归类。一位赤卫队员后来称,马尔金几乎一直没动地方,吃住在档案室的一个角落里。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他们还专门送来了一个防火的柜子,专门用来保存整理好的文件。
两位领袖心里十分清楚,新政权没有大量任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人员,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前更是与旧俄政权无涉,所以揭露的力度完全不必有所保留。
1917年12月,100多份秘密档案整理完毕,《真理报》和《消息报》将全部文件公诸于众,国际媒体疯狂转载。1892年法俄军事秘密协定、1905年俄德军事条约、1907年英俄瓜分伊朗、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秘密协定统统大白于天下。诸如英法俄商定瓜分奥斯曼土耳其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让阿拉伯人单独建国的协议内容给伦敦造成了不小的国际压力。讨伐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袭来,列强应接不暇,布尔什维克人的信息战初战告捷。列宁为新生的政权营造了一个崭新的形象。
山雨欲来
列宁因此而被挪威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但以西方对红色政权的敌视,他的提名很自然的被驳回了,理由是“已经错过了提名时间”。诺奖委员会补充称,如果列宁及其政府可以在国内停止战争、确立和平,委员会不反对在未来授予其和平奖。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说辞。1918年1月3日,对苏俄的《和平法令》反应敏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与英国大使赖斯会谈时说:“如果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吁继续得不到答复,如果丝毫不去抵抗它,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扩大。”5天后,这位学者出身的总统向国会托出了自己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两年后,以它为基础的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成立。
平心而论,初生的布尔什维克身处险境,所以它在这场信息战中自保的成分居多,但客观上确实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战场上推动了和平进程的前进,仅此一项想必便当得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法令》和“红色维基解密”固然起到了树立形象的作用,但也在更大程度上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不到一个月之后,日本的军舰就强行进入了海参崴港,英美军舰也随后抵达。第二年,被困苏俄的捷克军团起事造反,得到西方多国的支持。8月,多国干涉军进入俄国,加上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等各地的残余势力借势加紧进攻,新生苏维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当中。事实证明,若不是多国干涉军貌合神离,苏维埃政权恐怕真的会如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所说的那样被“用铁丝勒死”。作战期间,日美两国矛盾连连,若不是日方在关键时刻做出部分撤军决定,两国或许就将刀兵相向。
当此危急之时,类似对德《布勒斯特和约》这种委曲求全的买卖已是在所难免。在经历了数轮内部争论之后列宁坚持与德国缔结了这一割让大部分利益的和约。若在中国语境下,此约绝对可称得上“丧权辱国”。
强敌环伺,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列宁先前提出的《和平法令》的精神,苏维埃俄国都必须联手众多被列强欺凌的小国与弱国。一系列废除沙俄旧约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宣言与行动被频频祭出。在日本军舰出现在海参崴仅一天后,布尔什维克便宣布承认已被沙俄兼并了100多年的芬兰的独立地位。半年后,波兰也从列宁口中讨得独立地位,尽管它历史上曾数次被德、奥、俄三国瓜分。紧接着《告俄罗斯及全体东方穆斯林人民书》、《土耳其、亚美尼亚独立法令》先后出炉,而在对中国这个东方最为重要的潜在盟国身上,布尔什维克们更是寄予厚望,一份《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向中国人民许以重利,以求中国撤回自己的干涉军、肃清境内帝俄残余势力并成为阻挡日本西侵的重要屏障。按照这份宣言,苏俄政府将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
这一切听起来当然是相当诱人的,但这世界上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吗?真有不计利益得失的国家吗?更何况,那是俄国人。
横空出世的《对华宣言》
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亚大陆东端的封贡体系便已开始动摇。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努尔哈赤在满洲坐大,两人共同奏响了中国“去帝国化”的历史强音。在经历了满清所奉献的最后一个盛世之后,中国几乎彻底万劫不复。列强的撕咬痛彻心扉,近邻的啃噬更加刻骨铭心。历怀不臣之心的日本已是骑在睡狮头上的豺狼,但直到遇上俄国的东侵,中国人才知远甚豺狼的熊虎之怖。相比于日本的不甘居岛国一隅,俄国人对陆地空间和天然海港的狂热几乎是深入血液骨髓的原始本能。列强围噬之下,中国之贫弱显露无疑,俄国之贪婪更显疯狂,一跃成为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
近百年来的国人记忆是被一刀刀劈砍出来的,北方近邻留下的伤痕最深。
所以,毫不奇怪,俄帝国代之以斧头镰刀之后从北国传出的第一声问候到达中国的历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通过数个渠道,《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回了国内,但并未被中国民众所知晓。张斯麟便是几个传递者中的一个。1919年7月25日,这份宣言正式问世。半年后,身为中华民国驻哈尔滨边防处的张斯麟将宣言传递至北京。
及至1919年,苏俄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在美国干涉军于1918年撤回菲律宾之后,多国部队也都先后回国,只剩下从一开始就抱定吞噬远东领土之心的日本。曾经被列强遵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次在日本人身上不灵了,华盛顿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一意孤行的日本人用种种借口占据远东、侵占中俄领土并扶植傀儡,在承诺将追随美军撤军后却最终赖在当地。
就这样,先后击败了高尔察克等帝俄遗留将领以及其他干涉军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猛然发现西部因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并击败干涉军而局面大大缓解之后,东部反倒面临着日本人的威逼。如此,东方大国中国成为苏俄必须牵手的伙伴,以期借此缓解日本的压力。更何况,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也包括发表了《进军海参崴宣言》的中国北洋政府,苏俄更需早日将中国军队“劝”回国内。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权的北洋政府丝毫不为苏俄提出的诱人条件所打动。唯协约国马首是瞻的他们再胆大也不敢擅自同红色苏维埃接触,哪怕他们只求中国的外交承认。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后鼎沸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竟对苏俄十分青睐,街头要求承认苏俄的声势日盛。扛不住压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回行事,派人赴俄与苏俄接触,只是一切均低调从事,恪守非官方接触的原则。至于赴俄的人选,正是第一批传回苏俄《对华宣言》之一的张斯麟。
艰难转圜
这可称是中俄交往史中罕见一景,因为就在张斯麟以非官方身份远赴莫斯科时,远东共和国(为抵御日本压力而由莫斯科在远东成立的缓冲国,服从莫斯科领导)外交代表优林也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两人相对而行,但却同样都未实现进行外交照会。这罕见一景实际上道出一点,中俄是如此的需要进行接触。
两个民族在非常时期派出的两位外交官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张斯麟由于缺少照会而在远东遭到冷遇。远东共和国向北京发来问询,却得不到答复。困于远东的张斯麟不得已只得亲自向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发去电报。契切林接报后向中方进行询问,结果得到的却是北洋政府语焉不详的答复。至于后者为何如此行事,毫无疑问,是怕协约国据此将此次访问看做是官方行动。结果,搞得张斯麟进退失踞,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而不远之外的优林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样由于没有外交照会,他被阻在中国远东共和国边境动弹不得。数次向北京发出的申请如石沉大海。原因是一样的,北洋政府万万不敢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如果协约国列强不点头的话。
情急之下,张斯麟独辟蹊径,向莫斯科当地侨领发去电报,望后者提供协助。幸运的是,接报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与列宁颇有私交,甚至持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在他的周旋之下,列宁亲自首肯了张斯麟的访问,并表示正急着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命令传至远东共和国,张斯麟转眼间又成了上宾,待遇即刻升格。几天后即出发前往莫斯科。当然,在这之前他没有忘记为尚困在边境的优林助一臂之力。他电告北京,优林为商谈中俄外交之事而来,但并非官方代表,可予以放行并予以接待。这样,优林才最终踏上了中国土地。
不过,优林的访问并未能取得进展,北洋政府只与其就边境贸易进行了简要商谈。相比之下,张斯麟的访问收获颇丰。他直接见到了列宁,并将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起草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也带回了国内。列宁与张斯麟相谈甚欢,苏方对这位首位来自中国的使者极为看重,甚至也将与刘绍周所持有的相同的克里姆林宫通行证给了他。列宁向张斯麟表达了希望尽快与中国建交的愿望。通过交流,张斯麟明白,列宁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中国不能在未来成为帝俄残部从事反苏活动的基地。此外,苏方愿意与中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以及边界问题展开谈判。
而在《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中,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有关中东铁路的条款已经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而在列宁口中,交还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也成了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
无论怎样,张斯麟确实打开了中苏之间的大门。接着,仍是在汹涌民意的推动下以及已有列强作为开路先锋的背景下,北洋政府下决心与苏俄正式接触。
归国的张斯麟偶然碰到了即将赴任驻莫斯科总领事的陈广平和著名报人瞿秋白。张斯麟向两人大倒苦水,抱怨北洋政府的裹足不前,因为他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举通关,促成两国正式建交。
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由这些探路者和列强们规定了轨道,俄国外交官越飞以及两次《对华宣言》的作者加拉罕先后访华。并最终在加拉罕与中方的斗智斗勇后双方签署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两国建交画上了句号。
这个句号可没有《对华宣言》中声称的那么美,中国最为在意的外蒙古问题,苏方并未承诺撤军,只是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双方承诺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可由中国赎回,而不是《对华宣言》中所称的无条件归还,分文不取。而且,俄罗斯还通过人员调配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
北洋政府曾因无法接受苏方的苛刻条件而让谈判破裂,但却因无法应付国内学生的“无条件与苏建交”的压力而被迫回到谈判桌上。
笔者无法像专业学者那样掌握最为详细的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信息,但却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加拉罕曾于1923年12月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此举当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似乎中方的不满并未取得什么效果。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在其与人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曾评价,加拉罕在此间的表现是坚强又成功的。
我相信,此言不虚。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内心总有些沉重,不愿再读下去。中国雄鸡“鸡冠”上的那大片的土地一直被国人算做应该由俄国人归还的行列。但毫无疑问,列强混战的“帝国时代”已然远去,能够生活在国际法具有一定效力的时代是一种幸福,只是遗憾是难免的,要想向北边的邻居讨回那片土地或者让他们兑现昔日的诺言已经愈发不可能。
每每谈及此段历史,我也总会想起几年前在俄留学时的场景。历史课堂上,俄罗斯老师像我小学时的中国历史老师一样,将自己国家的历史描述的无比悲情。谈及康熙时期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更是强调其对俄罗斯的不公平,全然不在意下面坐着的是一群中国学生。更过分的是,毕业论文选定题目时,一位导师居然为我的同学推荐了一个《大连——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城市》的题目。
愤怒之余,我会冷静地思考,并非是这些老师挑衅,我相信这只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历史教育。
如果这些老师是这样的,那么当年“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就不是这样吗?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同样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从策划那场信息战到与众多小国交好,再到对中国施展“甜言蜜语”,站在背后的无不是民族主义思维。待到真正与中国人走上谈判桌时,苏俄的境遇已经大为改观,自然无需再做太多让步。
这本是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不变规律,那些走上街头鼓噪“无条件承认苏联”的师生们,难道当时他们都忘了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