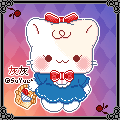宋代史书流传的“名人效应”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是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先例。毛泽东曾说:“《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与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也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
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
这方面例子非常多。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等著作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对于时人所撰史著,尤其是叙事颇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极大热情予以赞扬推荐
对于刘恕及其《十国纪年》,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饱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他又在该书末言:“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此后,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中亦论道:“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在此司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该书在同类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可见叶氏从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
这方面,如对于袁枢的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习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
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
总而言之,从以上诸种情况来看,名家不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爱的史著,而且还常常受人邀请,以极高热情推举赞扬相关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扩大这些史著的流传范围。同时,在推举称赞方式上,他们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而且多从阅读者的角度论述问题。具体而言,名家们有时采用直接评论,有时则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个人亲身感受来说明阅读心得,由此彰显相关史著的优点,以期达到对相关史著流传、刊刻的助推作用。
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名人对史书流传时的助推传播作用不容忽视。
(燕永成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与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也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
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
这方面例子非常多。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等著作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对于时人所撰史著,尤其是叙事颇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极大热情予以赞扬推荐
对于刘恕及其《十国纪年》,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饱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他又在该书末言:“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此后,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中亦论道:“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在此司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该书在同类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可见叶氏从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
这方面,如对于袁枢的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习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
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
总而言之,从以上诸种情况来看,名家不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爱的史著,而且还常常受人邀请,以极高热情推举赞扬相关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扩大这些史著的流传范围。同时,在推举称赞方式上,他们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而且多从阅读者的角度论述问题。具体而言,名家们有时采用直接评论,有时则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个人亲身感受来说明阅读心得,由此彰显相关史著的优点,以期达到对相关史著流传、刊刻的助推作用。
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名人对史书流传时的助推传播作用不容忽视。
(燕永成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