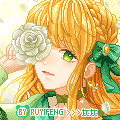“巫”作为一种职业
在宋代著名的志怪笔记《夷坚志》中,洪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南方地方信仰的大致蓝图:
大江之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方风俗的多样化特征以及跨地区地方神信仰的存在。虽然地方神的类型多种多样,很难找到一种固定的模式,然而主持各种祭祀仪式的巫师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根据《周礼》的分类,中国传统的鬼神被分成“天神”、“地袛”、“人鬼”、“物”(物怪、物魅、精怪)四大类。在宋代以前,历代政府的祭祀对象往往只限于前三大类,但是在两宋时期,不少巫师的祭祀对象变成了物魅、精怪。加上两宋瘟疫频频爆发,无论是道教还是巫师所代表的“民间宗教”都相当尊崇“瘟神”。宋代的巫者还会祭祀一些来历不明或是事迹无法考证的地方神。
宋代巫师信仰最受瞩目的仪式是迎神赛会。信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求消灾赐福。基本上,这和佛道二教利用社日或神明诞辰所举行的宗教活动,在仪式的功能和结构上并无太大不同。
这些“新风”的出现,也让宋代巫师往往收入不菲,如《岭外代答》第十卷记载:
里巷大罐,结竹粘纸,为轿马、旗帜、器械,祭之于郊,家出一鸡。既祭,人惧而散,巫独携数百鸡以归,因岁祠之。巫定例云,与祭者不得肺,故巫岁有大获,在钦为尤甚。
在祭祀结束后,祭坛上的供物一部分会归为巫师所有,或为众巫师瓜分,或将之分给与祭者,但在上面的材料中,巫师事先规定与祭者不得分享祭品,因此独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鉴于主持祭仪、沟通神灵是巫师的日常工作,这些供物也就构成了巫师主要和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大多数巫师游离于“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之外,他们不需从政、务农、做工或是长途奔波,只需频繁主持祭仪、为人攘灾求福,即能如《夷坚志》所载的邓城巫一般“藉此自给,无饥乏之虑”。这样的生存方式在农耕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中下层民众投入到民间巫术活动中去。
此外,这一时期巫师与佛教信仰已经发生了一些交集,在一些志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会用佛教咒语降妖除魔的巫师,比如《夷坚志》所载:福州有巫,能持秽迹咒行法,为人治祟甚验,俗称大悲巫。这是巫师主动吸收佛教持咒驱魔法术的结果,也是民间宗教试图借助正统佛教信仰将自己合法化的努力。而这种仪式杂合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宋代巫师社会对于政府压迫的直接反应。宋代朝廷颁布的禁巫诏令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任何一朝。但是也正因为宋代政府屡颁禁巫的法令,我们似乎可以侧面解读为当时“巫风炙烈”的明证。
男女巫师的职能分工
男女有别,男女巫师的职能也有着很大差异。
在宋代许多志怪小说中,女巫作为召魂者和驱魔者的角色反复出现。在《茅亭客话》中,一个名叫孙知微的处士与一位据说是当时的知名女巫展开了一段相当奇妙的对话:
女巫曰:“鬼有数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与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气劣神悴,假某传言,皆在乎一时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与求一鬼,请处士亲问之。”
知微曰:“鬼何所求?”
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
知微曰:“尝闻人死为冥吏追捕,案籍罪福,有生为天者,有生为人者,有生为畜者,有受罪苦经劫者。今闻世间人鬼各半,得非谬乎?”
女巫曰:“不然。冥途与人世无异,苟或平生不为不道事,行无过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见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事,处士有疑,请自问之。“
……
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
应者曰:“杀生与负心尔。所景奉者,浮图教也。”
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女巫的两种职能:第一,女巫可以通过法术召唤鬼神,并且可以被鬼神凭依;第二,女巫被认为可以预测人的命运。在上述对话中,女巫告诉孙知微她并不了解鬼神的实际情况,鬼神只是通过她的声音来与生人沟通,所以,女巫通常被认为是无意识的。
作为灵媒似乎是女巫主要的工作内容,她们可以通过灵魂旅行来与异世界的鬼神、祖先以及其他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也能被来自冥界的死者凭依从而让死者与其生人亲属沟通。在《夷坚志》的一条志怪故事中,官府甚至聘请了一位女巫来召唤受害人的鬼魂,查证一桩疑难案件的真凶:
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询之,方及门,巫举止言语如叶平生,大恸曰:“为我谢二尉,我以宿业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数日就擒,无所憾,独念母老且贫,吾囊中所贮,可及百千,望为火吾骸,收遗骨及余赀与母,则存没受赐矣。”尉悉如所戒,后五日,果得盗。
如前所述,灵媒是女巫的专属,而主持驱魔仪式似乎被认为是男巫的工作职能。宋代的巫师和道教的法师、佛教的僧侣一样,也是颇具威力的驱魔者,当家属邀请巫师来治疗他们被鬼神凭依的亲人时,巫师需要召唤超自然的其他鬼神来凭依他本人的身体,以获得属于这些鬼神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男巫并不仅仅是鬼神的载体,更具备控制和役使鬼神的能力,他们占据着主导权。从一个生动的案例,我们能直观地看到男巫所具有的强大法力: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兴二年秋,比邻沈氏母病,宣遣子沄与何氏二甥问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与二甥皆见神将,著戎服,长数寸,见于茶托上,饮食言语,与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挟与偕去,追沈母之魂,顷刻而至。形如生,身化为流光,入母顶,疾为稍间。沄归,夸语薛族,神其事。
比起男巫的这种强力功能,许多情况下,女巫经常只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媒介,她们的力量不足以“使鬼神”,而仅仅只是作为载体“通鬼神”。很明显,女巫在运用她们的超自然力量时被放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
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大变革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女巫不被认为和男巫具有同样的力量。伴随着文人地位的提高,优雅的士大夫阶层首先形成并引领了以娇弱为主导的审美风尚。腰细惊风、摇摇欲倒的女性形象深深满足了文人对自己男性气概的想象,也直接推动了缠足之风在整个社会的兴起。因此巫师世界也受到了这种社会整体性变革的影响。而根据杨剑利的研究,“巫”与“觋”的分化带来了氏族由母系向父系制的转型,随之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这种原始的分化构成了宋代巫师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大前提。
“巫”与政府的互动
如前文所述,宋朝的巫师需求大、收入高、能力强,似乎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然而在政府看来,巫师们所主持的民间宗教活动“皆祀典之所不载”,官员们将其视为是需要根除的“淫祀”。宋朝的巫师们其实并不好过。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当时非法的地方神崇拜已然成为了审判巫师的罪名:
黄六师者,乃敢执迷不悟,首犯约束。观其所犯,皆祀典之所不载,有所谓通天三娘,有所谓孟公使者,有所谓黄三郎,有所谓太白公,名称怪诞,无非丽魅魍魉之物。且从轻杖一百,编管邻州。其乌龟大王庙,帖县日下拆毁,所追到木鬼戏面等,并当厅劈碎,市曹焚烧。
上古中国建立了所谓“绝地天通”的宗教传统。这种信仰的基本特征是将人与神加以区隔,双方互为禁忌,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即《书·吕刑》所说的“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官方认为只有垄断祭祀的权力,才能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所以一直对各种地方神信仰加以限制。
但是,作为国家行为的大型祭祀难以满足地方民众治病祈福、祭拜祖先的需求,民众希望能够直接与神灵沟通,因此民间信仰得以大量涌现。然而民间宗教并不像儒释道三教那样直接以“神道设教”的方式与封建政权共谋,而只能暗中流传于民间,“执左道以乱政”、“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廖刚《乞禁妖教劄子》),长期以来,民间信仰与正统教化处于有所区隔又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中。民间信仰对公共秩序保持着潜在的威胁,其极端者甚至会如后来的摩尼教、白莲教那样,以反对当前政权的形式浮现出来,为起义提供合法性基础。这正是政府严格限制“淫祀”的原因之所在。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宋代巫师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艰难地在获得承认与违法犯禁的夹缝中生存,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律令的边界周围;而另一方面,两宋疆域大部处于南方,因为瘟疫的横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与当地民风的趋向,如学者所言,民众“笃信巫鬼,病不求医”的地步:“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独醒杂志》)他们的活动在民间又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因此我们看到,以摩尼教“吃菜事魔”之事为例,在绍兴四年出现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的局面,巫师作为“淫祀”的操办者,也是民间信仰的承载与传播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间宗教与政府的纠葛构成了宋代巫师基本的生存环境。
在宋代著名的志怪笔记《夷坚志》中,洪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南方地方信仰的大致蓝图:
大江之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方风俗的多样化特征以及跨地区地方神信仰的存在。虽然地方神的类型多种多样,很难找到一种固定的模式,然而主持各种祭祀仪式的巫师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根据《周礼》的分类,中国传统的鬼神被分成“天神”、“地袛”、“人鬼”、“物”(物怪、物魅、精怪)四大类。在宋代以前,历代政府的祭祀对象往往只限于前三大类,但是在两宋时期,不少巫师的祭祀对象变成了物魅、精怪。加上两宋瘟疫频频爆发,无论是道教还是巫师所代表的“民间宗教”都相当尊崇“瘟神”。宋代的巫者还会祭祀一些来历不明或是事迹无法考证的地方神。
宋代巫师信仰最受瞩目的仪式是迎神赛会。信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求消灾赐福。基本上,这和佛道二教利用社日或神明诞辰所举行的宗教活动,在仪式的功能和结构上并无太大不同。
这些“新风”的出现,也让宋代巫师往往收入不菲,如《岭外代答》第十卷记载:
里巷大罐,结竹粘纸,为轿马、旗帜、器械,祭之于郊,家出一鸡。既祭,人惧而散,巫独携数百鸡以归,因岁祠之。巫定例云,与祭者不得肺,故巫岁有大获,在钦为尤甚。
在祭祀结束后,祭坛上的供物一部分会归为巫师所有,或为众巫师瓜分,或将之分给与祭者,但在上面的材料中,巫师事先规定与祭者不得分享祭品,因此独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鉴于主持祭仪、沟通神灵是巫师的日常工作,这些供物也就构成了巫师主要和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大多数巫师游离于“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之外,他们不需从政、务农、做工或是长途奔波,只需频繁主持祭仪、为人攘灾求福,即能如《夷坚志》所载的邓城巫一般“藉此自给,无饥乏之虑”。这样的生存方式在农耕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中下层民众投入到民间巫术活动中去。
此外,这一时期巫师与佛教信仰已经发生了一些交集,在一些志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会用佛教咒语降妖除魔的巫师,比如《夷坚志》所载:福州有巫,能持秽迹咒行法,为人治祟甚验,俗称大悲巫。这是巫师主动吸收佛教持咒驱魔法术的结果,也是民间宗教试图借助正统佛教信仰将自己合法化的努力。而这种仪式杂合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宋代巫师社会对于政府压迫的直接反应。宋代朝廷颁布的禁巫诏令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任何一朝。但是也正因为宋代政府屡颁禁巫的法令,我们似乎可以侧面解读为当时“巫风炙烈”的明证。
男女巫师的职能分工
男女有别,男女巫师的职能也有着很大差异。
在宋代许多志怪小说中,女巫作为召魂者和驱魔者的角色反复出现。在《茅亭客话》中,一个名叫孙知微的处士与一位据说是当时的知名女巫展开了一段相当奇妙的对话:
女巫曰:“鬼有数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与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气劣神悴,假某传言,皆在乎一时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与求一鬼,请处士亲问之。”
知微曰:“鬼何所求?”
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
知微曰:“尝闻人死为冥吏追捕,案籍罪福,有生为天者,有生为人者,有生为畜者,有受罪苦经劫者。今闻世间人鬼各半,得非谬乎?”
女巫曰:“不然。冥途与人世无异,苟或平生不为不道事,行无过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见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事,处士有疑,请自问之。“
……
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
应者曰:“杀生与负心尔。所景奉者,浮图教也。”
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女巫的两种职能:第一,女巫可以通过法术召唤鬼神,并且可以被鬼神凭依;第二,女巫被认为可以预测人的命运。在上述对话中,女巫告诉孙知微她并不了解鬼神的实际情况,鬼神只是通过她的声音来与生人沟通,所以,女巫通常被认为是无意识的。
作为灵媒似乎是女巫主要的工作内容,她们可以通过灵魂旅行来与异世界的鬼神、祖先以及其他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也能被来自冥界的死者凭依从而让死者与其生人亲属沟通。在《夷坚志》的一条志怪故事中,官府甚至聘请了一位女巫来召唤受害人的鬼魂,查证一桩疑难案件的真凶:
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询之,方及门,巫举止言语如叶平生,大恸曰:“为我谢二尉,我以宿业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数日就擒,无所憾,独念母老且贫,吾囊中所贮,可及百千,望为火吾骸,收遗骨及余赀与母,则存没受赐矣。”尉悉如所戒,后五日,果得盗。
如前所述,灵媒是女巫的专属,而主持驱魔仪式似乎被认为是男巫的工作职能。宋代的巫师和道教的法师、佛教的僧侣一样,也是颇具威力的驱魔者,当家属邀请巫师来治疗他们被鬼神凭依的亲人时,巫师需要召唤超自然的其他鬼神来凭依他本人的身体,以获得属于这些鬼神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男巫并不仅仅是鬼神的载体,更具备控制和役使鬼神的能力,他们占据着主导权。从一个生动的案例,我们能直观地看到男巫所具有的强大法力: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兴二年秋,比邻沈氏母病,宣遣子沄与何氏二甥问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与二甥皆见神将,著戎服,长数寸,见于茶托上,饮食言语,与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挟与偕去,追沈母之魂,顷刻而至。形如生,身化为流光,入母顶,疾为稍间。沄归,夸语薛族,神其事。
比起男巫的这种强力功能,许多情况下,女巫经常只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媒介,她们的力量不足以“使鬼神”,而仅仅只是作为载体“通鬼神”。很明显,女巫在运用她们的超自然力量时被放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
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大变革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女巫不被认为和男巫具有同样的力量。伴随着文人地位的提高,优雅的士大夫阶层首先形成并引领了以娇弱为主导的审美风尚。腰细惊风、摇摇欲倒的女性形象深深满足了文人对自己男性气概的想象,也直接推动了缠足之风在整个社会的兴起。因此巫师世界也受到了这种社会整体性变革的影响。而根据杨剑利的研究,“巫”与“觋”的分化带来了氏族由母系向父系制的转型,随之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这种原始的分化构成了宋代巫师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大前提。
“巫”与政府的互动
如前文所述,宋朝的巫师需求大、收入高、能力强,似乎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然而在政府看来,巫师们所主持的民间宗教活动“皆祀典之所不载”,官员们将其视为是需要根除的“淫祀”。宋朝的巫师们其实并不好过。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当时非法的地方神崇拜已然成为了审判巫师的罪名:
黄六师者,乃敢执迷不悟,首犯约束。观其所犯,皆祀典之所不载,有所谓通天三娘,有所谓孟公使者,有所谓黄三郎,有所谓太白公,名称怪诞,无非丽魅魍魉之物。且从轻杖一百,编管邻州。其乌龟大王庙,帖县日下拆毁,所追到木鬼戏面等,并当厅劈碎,市曹焚烧。
上古中国建立了所谓“绝地天通”的宗教传统。这种信仰的基本特征是将人与神加以区隔,双方互为禁忌,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即《书·吕刑》所说的“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官方认为只有垄断祭祀的权力,才能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所以一直对各种地方神信仰加以限制。
但是,作为国家行为的大型祭祀难以满足地方民众治病祈福、祭拜祖先的需求,民众希望能够直接与神灵沟通,因此民间信仰得以大量涌现。然而民间宗教并不像儒释道三教那样直接以“神道设教”的方式与封建政权共谋,而只能暗中流传于民间,“执左道以乱政”、“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廖刚《乞禁妖教劄子》),长期以来,民间信仰与正统教化处于有所区隔又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中。民间信仰对公共秩序保持着潜在的威胁,其极端者甚至会如后来的摩尼教、白莲教那样,以反对当前政权的形式浮现出来,为起义提供合法性基础。这正是政府严格限制“淫祀”的原因之所在。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宋代巫师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艰难地在获得承认与违法犯禁的夹缝中生存,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律令的边界周围;而另一方面,两宋疆域大部处于南方,因为瘟疫的横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与当地民风的趋向,如学者所言,民众“笃信巫鬼,病不求医”的地步:“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独醒杂志》)他们的活动在民间又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因此我们看到,以摩尼教“吃菜事魔”之事为例,在绍兴四年出现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的局面,巫师作为“淫祀”的操办者,也是民间信仰的承载与传播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间宗教与政府的纠葛构成了宋代巫师基本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