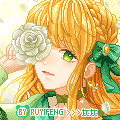1952年以前,“历史系”在南开大学实在是不成气候,历史这门学科也不被重视,名师寥寥,学生稀少。虽然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现称历史学院)始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23年,但当时的历史系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南开文科建制虽早,却偏重经济与政治之类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似乎只是补充课程而已,所以直到1927年时,南开文科的情状还很不乐观,文科内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心理、历史五系,始终无法摆脱“教授少,力量分散;学生少,各系所开课程只顾一系”的局面。尽管早在1923年之前,梁启超便在南开筹划创建东方文化研究院,希望通过此一机构来实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抱负,用以发扬国学,惜之响应者寡,社会反响亦是平平。其中奥妙自然是缘于南开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所限,一个私立大学根本不能满足此类纯学术机构“为学术而学术”的发展要求。不过,南开的后辈们议论校史向来以梁启超讲学南开为荣,甚至追尊其为历史系的四大名师之首(另外三位分别为蒋廷黻、郑天挺、雷海宗),每以谈论梁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为美。此一史话留给外人的感觉便是南开史学似乎素有家承,传统也甚为悠长。其实不然!南开人的这种自鸣得意实乃缘于一种颇为牵强的自家“传说”。其实,梁启超的那次学术经历对于其个人而言,只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普通片断而已。梁启超本人虽然对于倡办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极为热心,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不太满意。他称:“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比谬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他还曾坦言,要“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可见,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最终行诸于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不能成为南开向世人夸耀学术资本。仅仅一个学期且未形成规制的学术讲演,单是梁启超的一家之言,似不大可能会对一个学科,一个学系,乃至一个学校产生太大的影响。更何况,晚年的梁启超常常寓于京津两地,而其学术活动又多侧重于清华,若论南开史学传统之中继承了多少梁氏的精华,恐怕还需细细辨之!
或有以1923年蒋廷黻受聘南开讲授西洋史作为南开史学的滥觞而立论者,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可过于推崇,毕竟其时南开史学的研究状况确是名实俱渺。假设当年南开的学术环境宜人,条件可用,蒋廷黻也不会有“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伯苓)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的一番感慨。尽管在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承认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但那番记述的确表达出当时蒋廷黻的真实心态和南开史学研究的尴尬。而蒋氏移砚清华大学后,认为学校“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由蒋氏回忆,大致可以看出当年南开、清华两校学术机制的优劣。讲学南开期间,蒋廷黻虽已注意到近代外交史料之重要,但研究还并未走上正规,数年间也仅有一篇文章问世,若尊其为南开史学的“远祖”,似也颇为牵强。南开人如果远追(院)系之史,似可以梁、蒋史迹为美,但若论起当年南开史学之学术传统、治学门径、研究方法,却实在称不起有何鲜明特色。
至于南开史学之有所展进,倒是在西南联大时期,那时不仅系科规模略有扩充,而且学校也开始注意搜罗史学研究人才,及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南开大学历史系才粗具规模,先后有杨志玖、王玉哲、吴廷璆、杨生茂诸先生加盟。不过,南开历史学科真正意义上获得生机则还是要归功于1952年的那次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那一年,北大、清华两位重量级学者——郑天挺、雷海宗——调入南开大学参与系科建设、完善建制,并明确教研方式,名家的到来固然是历史系日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更为要紧的是,按照学科的标准而言,自此以后的南开大学终于确立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特定的概念体系的历史学科,这门学科正式在南开确立了地位,从而奠定下南开史学扎实、谨慎;重考证、轻玄谈的学术风格,由此以后逐渐开创出有自家特色的学术风范。
或有以1923年蒋廷黻受聘南开讲授西洋史作为南开史学的滥觞而立论者,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可过于推崇,毕竟其时南开史学的研究状况确是名实俱渺。假设当年南开的学术环境宜人,条件可用,蒋廷黻也不会有“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伯苓)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的一番感慨。尽管在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承认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但那番记述的确表达出当时蒋廷黻的真实心态和南开史学研究的尴尬。而蒋氏移砚清华大学后,认为学校“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由蒋氏回忆,大致可以看出当年南开、清华两校学术机制的优劣。讲学南开期间,蒋廷黻虽已注意到近代外交史料之重要,但研究还并未走上正规,数年间也仅有一篇文章问世,若尊其为南开史学的“远祖”,似也颇为牵强。南开人如果远追(院)系之史,似可以梁、蒋史迹为美,但若论起当年南开史学之学术传统、治学门径、研究方法,却实在称不起有何鲜明特色。
至于南开史学之有所展进,倒是在西南联大时期,那时不仅系科规模略有扩充,而且学校也开始注意搜罗史学研究人才,及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南开大学历史系才粗具规模,先后有杨志玖、王玉哲、吴廷璆、杨生茂诸先生加盟。不过,南开历史学科真正意义上获得生机则还是要归功于1952年的那次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那一年,北大、清华两位重量级学者——郑天挺、雷海宗——调入南开大学参与系科建设、完善建制,并明确教研方式,名家的到来固然是历史系日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更为要紧的是,按照学科的标准而言,自此以后的南开大学终于确立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特定的概念体系的历史学科,这门学科正式在南开确立了地位,从而奠定下南开史学扎实、谨慎;重考证、轻玄谈的学术风格,由此以后逐渐开创出有自家特色的学术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