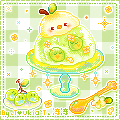一转眼,又是八一建军节;再过几天,就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打仗需要军人,军人需要熗支、需要弹药、需要吃饭、需要穿衣,倘若作战受伤,受了伤,还需要医生救治。所以,在那场决定国家气运、民族存亡、个人生死的战争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大批的爱国者。
林可胜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白衣
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祖籍福建海澄,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其父亲是著名医生,曾作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医生。[1]
家学渊源,使得林可胜也选择了这条路。他8岁即前往英国求学,随后考入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先后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的学士学位、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学位,还曾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可胜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学业、服从兵役,成为了一名战场医生。4年的军队生涯,既让他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又给了他战地救护的第一手资料。
医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医生却有自己的祖国。1925年秋,林可胜毅然回国,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也是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
自古以来,凡是“第一”,都会遇到不少困难。不过,林可胜很好地适应了新环境。作为雇员,他用扎实的学识,折服了故意刁难的外国教授;作为教授,他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用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考察学生对相关生理知识的掌握,据说林先生在讲课的时候,可以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比小龙女的“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更加传奇[3];作为学科负责人,他一方面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给了国内生命科学研究者一个坚实的阵地;另一方面,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4]
烽火
林可胜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个是肠抑胃素,一个是乙酰胆碱。
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进食脂肪后,胃液的分泌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林先生在1929年提出了肠抑胃素的概念,认为,脂肪会刺激肠道分泌肠抑胃素,进而通过肠抑胃素影响胃液的分泌。[5]
乙酰胆碱的实验则较晚,做于1936年。在这个实验中,林先生开创性地改进了电泳技术,试图确定乙酰胆碱的中枢效应。[6]
倘若时间足够,也许林先生可以继续改进自己的实验,为神经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可惜,时间不够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的协和,不是现在的协和。早在“七七事变”前夕,整个华北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林可胜就向当时的协和校长胡恒德(H.S.Houghton)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南下南京。但是胡恒德不仅要考虑到校方、美国的利益,而且顾虑日本的反应,所以,选择中立,并且建议林可胜去英国休假。[7]
家里着火了,别人可以旁观,自己难道也要袖手吗?
林可胜假借休假之名,一方面将自己的家人送至新加坡,以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只身南下武汉,组织了中国红十字会总救护队。[2]
战场救护之难,首先难在人员。林可胜的医术再好,也照顾不过来华北、华南各大战区的军人。所以,林可胜在上任之初,就将训练临床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仅仅半年内,便给三十二名外科医生、一百六十余名内科医生进行了培训,训练了一千四百余名医务工作者。[1]
第二,难在物资。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穷国。药物基本依赖进口不说,因为交通不便,即使有,也未必能及时输送。对此,林可胜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知名度,吸引了大量海外捐助;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想出了很多“土法子”。1938年,长沙大火,很多伤员患上了皮肤病,林可胜便把汽油桶改装成锅炉,布置成一个简单的灭虱治疥站,为患者洗澡、灭虱、治疥,解决了燃眉之急。
第三,难在疫情。战争时期,因为资源紧张、人力集中,不仅军队中容易出现疫情,民间也有可能爆发瘟疫。1940年夏天,林可胜光着上身、头包白布、一路步行,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随后,他又制订了“水与污染物管制计划”。先在长沙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对于减少战时疫情、提升部队战斗力,有不小的贡献。[1]
第四,难在战况多变。抗日救护总队成立于武汉汉口。因为战况吃紧,众人商议转移至祁阳。可惜“天不遂人愿”,战局变化太快。抗日救护总队刚赶到祁阳,就不得不再次开拨。几经辗转,最终选择了贵阳图云关落脚。图云关既是交通要道,也是不毛之地,救护队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住草棚、吃糙粮,靠着巨大的热情,支撑着自己的工作。[7]
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抗日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进行了11万9836次手术,收治了214万2997名住院患者。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奇
战争救护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难在凝聚人心。林先生虽然不是读死书的,但是难免有些书生的天真。抗日战争虽然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但历来,有干事儿的,就有拆台的。
林先生曾在香港接受一批国外左翼人士捐赠的药品、器械,然后运送给白求恩医院。为此,受到“亲共”的指责。对于国内各大战区,林先生也是一视同仁,不仅向西北地区运输物质,而且派出医疗队,到解放区和新四军工作。
在林可胜先生眼里,这是一场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战争,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不应该有门派之间,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里首先是中国,其次必须是国民党治下的中国。[8]
种种桩桩的摩擦,迫使林先生先后多次辞职,并最终在1942年离开抗战救护总队,进入中国远征军,帮助远征军开展救护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林可胜推辞了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职务,于1949年远赴美国。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林可胜一直没有忘记中国。
他一直关心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在英文刊物上引用中国文章的科学家。[9]可能是因为对战争的记忆太深,在晚年,林可胜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阿司匹林的镇痛机制。他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证实,阿司匹林是在外周发挥镇痛作用的。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1969年7月8日,林可胜先生因为癌症去世。但是,他对技艺的追求、对家国的热爱,将永远激励我们;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机敏练达、仁心仁术,更是早已成为一段传奇,永远流传。
--------------------------------------------------
参考文献
[1] 智效民. 民国时期的科学家 (之六)——林可胜与中国的红十字会[J]. 社会科学论坛, 2015(6): 162–167.
[2] 陈民. 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J]. 抗日战争研究, 1992, 4(2): 218.
[3] 讴歌. 协和医事[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汪子春, OTHERS. 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发展概况[J]. 中国科技史料, 1988, 2: 17–35.
[5] 陈适等. 国际肠抑胃素和肠促胰素研究的先驱: 北平协和医学院林可胜教授[J]. 协和医学杂志, 2017, 8(1): 76–79.
[6] 陈宜张. 记粟宗华, 王嘉祥, 林可胜 1936 年的小电泳实验[J]. 生理学报, 2011, 63(5): 477–478.
[7]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 “林可胜时期”(上)[J]. 南通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20(2): 1–6.
[8]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下) --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V6.5)[EB/OL]. [2017-07-12].
[9] 饶毅. 几被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 中国生理科学之父: 林可胜[J]. 中国神经科学杂志, 2001, 17(2): 171–172.
[10] BENEDETTI F. The patient’s brain: the neuroscience behi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林可胜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白衣
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祖籍福建海澄,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其父亲是著名医生,曾作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医生。[1]
家学渊源,使得林可胜也选择了这条路。他8岁即前往英国求学,随后考入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先后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的学士学位、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学位,还曾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可胜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学业、服从兵役,成为了一名战场医生。4年的军队生涯,既让他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又给了他战地救护的第一手资料。
医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医生却有自己的祖国。1925年秋,林可胜毅然回国,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也是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
自古以来,凡是“第一”,都会遇到不少困难。不过,林可胜很好地适应了新环境。作为雇员,他用扎实的学识,折服了故意刁难的外国教授;作为教授,他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用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考察学生对相关生理知识的掌握,据说林先生在讲课的时候,可以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比小龙女的“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更加传奇[3];作为学科负责人,他一方面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给了国内生命科学研究者一个坚实的阵地;另一方面,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4]
烽火
林可胜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个是肠抑胃素,一个是乙酰胆碱。
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进食脂肪后,胃液的分泌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林先生在1929年提出了肠抑胃素的概念,认为,脂肪会刺激肠道分泌肠抑胃素,进而通过肠抑胃素影响胃液的分泌。[5]
乙酰胆碱的实验则较晚,做于1936年。在这个实验中,林先生开创性地改进了电泳技术,试图确定乙酰胆碱的中枢效应。[6]
倘若时间足够,也许林先生可以继续改进自己的实验,为神经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可惜,时间不够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的协和,不是现在的协和。早在“七七事变”前夕,整个华北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林可胜就向当时的协和校长胡恒德(H.S.Houghton)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南下南京。但是胡恒德不仅要考虑到校方、美国的利益,而且顾虑日本的反应,所以,选择中立,并且建议林可胜去英国休假。[7]
家里着火了,别人可以旁观,自己难道也要袖手吗?
林可胜假借休假之名,一方面将自己的家人送至新加坡,以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只身南下武汉,组织了中国红十字会总救护队。[2]
战场救护之难,首先难在人员。林可胜的医术再好,也照顾不过来华北、华南各大战区的军人。所以,林可胜在上任之初,就将训练临床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仅仅半年内,便给三十二名外科医生、一百六十余名内科医生进行了培训,训练了一千四百余名医务工作者。[1]
第二,难在物资。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穷国。药物基本依赖进口不说,因为交通不便,即使有,也未必能及时输送。对此,林可胜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知名度,吸引了大量海外捐助;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想出了很多“土法子”。1938年,长沙大火,很多伤员患上了皮肤病,林可胜便把汽油桶改装成锅炉,布置成一个简单的灭虱治疥站,为患者洗澡、灭虱、治疥,解决了燃眉之急。
第三,难在疫情。战争时期,因为资源紧张、人力集中,不仅军队中容易出现疫情,民间也有可能爆发瘟疫。1940年夏天,林可胜光着上身、头包白布、一路步行,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随后,他又制订了“水与污染物管制计划”。先在长沙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对于减少战时疫情、提升部队战斗力,有不小的贡献。[1]
第四,难在战况多变。抗日救护总队成立于武汉汉口。因为战况吃紧,众人商议转移至祁阳。可惜“天不遂人愿”,战局变化太快。抗日救护总队刚赶到祁阳,就不得不再次开拨。几经辗转,最终选择了贵阳图云关落脚。图云关既是交通要道,也是不毛之地,救护队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住草棚、吃糙粮,靠着巨大的热情,支撑着自己的工作。[7]
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抗日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进行了11万9836次手术,收治了214万2997名住院患者。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奇
战争救护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难在凝聚人心。林先生虽然不是读死书的,但是难免有些书生的天真。抗日战争虽然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但历来,有干事儿的,就有拆台的。
林先生曾在香港接受一批国外左翼人士捐赠的药品、器械,然后运送给白求恩医院。为此,受到“亲共”的指责。对于国内各大战区,林先生也是一视同仁,不仅向西北地区运输物质,而且派出医疗队,到解放区和新四军工作。
在林可胜先生眼里,这是一场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战争,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不应该有门派之间,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里首先是中国,其次必须是国民党治下的中国。[8]
种种桩桩的摩擦,迫使林先生先后多次辞职,并最终在1942年离开抗战救护总队,进入中国远征军,帮助远征军开展救护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林可胜推辞了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职务,于1949年远赴美国。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林可胜一直没有忘记中国。
他一直关心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在英文刊物上引用中国文章的科学家。[9]可能是因为对战争的记忆太深,在晚年,林可胜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阿司匹林的镇痛机制。他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证实,阿司匹林是在外周发挥镇痛作用的。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1969年7月8日,林可胜先生因为癌症去世。但是,他对技艺的追求、对家国的热爱,将永远激励我们;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机敏练达、仁心仁术,更是早已成为一段传奇,永远流传。
--------------------------------------------------
参考文献
[1] 智效民. 民国时期的科学家 (之六)——林可胜与中国的红十字会[J]. 社会科学论坛, 2015(6): 162–167.
[2] 陈民. 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J]. 抗日战争研究, 1992, 4(2): 218.
[3] 讴歌. 协和医事[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汪子春, OTHERS. 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发展概况[J]. 中国科技史料, 1988, 2: 17–35.
[5] 陈适等. 国际肠抑胃素和肠促胰素研究的先驱: 北平协和医学院林可胜教授[J]. 协和医学杂志, 2017, 8(1): 76–79.
[6] 陈宜张. 记粟宗华, 王嘉祥, 林可胜 1936 年的小电泳实验[J]. 生理学报, 2011, 63(5): 477–478.
[7]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 “林可胜时期”(上)[J]. 南通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20(2): 1–6.
[8]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下) --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V6.5)[EB/OL]. [2017-07-12].
[9] 饶毅. 几被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 中国生理科学之父: 林可胜[J]. 中国神经科学杂志, 2001, 17(2): 171–172.
[10] BENEDETTI F. The patient’s brain: the neuroscience behi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此帖被十夜凉在2018-01-09 00:01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