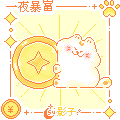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12日,山东威海卫的海面,寒风凛冽,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最高官员丁汝昌在北洋海军提督署留下绝命书,服毒自尽。这位表示“决不弃报国大义”慷慨赴死的将领,在身后却遭到了清廷“毋庸议恤”的冷遇,让人唏嘘不已。北洋舰队为何战败?丁汝昌为什么要自杀?他的死真的是胆怯无能,逃避罪责吗?这一切都要从59年前安徽庐江县乡村说起。
出入天国:个人自觉的迷失
丁汝昌于道光十六年(1836)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丁家坎村,早年经历颇为坎坷,曾经“被掠入伍”。
太平军过庐邑(1854年1月),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
“汝昌被掠”发生在太平军西征的路上。然而,从1851年金田起义,直至1853年定都天京,北伐、西征,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壮大难道都是靠“掠人入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洪秀全汲取基督教布道书的某些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和本土宗教相结合而提出的“拜上帝”主张,利用“拜上帝会”笼络人心,团结穷苦农民,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这场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广西地瘠民贫,人地矛盾尖锐;道光末年以来天灾频繁,民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来土之争”的白热化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鸦片战争更是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究其根源还在于“官府疲玩泄沓”“贪墨成风”,民不聊生之下,势必“铤而走险”。
不过,关于丁汝昌早年加入太平军的缘由,坊间传闻与陈诗《丁汝昌传》记载不符。戚其章先生调查发现,坊间皆传丁汝昌是主动投入太平军的,更有甚者提出,“业农”“家贫”的丁汝昌之所以主动投入,是受到《天朝田亩制度》的吸引,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
根据丁汝昌“家贫”“业农”的出身背景,以及《天朝田亩制度》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主张对农民阶级获得土地和追求社会财富平均等理想欲望的满足和吸引,结合时间线索的考证——《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于1853年,恰巧是丁汝昌加入太平天国的前一年,一切似乎都显得逻辑合理,水到渠成。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出于主观臆想,我们要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做到论从史出。下面这则史料可能会颠覆原先的认知。
此书(《天朝田亩制度》)贼中似未梓行……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
《天朝田亩制度》“似未梓行”,即没有公开刊印发行过,丁汝昌又怎么能见过呢?所以“受《天朝田亩制度》吸引而加入太平天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七年以后的1861年,丁汝昌在安庆战役中投降了“湘乡”曾国荃。
(1861年3月)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今安庆),学启(程学启,陈玉成部下)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
“湘乡”指的是曾国藩招募湖南乡勇组建的湘军,由于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腐败废弛、一战即溃,清廷不得不倚重湘军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武装来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他擅长挖战壕,人称“曾铁桶”,对太平军而言是不可小觑的劲敌。
关于太平天国降将群体的研究,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觉得是清廷策反起了效果,有人认为是天京事变后人心涣散;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军事形势变化的考虑,毕竟安庆被围,形势不利。然而,就丁汝昌个人投降动机而言,可供研究的史料相对匮乏,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撷取有效信息,找寻相关蛛丝马迹。
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可以得知,丁汝昌是跟着上司程学启投降的,是基于对上司的服从和效忠,他与程学启“倾怀效能,意气相得”也是导致其投降的重要诱因。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目前难以窥视丁汝昌此番抉择的动机全貌,对于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种,确定真实的情况;第二种,确定是假的或者虚构的;第三种,不能确定,只能存疑,存在多种可能性。丁汝昌从太平军反叛、投入清军是哪一种情况呢?当然是第三种情况。
可惜,湘军也不信任反叛的人,丁汝昌与他的大哥程学启只能用屠杀太平军来证明自己,他们成了湘军攻克安庆的功臣,才被信任。不久,李鸿章在曾国藩授意下组建淮军,淮军多是安徽人,丁汝昌于是改隶淮军。1861—1864年,湘军和淮军逐步逼近天京,最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作为农民阶级救亡图存的探索,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跳出从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改朝换代”轮回,“天京事变”将农民阶级“享乐主义”“等级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与保守彰显得淋漓尽致,尽管洪仁玕等人曾通过《资政新篇》对“农民革命应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过相应的探索,但受制于历史条件,终究未能实施。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其无法冲破封建秩序的藩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在传统的国家观念中,“朕即国家”“家国同构”,王朝与国家的概念是重合的,“忠君”便是“国家认同”的最佳诠释。在以丁汝昌为代表的传统官僚心目中,“大清”的兴衰沉浮便与“国家”命运裹挟在一起。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使一度濒临倾覆的清廷开始转危为安,并引发了传统政治与权力结构的嬗变。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战时型督抚”体系并没有因为天国的覆灭而解体,督抚在任免、保荐地方官吏上的自主权,在维系和扩张势力之余,也为兴办洋务觅求相关人才提供了些许便利。丁汝昌此后的宦海沉浮也与此息息相关。
作为地主阶级救亡图存的尝试,“兴办洋务”之举对国家命运的转圜是否有所裨益?为什么湘军和淮军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逐步取胜呢?
投身洋务:阶级自觉的桎梏
有人说,武器不同,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为湘军提供近代新式武器装备;然而,太平军也有火器,据外国侵略者回忆,1863年,苏州的太平军“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熗和来福熗”,其火器装备“精利”可见一斑。为什么太平军仍旧难逃失败的命运呢?
据《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若施放熗炮,命中致远,千百贼中无一能者……”,无论洋熗洋炮威力如何,打不准是没有战斗力的。而李鸿章的淮军“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依照洋人声口”,战斗力的提高,以洋熗队之“常胜军”首领戈登为代表的洋人教练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以冷兵器为主的八旗、绿营一蹶不振,面对新式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膨胀的湘军淮军,面对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中央权力下移,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深感恐慌,下令裁兵。
在裁兵令下,淮军中这位在“平吴剿捻”中立下赫赫战功,已然官至总兵的丁汝昌,不得不于1874年交卸营务,解甲归田。然而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已成定局,他们在洋务运动和边疆危机等重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丁汝昌个人的仕途命运而言,淮系的关键人物李鸿章是他的贵人,他能东山再起,李鸿章功不可没。
关于丁汝昌的东山再起,李鸿章于1879年撰写的《奏留丁汝昌片》中有详细的记载。
(丁汝昌)嗣因交卸营务,光绪三年(1877年)秋间给咨赴部……奉旨发往甘肃差遣……行至天津伤病复发,呈请咨部展限在案……准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以资造就。
时间定格在1877年,丁汝昌迎来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清廷派他去“甘肃差遣”,“甘肃差遣”有何玄机?为什么在此问题上,李鸿章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借口,从中斡旋阻挠呢?他要求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此举又折射出晚清国防战略怎样的争端?
首先,朝廷派丁汝昌去“甘肃差遣”,是为了配合湘系大员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新疆遭遇到了怎样的边患危机?英国支持浩罕国首领阿古柏入侵,沙俄也趁火打劫,侵占伊犁地区;然而,在西北边疆遭受蹂躏之际,东南海防也告急——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屡次侵扰东南沿海,附属国琉球被吞并,台湾也惨遭荼毒侵扰。
如此群狼环伺、烽烟四起之际,朝堂之上展开了一场针对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事业;而左宗棠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这场针对国防战略观点的交锋实际掺杂着派系利益之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李鸿章在丁汝昌“甘肃差遣”的问题上“从中作梗”了。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策略。
左宗棠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收复新疆,清政府也于1884年新疆建省,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认为海防乃“腹心之大患”的李鸿章,从1875年开始筹划北洋海防事宜。1879年,丁汝昌被受命“海防差遣",此后奉命去英国购买战舰,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始初见雏形。然而,由于政府财政支持向塞防倾斜,导致海防建设资金紧张,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海防再次告急。
中法战争使清政府深刻意识到台湾作为东南海防左护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性,1885年台湾建省,在加强对台湾地区管辖的同时,北洋舰队的筹建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在中法战争期间,发生了“甲申易枢之变”,恭亲王奕䜣集团被罢黜,醇亲王奕譞和孙毓汶集团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在时人的评述中,这次换班恰如“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此后“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闻”,在张謇看来,甲申易枢与甲午败局、戊戌政变、庚子拳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都是“因果相乘”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醇亲王出于与奕䜣的权力斗争考量,在客观上迎合了李鸿章等人的海防思想,促成了海军衙门的建立,又拨出厘金,保障了南北洋海军的经费供应。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有着近10年海军生涯的丁汝昌被任命为海军提督。而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近代新式海军,也是晚清“洋务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说起兴办“洋务新政”的缘由,1861年曾国藩的一份奏折中曾有过翔实的表述:“况今日和议既成……购买外洋器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名义上“和好”,外患却并未消除,国内依然面临“剿发逆”的难题,“发逆”即太平天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购买外洋器物可以镇压农民起义,可以以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封建统治。提倡洋务新政的代表人物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是封建官僚出身,因此,这场洋务运动显然是地主阶级的自救道路。
北洋海军需要炮弹,需要军舰,需要海军专业人才,也需要翻译人员与雇佣的“洋员”交流。除了数量稀少、造价昂贵的“开花弹”依赖进口,也配备了不少“国产”的里面掺沙子的实心弹,主要是天津军械局提供的。最大的兵工厂,则是江南制造总局,其机械化的布局与传统的手工工场有着天壤之别,使用机器生产,是近代工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洋务运动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初步尝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19世纪70年代以来,李鸿章花重金多次从海外购买军舰,其中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购自德国,是丁汝昌亲自验收接回的。北洋舰队也有国产舰,例如平远舰,由福州船政局生产。福州船政局除制造军舰外,还肩负起海军和工程技术教育、舰队编练管理等职能,为北洋海军培养了以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为代表的优秀海军专业人才,其中林永升、刘步蟾等人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在丁汝昌统领海军时,邓世昌已毕业,林永升等留学生也已归国,可为什么李鸿章舍弃专业人才,让邓世昌等人任“管带”(舰长),反而选用丁汝昌这个陆军出身的门外汉做北洋海军的提督?丁汝昌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李鸿章为什么要作此选择呢?
首先,在李鸿章的眼中,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作战勇武有才略,为人忠心;其次,丁汝昌在任北洋海军提督前已经有近10年的海军生涯,他为弥补业务能力的不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况且,他“剿平粤、捻各逆,迭著战功”,相对于“战阵实际概未阅历”的“学堂出身者”,丁汝昌丰富的实战经验也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李鸿章将北洋海军作为淮系势力消长的重要资本,丁汝昌淮军出身,是“自己人”,听话忠心,有利于他更好地控制北洋海军。
由于最高统治者慈禧和执掌大权的醇亲王集团人员平庸无能,顽固守旧势力阻力甚大,洋务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遭遇重重桎梏,终究难以形成举国共襄的行动,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为牟取私利任人唯亲已成常态。可是,面对救亡图存,需要的是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
尽管丁汝昌作战才略武勇,也不缺乏忠诚,但他治军下的北洋舰队却军纪涣散,“训练无实”,衙门习气甚重,令人忧心。北洋舰队,这支曾经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近代海军,真的是一支近代化了的部队吗?当军队编制和领导体系还停留在旧的封建军事制度上时,武器的近代化只是虚有其表,行之不远。这是由办洋务的初衷所决定的,洋务派超越不了阶级利益的桎梏,将阶级集团利益放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近代化又何以能行稳致远呢?
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对手也变了,丁汝昌将要面对的不是落后的农民军,而是正在崛起的日本。
拒敌甲午:民族自决的悲呼
甲午战争的最后关头,当日军完成对威海卫的海陆夹攻之势时,整个刘公岛上士气低落,绝望颓丧,“衰求生路”的乞降之声蔓延开来,“弹药将罄,援军绝”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场面,局面为什么会如此不堪?
长久以来,史学界都对山东巡抚李秉衡诟病不已,认为他是出于派系斗争的缘故而对北洋舰队见死不救,丁汝昌在《致戴宗骞书》中曾提及军情危急之际,“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以李秉衡为代表的清流派就曾弹劾丁汝昌“贻误军机”,要求将其明正典刑,以慑将士。这些指责亦多为不实。可是,李秉衡也并非在国难当头完全隔岸观火、置身事外,他招募新兵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在国难当头,我们居然看不到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昂扬斗志,麻木、冷漠和退缩让人痛心疾首,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谈何救亡图存,谈何强国御侮呢?
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绝非个人因素,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在致丁汝昌的劝降书中曾一针见血提出溃败根源,“墨守常经,不通变”——三十年洋务,单纯引进西方先进军事和生产技术,而不触及封建制度的变革,失败是必然的,甲午战争之败,实际上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面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一次大溃败。一个政府,太后的六十大寿排场都比海防事业重要,如此不辨轻重缓急,是何等的腐朽和冥顽不灵?
既然甲午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并非丁汝昌,为何他要选择自杀?有人说他通过自杀向皇帝表明忠心,因为军中有人乞降,向他乞求生路,而丁汝昌不愿意投降,但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他为下令炸船以免资敌却无人响应而深感绝望,为了表明对皇帝的忠心,他只能自杀殉国以表忠心。
可是我们再看一则材料。
清廷最高当局是否主张北洋海军株守军港呢?否!……即使李鸿章的指示有不明确……甚至与清廷有抵牾之处,丁汝昌也应坚决执行清廷的决策而不得踌躇延误。但是,丁汝昌却始终率领舰队株守军港坐以待毙……
躲进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的指令是皇帝下的吗?清廷最高当局赞同这个方案吗?作为海军提督的丁汝昌,深知躲进威海卫港实乃兵家之大忌。他在遗书中,毫不隐讳表达了这一点。可是他为什么还要选择“株守”威海卫军港坐以待毙这个极端愚蠢的行为?因为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指示,因为地方势力崛起后中央权力下移,因为北洋海军受北洋大臣的节制,更因为李鸿章对他“蒙恩殊遇”,他又是如此忠心、听话的人,面对战败罪责的承担,他唯有一死以报李鸿章知遇之恩。
“忠心”二字是丁汝昌命运的枷锁,他的悲剧是时代的缩影,他的个人沉浮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晚清波诡云谲的权力政治中,他身不由己。时代赋予了他,一个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不能承受之重。
甲午战争的惨败改变了远东国际局势,蕞尔小国的日本击败了所谓“亚洲强国”——大清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巨大利益刺激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泰晤士报》的记者吉尔乐就曾断言:“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光绪皇帝表示要“痛除积弊”、续谋自强,为“筹饷练兵”“恤商惠工”令各地条陈时务,为接踵而至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作了初步准备;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梁启超曾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偿二百兆始。”在激发强国御侮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中国各阶层仁人志士也在寻求救亡新路,在梁启超看来,洋务派败在舍本逐末,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将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甲午战争还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力图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求“申民志而扶国宗”;而农民阶级从反洋教的斗争发展成席卷山东、直隶的义和团运动,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口号的变迁,正是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力求救亡图存的鲜明反映。
“近代国家”的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朕即国家”观,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国家命运几经起落,农民阶级不能救中国,地主阶级的“自强”道路广受抨击,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中道崩殂,清王朝最终命运如何?中华民族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真正地实现救亡图存?
1895年2月12日的威海卫。丁汝昌自杀之前,很可能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成为反叛的太平军,又进入湘军,改隶淮军,逐步成为赫赫有名的清军将领,最后成为当时东亚第一舰队的提督。面对败局,他只求一死,为了自己信赖的上司,也为了朝廷的名誉,或许还有义无反顾的几分悲壮!至于大清的结局,丁汝昌无从想起,也无法知晓。17年之后,公历1912年2月12日,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曾经的帝国便轰然倒塌。其实,甲午战争是两国血与火的考场,北洋舰队的覆亡,既是结果,一战定胜负,又是先兆,预示着一个王朝行将灭亡。
当然,严重的民族危机也蕴含着机遇。中国下一步该如何走?未来在哪里?路在何方,如何抉择,历史自有它自己的理性和逻辑。
出入天国:个人自觉的迷失
丁汝昌于道光十六年(1836)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丁家坎村,早年经历颇为坎坷,曾经“被掠入伍”。
太平军过庐邑(1854年1月),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
“汝昌被掠”发生在太平军西征的路上。然而,从1851年金田起义,直至1853年定都天京,北伐、西征,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壮大难道都是靠“掠人入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洪秀全汲取基督教布道书的某些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和本土宗教相结合而提出的“拜上帝”主张,利用“拜上帝会”笼络人心,团结穷苦农民,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这场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广西地瘠民贫,人地矛盾尖锐;道光末年以来天灾频繁,民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来土之争”的白热化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鸦片战争更是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究其根源还在于“官府疲玩泄沓”“贪墨成风”,民不聊生之下,势必“铤而走险”。
不过,关于丁汝昌早年加入太平军的缘由,坊间传闻与陈诗《丁汝昌传》记载不符。戚其章先生调查发现,坊间皆传丁汝昌是主动投入太平军的,更有甚者提出,“业农”“家贫”的丁汝昌之所以主动投入,是受到《天朝田亩制度》的吸引,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
根据丁汝昌“家贫”“业农”的出身背景,以及《天朝田亩制度》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主张对农民阶级获得土地和追求社会财富平均等理想欲望的满足和吸引,结合时间线索的考证——《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于1853年,恰巧是丁汝昌加入太平天国的前一年,一切似乎都显得逻辑合理,水到渠成。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出于主观臆想,我们要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做到论从史出。下面这则史料可能会颠覆原先的认知。
此书(《天朝田亩制度》)贼中似未梓行……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
《天朝田亩制度》“似未梓行”,即没有公开刊印发行过,丁汝昌又怎么能见过呢?所以“受《天朝田亩制度》吸引而加入太平天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七年以后的1861年,丁汝昌在安庆战役中投降了“湘乡”曾国荃。
(1861年3月)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今安庆),学启(程学启,陈玉成部下)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
“湘乡”指的是曾国藩招募湖南乡勇组建的湘军,由于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腐败废弛、一战即溃,清廷不得不倚重湘军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武装来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他擅长挖战壕,人称“曾铁桶”,对太平军而言是不可小觑的劲敌。
关于太平天国降将群体的研究,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觉得是清廷策反起了效果,有人认为是天京事变后人心涣散;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军事形势变化的考虑,毕竟安庆被围,形势不利。然而,就丁汝昌个人投降动机而言,可供研究的史料相对匮乏,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撷取有效信息,找寻相关蛛丝马迹。
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可以得知,丁汝昌是跟着上司程学启投降的,是基于对上司的服从和效忠,他与程学启“倾怀效能,意气相得”也是导致其投降的重要诱因。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目前难以窥视丁汝昌此番抉择的动机全貌,对于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种,确定真实的情况;第二种,确定是假的或者虚构的;第三种,不能确定,只能存疑,存在多种可能性。丁汝昌从太平军反叛、投入清军是哪一种情况呢?当然是第三种情况。
可惜,湘军也不信任反叛的人,丁汝昌与他的大哥程学启只能用屠杀太平军来证明自己,他们成了湘军攻克安庆的功臣,才被信任。不久,李鸿章在曾国藩授意下组建淮军,淮军多是安徽人,丁汝昌于是改隶淮军。1861—1864年,湘军和淮军逐步逼近天京,最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作为农民阶级救亡图存的探索,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跳出从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改朝换代”轮回,“天京事变”将农民阶级“享乐主义”“等级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与保守彰显得淋漓尽致,尽管洪仁玕等人曾通过《资政新篇》对“农民革命应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过相应的探索,但受制于历史条件,终究未能实施。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其无法冲破封建秩序的藩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在传统的国家观念中,“朕即国家”“家国同构”,王朝与国家的概念是重合的,“忠君”便是“国家认同”的最佳诠释。在以丁汝昌为代表的传统官僚心目中,“大清”的兴衰沉浮便与“国家”命运裹挟在一起。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使一度濒临倾覆的清廷开始转危为安,并引发了传统政治与权力结构的嬗变。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战时型督抚”体系并没有因为天国的覆灭而解体,督抚在任免、保荐地方官吏上的自主权,在维系和扩张势力之余,也为兴办洋务觅求相关人才提供了些许便利。丁汝昌此后的宦海沉浮也与此息息相关。
作为地主阶级救亡图存的尝试,“兴办洋务”之举对国家命运的转圜是否有所裨益?为什么湘军和淮军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逐步取胜呢?
投身洋务:阶级自觉的桎梏
有人说,武器不同,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为湘军提供近代新式武器装备;然而,太平军也有火器,据外国侵略者回忆,1863年,苏州的太平军“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熗和来福熗”,其火器装备“精利”可见一斑。为什么太平军仍旧难逃失败的命运呢?
据《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若施放熗炮,命中致远,千百贼中无一能者……”,无论洋熗洋炮威力如何,打不准是没有战斗力的。而李鸿章的淮军“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依照洋人声口”,战斗力的提高,以洋熗队之“常胜军”首领戈登为代表的洋人教练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以冷兵器为主的八旗、绿营一蹶不振,面对新式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膨胀的湘军淮军,面对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中央权力下移,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深感恐慌,下令裁兵。
在裁兵令下,淮军中这位在“平吴剿捻”中立下赫赫战功,已然官至总兵的丁汝昌,不得不于1874年交卸营务,解甲归田。然而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已成定局,他们在洋务运动和边疆危机等重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丁汝昌个人的仕途命运而言,淮系的关键人物李鸿章是他的贵人,他能东山再起,李鸿章功不可没。
关于丁汝昌的东山再起,李鸿章于1879年撰写的《奏留丁汝昌片》中有详细的记载。
(丁汝昌)嗣因交卸营务,光绪三年(1877年)秋间给咨赴部……奉旨发往甘肃差遣……行至天津伤病复发,呈请咨部展限在案……准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以资造就。
时间定格在1877年,丁汝昌迎来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清廷派他去“甘肃差遣”,“甘肃差遣”有何玄机?为什么在此问题上,李鸿章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借口,从中斡旋阻挠呢?他要求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此举又折射出晚清国防战略怎样的争端?
首先,朝廷派丁汝昌去“甘肃差遣”,是为了配合湘系大员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新疆遭遇到了怎样的边患危机?英国支持浩罕国首领阿古柏入侵,沙俄也趁火打劫,侵占伊犁地区;然而,在西北边疆遭受蹂躏之际,东南海防也告急——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屡次侵扰东南沿海,附属国琉球被吞并,台湾也惨遭荼毒侵扰。
如此群狼环伺、烽烟四起之际,朝堂之上展开了一场针对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事业;而左宗棠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这场针对国防战略观点的交锋实际掺杂着派系利益之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李鸿章在丁汝昌“甘肃差遣”的问题上“从中作梗”了。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策略。
左宗棠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收复新疆,清政府也于1884年新疆建省,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认为海防乃“腹心之大患”的李鸿章,从1875年开始筹划北洋海防事宜。1879年,丁汝昌被受命“海防差遣",此后奉命去英国购买战舰,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始初见雏形。然而,由于政府财政支持向塞防倾斜,导致海防建设资金紧张,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海防再次告急。
中法战争使清政府深刻意识到台湾作为东南海防左护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性,1885年台湾建省,在加强对台湾地区管辖的同时,北洋舰队的筹建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在中法战争期间,发生了“甲申易枢之变”,恭亲王奕䜣集团被罢黜,醇亲王奕譞和孙毓汶集团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在时人的评述中,这次换班恰如“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此后“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闻”,在张謇看来,甲申易枢与甲午败局、戊戌政变、庚子拳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都是“因果相乘”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醇亲王出于与奕䜣的权力斗争考量,在客观上迎合了李鸿章等人的海防思想,促成了海军衙门的建立,又拨出厘金,保障了南北洋海军的经费供应。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有着近10年海军生涯的丁汝昌被任命为海军提督。而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近代新式海军,也是晚清“洋务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说起兴办“洋务新政”的缘由,1861年曾国藩的一份奏折中曾有过翔实的表述:“况今日和议既成……购买外洋器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名义上“和好”,外患却并未消除,国内依然面临“剿发逆”的难题,“发逆”即太平天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购买外洋器物可以镇压农民起义,可以以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封建统治。提倡洋务新政的代表人物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是封建官僚出身,因此,这场洋务运动显然是地主阶级的自救道路。
北洋海军需要炮弹,需要军舰,需要海军专业人才,也需要翻译人员与雇佣的“洋员”交流。除了数量稀少、造价昂贵的“开花弹”依赖进口,也配备了不少“国产”的里面掺沙子的实心弹,主要是天津军械局提供的。最大的兵工厂,则是江南制造总局,其机械化的布局与传统的手工工场有着天壤之别,使用机器生产,是近代工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洋务运动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初步尝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19世纪70年代以来,李鸿章花重金多次从海外购买军舰,其中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购自德国,是丁汝昌亲自验收接回的。北洋舰队也有国产舰,例如平远舰,由福州船政局生产。福州船政局除制造军舰外,还肩负起海军和工程技术教育、舰队编练管理等职能,为北洋海军培养了以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为代表的优秀海军专业人才,其中林永升、刘步蟾等人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在丁汝昌统领海军时,邓世昌已毕业,林永升等留学生也已归国,可为什么李鸿章舍弃专业人才,让邓世昌等人任“管带”(舰长),反而选用丁汝昌这个陆军出身的门外汉做北洋海军的提督?丁汝昌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李鸿章为什么要作此选择呢?
首先,在李鸿章的眼中,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作战勇武有才略,为人忠心;其次,丁汝昌在任北洋海军提督前已经有近10年的海军生涯,他为弥补业务能力的不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况且,他“剿平粤、捻各逆,迭著战功”,相对于“战阵实际概未阅历”的“学堂出身者”,丁汝昌丰富的实战经验也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李鸿章将北洋海军作为淮系势力消长的重要资本,丁汝昌淮军出身,是“自己人”,听话忠心,有利于他更好地控制北洋海军。
由于最高统治者慈禧和执掌大权的醇亲王集团人员平庸无能,顽固守旧势力阻力甚大,洋务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遭遇重重桎梏,终究难以形成举国共襄的行动,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为牟取私利任人唯亲已成常态。可是,面对救亡图存,需要的是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
尽管丁汝昌作战才略武勇,也不缺乏忠诚,但他治军下的北洋舰队却军纪涣散,“训练无实”,衙门习气甚重,令人忧心。北洋舰队,这支曾经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近代海军,真的是一支近代化了的部队吗?当军队编制和领导体系还停留在旧的封建军事制度上时,武器的近代化只是虚有其表,行之不远。这是由办洋务的初衷所决定的,洋务派超越不了阶级利益的桎梏,将阶级集团利益放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近代化又何以能行稳致远呢?
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对手也变了,丁汝昌将要面对的不是落后的农民军,而是正在崛起的日本。
拒敌甲午:民族自决的悲呼
甲午战争的最后关头,当日军完成对威海卫的海陆夹攻之势时,整个刘公岛上士气低落,绝望颓丧,“衰求生路”的乞降之声蔓延开来,“弹药将罄,援军绝”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场面,局面为什么会如此不堪?
长久以来,史学界都对山东巡抚李秉衡诟病不已,认为他是出于派系斗争的缘故而对北洋舰队见死不救,丁汝昌在《致戴宗骞书》中曾提及军情危急之际,“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以李秉衡为代表的清流派就曾弹劾丁汝昌“贻误军机”,要求将其明正典刑,以慑将士。这些指责亦多为不实。可是,李秉衡也并非在国难当头完全隔岸观火、置身事外,他招募新兵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在国难当头,我们居然看不到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昂扬斗志,麻木、冷漠和退缩让人痛心疾首,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谈何救亡图存,谈何强国御侮呢?
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绝非个人因素,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在致丁汝昌的劝降书中曾一针见血提出溃败根源,“墨守常经,不通变”——三十年洋务,单纯引进西方先进军事和生产技术,而不触及封建制度的变革,失败是必然的,甲午战争之败,实际上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面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一次大溃败。一个政府,太后的六十大寿排场都比海防事业重要,如此不辨轻重缓急,是何等的腐朽和冥顽不灵?
既然甲午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并非丁汝昌,为何他要选择自杀?有人说他通过自杀向皇帝表明忠心,因为军中有人乞降,向他乞求生路,而丁汝昌不愿意投降,但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他为下令炸船以免资敌却无人响应而深感绝望,为了表明对皇帝的忠心,他只能自杀殉国以表忠心。
可是我们再看一则材料。
清廷最高当局是否主张北洋海军株守军港呢?否!……即使李鸿章的指示有不明确……甚至与清廷有抵牾之处,丁汝昌也应坚决执行清廷的决策而不得踌躇延误。但是,丁汝昌却始终率领舰队株守军港坐以待毙……
躲进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的指令是皇帝下的吗?清廷最高当局赞同这个方案吗?作为海军提督的丁汝昌,深知躲进威海卫港实乃兵家之大忌。他在遗书中,毫不隐讳表达了这一点。可是他为什么还要选择“株守”威海卫军港坐以待毙这个极端愚蠢的行为?因为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指示,因为地方势力崛起后中央权力下移,因为北洋海军受北洋大臣的节制,更因为李鸿章对他“蒙恩殊遇”,他又是如此忠心、听话的人,面对战败罪责的承担,他唯有一死以报李鸿章知遇之恩。
“忠心”二字是丁汝昌命运的枷锁,他的悲剧是时代的缩影,他的个人沉浮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晚清波诡云谲的权力政治中,他身不由己。时代赋予了他,一个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不能承受之重。
甲午战争的惨败改变了远东国际局势,蕞尔小国的日本击败了所谓“亚洲强国”——大清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巨大利益刺激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泰晤士报》的记者吉尔乐就曾断言:“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光绪皇帝表示要“痛除积弊”、续谋自强,为“筹饷练兵”“恤商惠工”令各地条陈时务,为接踵而至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作了初步准备;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梁启超曾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偿二百兆始。”在激发强国御侮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中国各阶层仁人志士也在寻求救亡新路,在梁启超看来,洋务派败在舍本逐末,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将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甲午战争还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力图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求“申民志而扶国宗”;而农民阶级从反洋教的斗争发展成席卷山东、直隶的义和团运动,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口号的变迁,正是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力求救亡图存的鲜明反映。
“近代国家”的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朕即国家”观,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国家命运几经起落,农民阶级不能救中国,地主阶级的“自强”道路广受抨击,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中道崩殂,清王朝最终命运如何?中华民族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真正地实现救亡图存?
1895年2月12日的威海卫。丁汝昌自杀之前,很可能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成为反叛的太平军,又进入湘军,改隶淮军,逐步成为赫赫有名的清军将领,最后成为当时东亚第一舰队的提督。面对败局,他只求一死,为了自己信赖的上司,也为了朝廷的名誉,或许还有义无反顾的几分悲壮!至于大清的结局,丁汝昌无从想起,也无法知晓。17年之后,公历1912年2月12日,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曾经的帝国便轰然倒塌。其实,甲午战争是两国血与火的考场,北洋舰队的覆亡,既是结果,一战定胜负,又是先兆,预示着一个王朝行将灭亡。
当然,严重的民族危机也蕴含着机遇。中国下一步该如何走?未来在哪里?路在何方,如何抉择,历史自有它自己的理性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