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井》
—
本帖被 逆° 从 原创小说 移动到本区(2016-03-31)
—
心就像是一口干枯的井,朝外面无声地望着,失望到绝望,一步之遥。可是当一滴滴雨水滋润这口井的时候,阳光和风来临,也许希望也到来了罢。
井水无波,扭曲的脸蛋还是能看出几分清俊,额前的头发又调皮地跳到前面去了,这女人自从三个月前来到这个贫苦之家,她就没想过能过什么好日子。阿月,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也许就只能拥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她坐在井旁边向这个小院子四处张望时,她知道自己很想很想————回家。
家中有三口人,爹是个穷酸教书先生,弟弟还小才六岁,剩下的就是只有穿着短了一大截的裤子的阿月。弟弟时常和村口的阿花玩耍,两小无猜,童年,即使是贫穷的童年也是充满乐趣和欢笑的泡泡。
这天清晨,瓜瓢舀了一盆水放在弟弟的炕头上,又给院子里的鸡鸭喂了食。准备完了动物们的吃食,就该准备人的吃食了。她还是不习惯这里的菜的味道,苦苦涩涩的,而且爹一再嘱咐盐巴少放点,家里紧巴,哎有啥法。
今天是弟弟的生日,阿月老早就听见弟弟闹了,要吃野菜粥,于是早上就用家中所剩不多的米做了一顿野菜粥。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是几辈子也没有吃过这般好吃的东西,弟弟投胎总是闭着眼的罢。阿月想起自己的家,家中就她独女,父母经常在外面,好吃的好玩的自然能够带回来给她一个人独占,那时候望着家中的那口古老的钟,滴答滴答,等待他们回家是最无聊的时光,单调且乏味,比现在吃野菜更为艰涩。
“姐,把你铜镜借给我好吗?阿花要。”弟弟一脸坚毅,从村口玩耍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什么铜镜,天知道阿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她撩开布帘,进了自己房间,四处张望,目标最终还是放在一个,家中唯一的大柜子上,于是大柜子中间好几个小柜子里翻来拣去,针线不是,布娃娃不是,红绸带子不是,最后翻出一本看起来很古朴的旧书,刚把书拿起来准备放下,就看见书的背面压着的就是一面铜镜,镶得甚是好看,这个定是这个家中的娘遗留下来的。
叮嘱弟弟一定要小心,这个铜镜借给别人要问好还的日期。
把水烧好,爹回来时要喝热乎乎的茶,这个是他唯一的能享受不多的爱好了。做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阿月好奇地翻开从房间里找到的一本书,原本她以为那定是什么体什么体写就的诗画文章,第一页翻开,她的手竟然发抖,她的嘴唇舔了舔觉得有些干涸,心跳到了嗓子眼快要蹦了出来,眼睛一热:那个竟然是用钢笔写的简体字,久违的现代用具,久违而熟悉的字样。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种日记。它记述了一个女人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时空,所有的感受,从不敢相信到焦虑,从四面楚歌到重获新生,阿月一页一页地翻看,她的泪眼迷蒙,她何尝不曾有过和她同样的感受呢。后来那个女人遇到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书生,相遇相知,最终两人相爱,有子。
从时光的缝隙中稍稍抬了抬头,探出去,看着茫茫的天空,云霞惨红。
书写到十页后字迹越来越潦草,模糊不清,看来墨水快要用完了,终于那个女人提到她似乎找到了回去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当她要写出来的时候,竟然没有墨了,翻开后面,只是一页页的白纸,什么也没有。
阿月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她告诉自己要镇静,要沉着,一定有什么是她忽略的,那个女人最后没有写出来具体的方法,不代表一切就没有希望了。
她把书放到桌上,这本书上的字与这个时代的字完全不同,她一点也不担心别人能够看懂。如果爹问起她就回答是拿来准备垫桌子脚的。
她看天色已晚,于是又去喂家中的鸡鸭。
在她忙活完的时候,爹回来了,他疲惫地放下书袋子,背微微有点驼,他的表情总是有些愁苦,只有在提到娘的时候才显出几分才子的清绝光亮。
“阿月,我都听阿花的哥哥提起你把家里你娘的铜镜借给他们家了,什么时候你必须得拉下这个脸去要回来,而且越快越好。”爹喝了一口热茶,他把包里的束脩全都交到阿月的手心里。
“为啥哩,爹?”阿月还是有些不习惯这个地方的口音,真的很别扭。
爹来回走了几步,手背在后面,像是想什么大事情:“过了年,你就该嫁人了,你娘的那面铜镜可是决不能缺少的嫁妆。”
“爹,俺不想嫁人。”阿月摇头,她想回家。
爹的脸色像融化的冰水,他笑着说:“阿月,爹总是盼着你好的,有了自己的家,你才有了真正的依靠,到时候什么事情都有人分担,那种幸福喜悦,甚至是甜蜜是爹和你弟给不了你的。”
阿月闪神,她想爹一定很爱自己的子女,因为他太爱那个为他生了一双儿女的娘。而那个书中提到的女人她隐约猜到是谁了。
回想起现代的家,父母总是相敬如宾,互相冷漠以对,只有工作才是重要的事情。
她的童年总是在左和右中生存,左边是爸爸,右边是妈妈,一个叫她写作业,一个叫她看电视。
这天晚上阿月做了一个很混乱的梦,梦里有高楼大厦,也有农家小院,一个是爹的脸,一个是妈妈的脸,还有一汪清澈澈的水井。
早晨很早阿月就醒了,她已经习惯早起。日子日复一日的过着,人就像陀螺一刻也不得闲着。
上午看着弟弟带着阿花来家中玩耍,两人玩着跳房子,这个还是阿月指点的功劳。
她把那本书放在木墩上,看了几页随后又想起院子里的菜还没有摘。她又忙活去了,筲箕里满是白菜,这个腌泡菜最好吃了。她向房间的厨房走去,路过门口的时候,一阵风吹来,木墩上的书一角被翻开,随后风像是和书页玩起了游戏,它调皮地吹起,于是书一页又一页地翻开,阿月停下来看得有趣。她发觉每次停留的时候,她都能看到几段描写,那些描写里都提到了一口井。猛地,阿月手中的筲箕跌落,什么,井,难道那个就是通往另一个时空的隧道!天哪,我能够回去了。
一天很快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只有阿月知道她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她很想立即就跳下井里去,可是她的心又隐隐约约告诉她不可以。
她终于还是翻下床,她犹豫了一下,进了爹的房间,在对着床的方向阿月跪了下来,她怔怔地看着爹的睡颜,身边还窝着弟弟,嘴角挂着一滩口水。冷风灌了进来,弟弟缩了缩头猫着小腰往爹的怀里挤。阿月看了弟弟可爱的样子,微微一笑,她起身进了几步拉过薄薄的被子,粘着脖子往两人身上盖,弟弟突然说了一句梦话,听不大清楚完整了,只有零星的几个字“姐吃……”阿月眼睛酸涩,她不知道为何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能够让她的心这般柔软,温暖,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心硬如石了。
可是她想回家,她扭头,关上门,逃也似得离开。
水井晚上都很安静,只有“咚”地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了进去。
天渐渐亮,弟弟睁开双眼觉得有些不安,往常这时候姐姐一般都来叫自己了啊。
他迅速穿好衣服到姐姐的房间,人怎么不在了。
他急得到处乱窜,呀呀地叫“姐”可是姐不在了谁来答应他呢。
当他哭得昏天暗地时,阿月推开院子的门,她手里是扯来的新布:“傻弟弟,我这不是回家了嘛!”
井水无波,扭曲的脸蛋还是能看出几分清俊,额前的头发又调皮地跳到前面去了,这女人自从三个月前来到这个贫苦之家,她就没想过能过什么好日子。阿月,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也许就只能拥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她坐在井旁边向这个小院子四处张望时,她知道自己很想很想————回家。
家中有三口人,爹是个穷酸教书先生,弟弟还小才六岁,剩下的就是只有穿着短了一大截的裤子的阿月。弟弟时常和村口的阿花玩耍,两小无猜,童年,即使是贫穷的童年也是充满乐趣和欢笑的泡泡。
这天清晨,瓜瓢舀了一盆水放在弟弟的炕头上,又给院子里的鸡鸭喂了食。准备完了动物们的吃食,就该准备人的吃食了。她还是不习惯这里的菜的味道,苦苦涩涩的,而且爹一再嘱咐盐巴少放点,家里紧巴,哎有啥法。
今天是弟弟的生日,阿月老早就听见弟弟闹了,要吃野菜粥,于是早上就用家中所剩不多的米做了一顿野菜粥。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是几辈子也没有吃过这般好吃的东西,弟弟投胎总是闭着眼的罢。阿月想起自己的家,家中就她独女,父母经常在外面,好吃的好玩的自然能够带回来给她一个人独占,那时候望着家中的那口古老的钟,滴答滴答,等待他们回家是最无聊的时光,单调且乏味,比现在吃野菜更为艰涩。
“姐,把你铜镜借给我好吗?阿花要。”弟弟一脸坚毅,从村口玩耍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什么铜镜,天知道阿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她撩开布帘,进了自己房间,四处张望,目标最终还是放在一个,家中唯一的大柜子上,于是大柜子中间好几个小柜子里翻来拣去,针线不是,布娃娃不是,红绸带子不是,最后翻出一本看起来很古朴的旧书,刚把书拿起来准备放下,就看见书的背面压着的就是一面铜镜,镶得甚是好看,这个定是这个家中的娘遗留下来的。
叮嘱弟弟一定要小心,这个铜镜借给别人要问好还的日期。
把水烧好,爹回来时要喝热乎乎的茶,这个是他唯一的能享受不多的爱好了。做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阿月好奇地翻开从房间里找到的一本书,原本她以为那定是什么体什么体写就的诗画文章,第一页翻开,她的手竟然发抖,她的嘴唇舔了舔觉得有些干涸,心跳到了嗓子眼快要蹦了出来,眼睛一热:那个竟然是用钢笔写的简体字,久违的现代用具,久违而熟悉的字样。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种日记。它记述了一个女人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时空,所有的感受,从不敢相信到焦虑,从四面楚歌到重获新生,阿月一页一页地翻看,她的泪眼迷蒙,她何尝不曾有过和她同样的感受呢。后来那个女人遇到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书生,相遇相知,最终两人相爱,有子。
从时光的缝隙中稍稍抬了抬头,探出去,看着茫茫的天空,云霞惨红。
书写到十页后字迹越来越潦草,模糊不清,看来墨水快要用完了,终于那个女人提到她似乎找到了回去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当她要写出来的时候,竟然没有墨了,翻开后面,只是一页页的白纸,什么也没有。
阿月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她告诉自己要镇静,要沉着,一定有什么是她忽略的,那个女人最后没有写出来具体的方法,不代表一切就没有希望了。
她把书放到桌上,这本书上的字与这个时代的字完全不同,她一点也不担心别人能够看懂。如果爹问起她就回答是拿来准备垫桌子脚的。
她看天色已晚,于是又去喂家中的鸡鸭。
在她忙活完的时候,爹回来了,他疲惫地放下书袋子,背微微有点驼,他的表情总是有些愁苦,只有在提到娘的时候才显出几分才子的清绝光亮。
“阿月,我都听阿花的哥哥提起你把家里你娘的铜镜借给他们家了,什么时候你必须得拉下这个脸去要回来,而且越快越好。”爹喝了一口热茶,他把包里的束脩全都交到阿月的手心里。
“为啥哩,爹?”阿月还是有些不习惯这个地方的口音,真的很别扭。
爹来回走了几步,手背在后面,像是想什么大事情:“过了年,你就该嫁人了,你娘的那面铜镜可是决不能缺少的嫁妆。”
“爹,俺不想嫁人。”阿月摇头,她想回家。
爹的脸色像融化的冰水,他笑着说:“阿月,爹总是盼着你好的,有了自己的家,你才有了真正的依靠,到时候什么事情都有人分担,那种幸福喜悦,甚至是甜蜜是爹和你弟给不了你的。”
阿月闪神,她想爹一定很爱自己的子女,因为他太爱那个为他生了一双儿女的娘。而那个书中提到的女人她隐约猜到是谁了。
回想起现代的家,父母总是相敬如宾,互相冷漠以对,只有工作才是重要的事情。
她的童年总是在左和右中生存,左边是爸爸,右边是妈妈,一个叫她写作业,一个叫她看电视。
这天晚上阿月做了一个很混乱的梦,梦里有高楼大厦,也有农家小院,一个是爹的脸,一个是妈妈的脸,还有一汪清澈澈的水井。
早晨很早阿月就醒了,她已经习惯早起。日子日复一日的过着,人就像陀螺一刻也不得闲着。
上午看着弟弟带着阿花来家中玩耍,两人玩着跳房子,这个还是阿月指点的功劳。
她把那本书放在木墩上,看了几页随后又想起院子里的菜还没有摘。她又忙活去了,筲箕里满是白菜,这个腌泡菜最好吃了。她向房间的厨房走去,路过门口的时候,一阵风吹来,木墩上的书一角被翻开,随后风像是和书页玩起了游戏,它调皮地吹起,于是书一页又一页地翻开,阿月停下来看得有趣。她发觉每次停留的时候,她都能看到几段描写,那些描写里都提到了一口井。猛地,阿月手中的筲箕跌落,什么,井,难道那个就是通往另一个时空的隧道!天哪,我能够回去了。
一天很快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只有阿月知道她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她很想立即就跳下井里去,可是她的心又隐隐约约告诉她不可以。
她终于还是翻下床,她犹豫了一下,进了爹的房间,在对着床的方向阿月跪了下来,她怔怔地看着爹的睡颜,身边还窝着弟弟,嘴角挂着一滩口水。冷风灌了进来,弟弟缩了缩头猫着小腰往爹的怀里挤。阿月看了弟弟可爱的样子,微微一笑,她起身进了几步拉过薄薄的被子,粘着脖子往两人身上盖,弟弟突然说了一句梦话,听不大清楚完整了,只有零星的几个字“姐吃……”阿月眼睛酸涩,她不知道为何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能够让她的心这般柔软,温暖,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心硬如石了。
可是她想回家,她扭头,关上门,逃也似得离开。
水井晚上都很安静,只有“咚”地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了进去。
天渐渐亮,弟弟睁开双眼觉得有些不安,往常这时候姐姐一般都来叫自己了啊。
他迅速穿好衣服到姐姐的房间,人怎么不在了。
他急得到处乱窜,呀呀地叫“姐”可是姐不在了谁来答应他呢。
当他哭得昏天暗地时,阿月推开院子的门,她手里是扯来的新布:“傻弟弟,我这不是回家了嘛!”
[ 此贴被煞在2011-03-04 11:24重新编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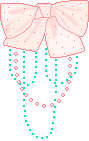

 忽略上面的话 表示我很喜欢这篇啊~~(^o^)/~
忽略上面的话 表示我很喜欢这篇啊~~(^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