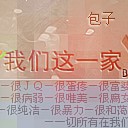一
我叫鑫儿。
从小,我就不喜欢这个名字。小时候是因为它笔划太多,懂事后则是因为总觉得被这三个“金”字压着,会喘不过气来。
每次向娘抱怨,娘总会扬着她那如孔雀般高傲的头,理直气壮地说,宰相家的女儿自然是金枝玉叶,不用金子来装饰,怎么能凸显高贵?
看着她满头的翠玉金钗,我不由得很疑惑,照娘的理论,那么耕地的人都该叫“垚”,水上人家都该叫“淼”,厨师离不开灶台只好叫“焱”,爹严肃古板像块石头应当叫“磊”,夫君木讷无趣自然该叫“森”罗……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停——我有点惊慌地捂住嘴,四下张望了一下。还好没人,宰相府里可不允许这般没规矩的乱笑,笑不露齿,行不露足可是大家闺秀最基本的规范!
突然觉得好累啊,反正四周无人,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哈欠。
算了,思考本不是咱们大家闺秀该做的,回房再睡个回笼觉吧。
穿过曲径,我遥遥忘向我的闺房,在一片竹林的掩映下,我的听竹轩显得分外的苍翠怡人。我喜欢绿色,因为它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与这死气沉沉地府邸正好相反的颜色。
透过卧房敞开的窗户,我竟看到了“森” 。不,我暗笑,是夫君。他今天回来得倒早啊。看着他那么专注地看着手中的案卷,我竟有一丝丝的妒忌。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啊。成亲已经一年了,我们却始终亲近不起来。就像娘的牡丹园四周种满了花开富贵的国色天香,而父亲却最爱在他的松涛阁内品茗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在两个世界里。
我一点都不喜欢爹和娘相处的样子。我的曾外祖父是前朝骁勇大将军,曾陪伴先皇立下赫赫战功。我的外祖父则是本朝镇远大将军,在母亲口中,外祖父英勇杀敌的模样绝对不逊于当年的曾外祖父。奇怪的是,他竟选中了一介儒生的父亲做了女婿。母亲骄矜高傲,父亲严肃古板,不难想象,这么两个人凑在一起,果真是——相敬如“冰”啊。或许,这种大户人家原本便应当这样吧,发乎情,止乎礼,不见悲,不见喜,永远没有真情的表露。唉,于是,他们的女儿居然也与他们一样——继续传承这“相敬如冰”的伟大情操。
我的夫君当然不叫“森”。
他的名字叫弘余。记得第一次从丫头口中听见这个名字时,我就乐了。红鱼?红烧的鱼吗?嘻嘻,天下间竟有这么有趣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应当也会很有趣吧!
可是,当这个新科状元站在我的面前,用他冷静的听不出感情的声音告诉我“此生弘余不为己,为国为民为苍生”时,我便知道我要失望了。我知道,他不是我盼的那一个,我恐怕也不是他盼的那一个,或许,宰相的女儿是,但——我不是!
果然,他的的确确无趣极了。所以,当他新婚之夜和衣而卧,当他在数不清的夜晚飘然无踪时,我倒也乐得轻松自在。只是偶尔在胡思乱想的老毛病发作时,也会有一点怀疑,他真的是没有感情的木头吗?爹对他的赞许有加,丫头们对他的无比崇拜,都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
哎呀呀,我这是干什么呢?堂堂宰相家的女儿,居然像个小贼,贼头贼脑的缩在角落里,偷看自己的夫君,成何体统呀!想到这儿,我连忙整整衣襟,咳嗽一声,便踏进卧房,准备梦我的周公去也。没想到,我还是吓了他一跳。只见他一惊,手中的案卷也落在地上。我微微地撇撇嘴,这个不禁吓的木头。为了表示大家闺秀贤良淑德的风范,我抢前一步,打算帮他把那案卷捡起来。但是,手长脚长的他动作更快,早已将那“案卷”抢在手中,纳入怀里。
那是……
我疑惑得抬起头,那不是案卷!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我还能分辨出一块粗布和精致的案卷之间的区别。那么,是什么布让状元大人,当朝正三品的侍郎大人这么宝贝,又那么紧张呢?
疑惑间,他已经掉过头去,轻咳一声道:“夫人今天到早。”
哈,他倒会抢话。“是啊,累了,所以想早点回来歇息。”装作不在意,我施施然走向床去。“那,下官不打扰夫人休息了。”他像如蒙大赦一般,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
“下官……” 我垂着头,握紧拳,指甲掐进了肉里。
哈,我这听竹轩何时竟也成了朝堂,那个冷冰冰,需要带着面具的朝堂!
真的好累啊,我要睡了。我心里这么想着,脚下却不能挪动一步。
不行!我突然下定了决心。
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这木头面具下的真正模样!
二
“如意小居”
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这所不起眼的宅子。
我,怎么会到了这里?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有一缕发丝垂到额前,真讨厌,我捋了捋头发,咦,我的珠钗呢?虽然平日里并不太在意这些劳什子,可少了它,我的头发可要造反的。所谓相由心生,我这三千烦恼丝又硬又直,也更容易折断。所以,每天,丫头们都要花好多功夫帮我梳妆,细细的为我涂上惜花坊最好的桂花油,再用金的银的玉的,簪啊钗啊花啊的压满我的头,压住我这一头的不驯。
至于今天……
对了,我怎么会忘了,我是跟着那个手长脚长的木头出的门啊。
我先是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大嗓门的,愣头愣脑正打算向我请安的门房一眼,吓的他把话又吞了回去,接着便无声无息地闪出了门。
真刺激!瞧着前面不远处,那个换下朝服青衫磊落,只用一根青色发带随意的绾了一个髻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羡慕地晃了晃自己沉重的脑袋。
他居然还挺好看,不是吗?虽然只是粗布麻衣,却遮不住剑眉入鬓,朗朗星眸。挺直的鼻梁写着骄傲,薄薄的嘴唇带着坚毅,那挺直不屈的脊梁更让人不敢小觑。一路上看到好些个姑娘家,眉目含春,频频望向他,我的心里有骄傲又有辛酸……骄傲,因为我是他的妻,辛酸,也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多么奇怪的感觉。
不好,他突然停住了,我一惊,他发现我了吗?敢忙回转过身,我假装忙着挑选身旁杂货郎正在热情叫卖的东西。
他在干什么?我斜斜地用余光瞟他。
他蹲下来了?还好,不是因为我。奇怪,他是肚子痛吗?怎么办?我有点着急。
不对,他在——
摘花!
天哪!木头在摘花!
我们家花园里什么花没有?且不说母亲的牡丹园,单是听竹轩旁的奇花异草便不可胜数,春日的空谷幽兰,夏夜的荷塘月色,秋日的菊花清高,冬季的梅花高洁……也不见他如何的欣赏陶醉呀!
他站起来了,手中小心翼翼的握着那朵不起眼的小野花,他用那样柔情的目光注视着,仿佛是捧着一样至珍至爱的宝贝。
这个木头,真是土死了,你喜欢花,我下次让娘把牡丹园给你啊!除非,真的是家花不如野花香?我气呼呼地想。
哎呀,他又迈开大步了,我得跟上去!
“小姐!小姐!您手里的东西一共五钱银子!”杂货郎一把揪住我的衣袖。
我不耐烦,随手便拔下了头上的珠钗抛给他,“拿去吧!”原来,珠钗便是在此刻与我分道扬镳的。
约莫又走了半个多时辰,我这辈子哪里走过这么多路呀?这个木头好像铁打的似的,健步如飞,那么能走啊!可怜我的养尊处优的玉足啊!就在我打算顾辆车打道回府的时候,他熟门熟路地走进了这座“如意小居”。
我已经呆呆地在这破屋子门口做了半个时辰的门神。
木头在里面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呢?那花儿……他要送给谁?我傻傻地看着手里劣质的梳子镜子盆子筷子。那个杂货郎现在一定很开心吧,唉,我下意识地看看铜镜里的自己,没了珠钗,几簇不听话的头发已经蠢蠢欲动,几个时辰地奔波,胭脂花粉也在汗水的晕染下化开,现在,恐怕没人会相信这是宰相家的千金了吧,顶多就是一个山妖!
铜镜里的山妖露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回去吧,站在这里自取其辱吗?
我正打算转身,吱嘎一声,从那道没有雕梁,没有画栋,毫不起眼的木门中走出了一个颀长的人影,不是木头是谁?他后面……我赶忙站住身子,瞪大眼睛,屏住呼吸。
只见他握着那人的手,应该是个年轻女子吧,那身影纤弱小巧,柔顺的头发披散着,鬓边正是那朵又脏又丑的野花!哼,这样的女子也只配这样的花儿!我酸酸地自言自语。
好了,好了,你们究竟还要握多久,望多久呀!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忽然间,我的脑海中闪过这样一句。
可是,这诗句不是成亲那天宾客们赠予我和木头的吗,怎么能用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