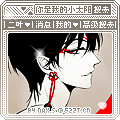梅艳芳菲雪散尽
嫁衣染血略相似
今日金凤鸾钗发结缡
却是单衣落梅人不知
我抿唇轻笑,眼波流转,口中低吟浅唱声声娇蛮。水袖翻飞作出终了的回眸,我充耳不闻台下的层层叫好,轻挥长衫,款款退下戏台。
“三弄,今儿唱得不错,就是曲不好。”沈家二少从软椅上立起身来,折扇玩转,满目笑意。
“二少过奖了。”我略拂袖遮颊,娇俏一笑,随后便是轻扭腰肢盈盈下拜。
“三弄今儿个可要谢了二少捧场。”
沈家富甲,二少风流,全苏州都知晓沈家有个面容肖似女子的倜傥少爷。我一介卑微戏子,自然要承欢奉意,寻准靠山。
良玉制的烟杆镶着莹绿翡翠,挂着的烟袋上绣有团团金丝,牡丹花卉,雍容华贵。我递上火石,二少将烟杆微微一送,姿态娴熟。
“二少,妾身听说您前些时候娶了一房美妻,改日可要请弄儿到府上一见啊。”我纤手轻摆,口吻携有嗔怒。
“莫听小柱子那厮胡搅!”他狭长的眉眼重重一挑,透露出不加掩饰的愠意,手上搁了烟袋,轻轻别过脸去。似是等我劝慰。
鸦片燃烧后的浓浓白烟弥漫在纸醉金迷的房间,狂嚣的雾霭却被薄薄的窗纸一举挡回。我侧首凝望男子线条明晰的下颏,险些窒息。
“二少可不能这般脾气大,妾身不说便是了。”漾出一抹柔媚的温情,我低声哝语着,做势推了他一把。
天微微凉,怕是要暗了罢。
二少和衣浅眠在躺椅上,雪青色的锦衣在洁白的羊绒垫漫漫铺开,宽大的衣袖懒散地落在地面。我轻摇臻首,口中幽叹一声,小心上前轻巧地在男子肩头搭上一条被褥。忽的,二少猛一翻身,一张微黄的纸笺从怀中飘落。我折腰拾起,是一副工笔丹青画像,笺上女子柳眉弯弯,笑若春山,白衣衬里的翠色衣裙隐在殷红的梅枝后一派姿容袅袅。我冷眼瞧去,明眸皓齿的面容之上,有一颗细小的泪痣开在眼角。纸笺下角题有一行工整的卫夫人小楷,莫吟梅。
我捏起那脆薄的纸笺转身坐在妆台边,略抬小臂,昏黄铜镜前的一盏烛活沉默地将画像吞没。火红的蜡油缓缓流入灯盏,宛若泪滴。我挥手一弹,满桌黯淡的灰烬。女子胭脂色的唇边勾起一丝笑意,窗外皎洁的月娘洒落一地婆娑的清辉。我轻立起身,在房内舞起水袖,抖落一室潋滟的柔光。身姿映入铜镜,镜中的窈窕女子,眼角赫然生着一枚泪痣。
梅舞先秋三弄雪,南雁纷飞尽成灰。
“弄儿?”二少微仰脸,凤眸眯起轻声唤。
我浅笑倩兮,手执一碗清茶迎上去,柔声道:“二少昨夜睡得可好?”
“这躺椅硬的难受,害我此时还腰酸。”二少扬眉,神情颇为不满,伸手便执起我颊边垂落的青丝细细玩弄。我眉眼一蹙,放下手中茶盏。
“二少,昨夜那画像,弄儿烧掉了。”
闻言男子手上重重一拽,竟是生生扯去几缕青丝。他面色苍白,惶然攀上眉梢。暗紫色的唇片颤抖着,二少厉声开口。
“黎三弄,你非要断了我的念想吗!”
我拂去他的手指,决然起身。移步来到窗前,淡漠地瞥他一眼。
“二少记得就好,妾身是入了乐籍的戏子黎三弄。”
清脆的瓷器碎裂声在身后响起,我纤细的指尖狠狠地嵌入红木制的窗棂。直至零乱纷沓的足音消失,我才松了一口气,无力地摔坐在地。
晌午,清凉的雨丝急急落下,尖角的屋檐下流挂着串串泠泠的水帘。我手执纱面扇倚在门边,凝眉望向晦暗的苍穹。
“弄儿姐。”一个旦角小婢怯怯地跑来,低声叫着。
“如何?”我粲然一笑,语调温婉。这浅吟阁的班子尊我为旦花,甚是恭敬。
“沈府的小柱子送信儿来,说是二少邀您上府。”
我略一颔首,眼波回转。
“好。”
沈氏宅邸。
月白色的繁复裙裾外一袭浅葱色萝裙,我双手合十在腰间,乌黑的发丝绾成一个精巧的流云髻。府中的小厮与婢女悄悄回首,我抿唇,凌霄一笑,莲步轻移。行至前堂,只听得妇人的尖声啐骂。
“沈府何时有过这般放浪形骸的女子!”
我垂首,眸中意味难测。
“沈夫人,贱婢三弄给您请安了。”我婷婷步入前堂,目光凛然扫过上位的宫装女子。
“黎三弄,你一个卑微的戏子还妄想入主沈家吗!”少妇满目怨怼,口吻甚是狠辣。一席话却被踏入的身影堵了回去。
“刘一婉,你若是再开口凌辱,休怪我将你休了丢回刘家!”二少的雪青锦衣行至正房婉夫人面前,眼中浓浓怒色几欲燃起。
我水袖遮去面上盈盈笑意,启齿却是哀怨至极。
“二少,夫人所言极是,请二少莫怪夫人一片衷心。”
“臭戏子你休要告状!相公,她——”
“啪。”二少凌厉的手掌扬起,我退步到堂外,不愿再看这荒唐的闹剧。抛却身后繁杂的喧嚣,我望见园中的一株红梅,袅袅挺立。那色泽犹如鲜血染红的白雪。
我举步上前折下一枝,放在指间仔细把玩,眸中尽是历经之后的倦然。
不知为何,我忽然忆起三年前初入戏班时学唱的第一支戏,叫做梅舞先秋,此刻蓦地就开了口婉转念唱。
晚风拂帷裳,梅影无灯伴
相离莫相忘,天涯两相望
月如霜,身畔相伴亦无双
铃儿轻轻荡,声声入愁肠
遥寄相思,远眺故乡,伊人何方
静夜阑,寥落微星挂天上
不思量,自难忘,浊酒一杯慰情殇
凭栏空对愁,岁月尽成憾
寒鸦秋梅携凄凉,久待思君为哪般
秋水望穿,临风轻叹
南雁不归,徒留情长
历遍巫山沧海,望尽洞庭云雨
红梅零落姻缘散,梦回几转泪轻淌
抚琴清唱梅枝舞
亦难追忆亦难忘
轻淡的唱腔空等了一生的荣华奢想,我从何时开始,已忘了自己的名讳。
撕碎了一地的红梅,我摇着纷沓的脚步匆匆离去。
二少终是休掉了婉夫人。那个本该享尽荣华美满的年轻女子成为纠缠不清的悲剧。时常,我会忆起她悬梁后幽怨的眼眸和颓败的妆容。深刻的仇恨和深刻的眷恋在某种意义上相通,去了一个婉夫人自然还有第二个。
今夜是我息戏的最后一场。这一场,我要唱梅舞先秋。
披上他钟爱的雪青色裙衫,穿上镶玉金缕鞋。我系上锁骨处的绣锦盘扣,斜睨镜中女子。苍白的面容被留晕的妆容掩盖,朱唇点点,眼眉横弯,眼角的泪痣用妆笔描绘成花,瞳中平静一片波澜不惊。终而我从檀木梳妆盒中取出一支黄杨木簪,被岁月侵蚀光滑的簪子上雕刻着流云鸾花,琢磨精致。轻挽起几缕发丝拧成一股,经手指细细缠绕绾成发髻置于鬓边。我微垂眼眸,淡淡扬起唇角。
精心搭建的高台之上,我立于大理石阶中央。舞起长袖柳眉一弯,口中吐出哀婉清脆的唱腔。
晚风拂帷裳,梅影无灯伴
相离莫相忘,天涯两相望
褪去淫靡的金石之音在寂静的夜色中显得半分突兀,我足尖旋转,余光瞥见满头青丝轻狂的在风中飘拂,面上笑意更深。歌声愈加高扬,身姿越舞越热烈。旋转太疾,却依然能望见台下那双流转的狭长凤目。二少带着温情的神情斜倚在椅上,他心以为这一舞之后我将随他远去大漠,瞧牛羊高歌看黄沙漫卷。举起兰花指,低声哼鸣,纤细的指尖滑过唇边,我露出一丝刻意的决然。
片刻之后,风静止而心不止。
女子随着疾去的风声轰然倒地,嘴角洇出的血迹一路蜿蜒到雪青色华服,娇吟戛然,眼睫疲倦地颤抖着。隐约听见玉器落地的声音。
慌乱的小厮奔上台来,我已经无力再开口。
“二少爷!二少啊!”挣扎着被半扶起,我的目光轻轻落在台下。雪青锦衣男子从椅上滑坐在地,唇边犹带血迹的他低沉的眼神紧紧锁住我。我回给一个虚弱却决绝的笑容,手指摇晃着从发间抽出发簪轻轻咬着。男子愣住,旋即微微颔首,嘴唇轻张,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点头,尔后安静地阖上双眼。
寒冷刺骨的夜风落在女子的身上,拂去纷繁的发丝露出一脸眷恋的平静,只因离去前那一声久待的的轻唤。
吟梅。
这是黎三弄一开始就决定的结局。她在每日的烟袋中撒去慢性毒药,只期盼一刻的坦诚同归。今夜上台前她在长长的指甲里藏入剧毒,待最后一字落下便翩然离去。黎三弄就是二少心心念念的莫吟梅,年少时的心猿意马与青梅同竹留下无尽的痛。那大漠是曾在梦里出现的遥远,太多的牵绊的纠缠无法割舍,黎三弄终究是选择了最刻骨方式教人遗忘。
生不能同眠死同穴。
黎三弄抑或莫吟梅,在翻山越岭后终了来到这片水域。她穿过群群银鱼,踏过纠缠的水草,直至华服浸染出颓败和绝望。遥而咫尺,欲寻不能。戏念在动情,却毁于情劫。论是谁,在冰冷的结局出场前做出挽留,月娘宽恕这死寂的悲歌。
或是有天,谁在树下唱一曲红梅,洒一地清酒,静盼远归的双雁得到比翼的半日安闲。
临别殷勤重寄情,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私语无人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