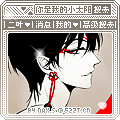面对那种绝对的高度,心里会生出恐惧,但是更多的,却是想跳下去的悸动。那种知道最坏的结果,而变得心痒难耐想加剧它毁坏的心悸。很美妙的感觉!
此刻,天空阴霾,因为正在下雨。
她没有撑伞,站在高楼上,下面几乎看不见她单薄的身影。而她眼神深远,如果不是外面的建筑太现代,真让人觉得那是一个来自深宫大院的悲凉女子。
雨滴在她身上已经不能再仔细分辨,她抹了把脸,顺手揉了下眼睛,凄迷的神色像极每一个渴望死亡的人。然而她不是那些人,她站在这里不是因为她迫切的希望连同灵魂一起重新开始,她的凄迷也不过是她惯有的表情。她只是,不能自已的想追求那份悸动。
她记得,她小时候是很害怕高处的,连被父亲举起都让她觉得恐慌。甚至,她不敢看那些高层的建筑,更害怕一抬头,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直线距离就能把她吞没。
因此,她一直低着头,看着每一个人来去匆匆的脚印,或者一个方向,或者另外一个方向。渐渐的,所有人在她眼里都成了一双脚搭着不同的鞋子,以及小半截裤腿。
然后,从有一天起,她的世界只剩下了一双穿着黑色高跟凉鞋的光裸小腿。她还记得那两条修长的小腿曾接送过她整个幼稚园和小学,也在中学等在门前欢迎她勇敢的归来。那两条腿的主人会给她烧美味的饭菜,会为她缝制美丽的袜子。她喜欢那些色彩各异的袜子,像喜欢那些不高的花朵。除了漂亮,隐隐的,她也知道,是因为自己比它们高,弯下腰就能很好的护住自己喜欢的东西。用自己护住自己喜欢的东西,像那双腿的主人曾对她做过的一样。
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她想起那把跌落在地上的雨伞。粉色的底面,圆形斑点,密密麻麻布满她的脑海,而每一个圆点中都生出一双穿着黑色高跟凉鞋的光裸小腿。
她开始不停的旋转,盯着天空飘落的雨滴,俯仰的姿势,什么也遮挡不住。簌簌而下的雨水,早已浇湿她的身体,没有了舞裙的飘逸,单纯的肢体摆动,像个傻瓜做的木偶。不过她很快乐,高高的地方,没有了阻碍,不用再卑微的以弯曲身体来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东西。
旋转中,有水滴又飞出,像她突然变晴的天空,虽然是任何人都得以肯定的阴霾,这一刻,至少,她放开了自己。在身体最后也变成水滴向四面散去的时候。
她不爱和人接触,或者说是恐惧和人接触,心理学上,被称为自闭症。她的母亲只是个没有文化的纺织女工,嫁给了厂长痴傻的儿子。那个傻爸爸,把她们都以为成了玩具。称心不如称手。她躲在妈妈怀里,暖暖的,仍然怕。
灯光下,妈妈给她逢袜子。厂里不用的零碎布片,形状不一,颜色繁多,是记忆里最丰富
色彩。她喜欢踩着那些布片做成的袜子,跳花儿在微风下跳出的快乐舞蹈。那时妈妈会看着她笑,坐在床下的她,抬头看着自己可爱女儿的舞蹈,眼神像地上的阳光一样温暖明亮。然后,暴力就来了,傻爸爸想要抓住那个叫做女儿的可爱玩具,但是妈妈惊恐他大力的手掌。她抱住床上的女儿,弯腰,贴住懵懂的女儿,说出美好的欺骗。宝宝乖,夜晚来临了,睡觉觉,睡觉觉,睡觉觉、、、、、、重复的话语,呢喃的轻吟,但是在那些背后,始终有咚咚的肌肉拍打声和脚大力蹋在地面的声音。然后,她睡着了,后面的声音消失了,脸上开始有滴滴答答的水液滑过。
到那一天,她低着头走过街道,拐出巷口,看到很多双脚在一个地方聚集。脚堆里有一双黑色高跟凉鞋的光裸小腿,不是站立,是平躺在路面上。好矮!就算蜷缩起自己也能将她覆盖住。她想着,就那样做了,抱住地上那个人,连自己一起蜷成一个圈,日子久了,就会长出壳,壳就能保护她们了。
她喜欢在雨天走出去,因为下雨,路上总是没有多少人的。她会到小区那头的花园去,那里,在雨天能看见很多的蜗牛。她们薄薄壳,从花叶上掉下来也不会碎,她一碰,她们就停下来,缩进壳里去。她想她以后也能有这样一个壳,等到她长大,就抱住妈妈,天长地久,她想和妈妈住在一个自己蜷成的壳里。
现在,她抱住那具冰凉的身体,明明,早上出门的时候,自己还在她的怀里,暖暖的。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你在这里,为什么你不说欢迎回来,为什么我明明还没有长大,却能抱住你了。周围一直好吵,像那个人来临了一样。她们要将我们分开,不!‘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妈妈,我们马上就能长出壳了、、、、、、
雨水下,旋转的脚步一个踉跄,她微抬头,想念的样子。身子一侧,就倒了下去。她想,下冲的速度是不是跟妈妈一个样。
她想起来,她知道的,她的妈妈死了。那双黑色高跟凉鞋的光裸小腿,是她的妈妈。她的妈妈被她的傻爸爸丢弃了,从高高的楼层上丢下来。而她,用蜗牛的壳压死了她的爸爸。
她想,她还是怕高,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也怕。她在空中缩起了身体,怀里空空的,只有抱住双脚,上面是一双碎布拼接的花色袜子。
后记
那一天的晚报,报道了一男子被重器砸伤丢弃在公园里,周身布满碎裂的蜗牛壳的事件。报道说因为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当场死亡。据现场遗留的粉色圆点雨伞来看,为他杀。



 近距离围观秀恩爱。
近距离围观秀恩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