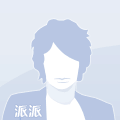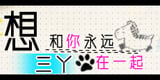| 《指间砂》一文四篇皆是典型的倒叙结构的短篇,虽然把结局提前来看不免是普遍意义上的悲剧,然而也多少有些死得其所,悲而不哀的归属感。其中尤其以碧落篇为独特,想来感情的纯度再如何被人歌颂或者诋毁都难有新意,那么只能改变书写感情的角度,恰好这一篇极是难得,即使在现在看起来,其中真意也值得反复品味。 理论上说短篇要写的好比长篇要难得多,起承转合的衔接和比重,矛盾的安排,情节的推动都需要更出色的写作功力,《指间沙》从情节上考量无功无过,并没有更多体现出调度的技巧,然而从情感的内核上说,却是相对构架出彩的,在我看来小妗的心智并不是那么的完整和成熟,且她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雏鸟情怀,封闭单调的环境造就了她毫不保留的执着和一贯的炽热情感。严重来说,小妗是无知而无畏的。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排遣寂寞的人,至于这个人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心理甚至是性别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那么一点温情便已足够。可叹,碧落正是那恰逢的最最温柔醉心的情人,便也就是这恰逢,才最是造就故事转折和结局的精彩绝妙之处。 纯如白纸的小妗和过尽千帆的碧落,如何就得以相爱呢?在我看来恰巧有点像两极理论般,人往往会被自己不具备的素质所吸引,所以碧落和小妗都惊喜那份新鲜,其实就是源自于他们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所造就的独特人格。待到热恋一过,这种互相无法理解的巨大心理落差就强烈的凸显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两人的误会。虽然情节安排在这里急转而下但是也还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待到后文,全文关于悲剧的争议之处出现了,也即是爱而死和死而爱的争端。个人看来最不幸的却不是小妗而已然是碧落,这不幸来源于天然的感情失落而非责任道义,所以也就无从谈起如何派遣解脱,继而只有不断地承受下去罢,从而出现全篇开头那醉酒的一幕,至此一节,我独独认为逝者的不幸还在其次,反而生者的备受折磨愈加脱俗了。 所以说碧落到底是成全了小妗还是辜负了小妗,已是不可辨别分明的问题,并且因为小妗的早夭,使得这份感情被时间打磨出更多真相之前就已经猝然盖棺定论。且在我看来小妗的成功正是来自于她的早夭,如果她长大,那么她有可能成为满腹幽怨的庸俗妇女或者因心智低幼无法适应世事而饱受艰辛早早磨灭了那份纯真。曾经看到有人评论冲田总司说:人们对他的赞颂怀念和无限美化正是因为他的早夭,若想永远不老,若想美好永生,就只有在最美丽灿烂的年纪决绝的死去——这是唯一悲哀的办法。而小妗也正是如此,她被死亡定格在那一瞬,被碧落的怀念催化为世间最美好的女子。 因悔恨而产生爱意,因消逝而衍生坚贞,正是不胜唏嘘! 结局虽是既定结果,但国人一向遵从的观念即是逝者为大,勿议身后。所以我对小妗和碧落的这份真相已经不想妄自揣测,作为读者不如抱着一点侥幸心理,沧月以情节服务感情所刻画出的激烈的故事和情感,语言优美寓意别出心裁,对于人情的种种揣摩和刻画也算娴熟,尤其此文以主角少年时期所经受的残忍与人格的缺失为基要相对比的情感刻画,惨烈且富于不真实感。虽则这种写作喜好得到了的尤其体现,但毕竟沧月的书一向是满足幻想而非追逐现实,所以我们往往也是于此处受创而他处得到补偿,不必一味的承受煎熬,想来也算平衡的很了。 {为了不精简而摘录文中的一小段,也是评论的出发点和重点} 其实,本来碧落未必会这样的看重那个女子——因为他从一开始,便是个游戏风尘惯了的人。如果跟他说什么坚贞、什么永恒,这个男子或许只会嗤之以鼻。 他对着每个遇到的女子承诺“永远”,然而他心里不相信有永远的爱情;那个痴情的少女也对他倾诉“永远”,但是那个才十几岁苗女未必真正明白什么是永远……永远的相爱,在这个瞬忽如浮云的世上,本来就是极其不可信的。 然而,不等时光褪去谎言镀上的金色,让他们亲眼看到那个“永远”的破灭,她却死了。 死亡在刹那间、就把她对他的爱凝固了在那一刻、嘎然而止成了永远。 那个承诺不再是一个谎言!她对他的爱便是永远的,钉在了他的心里——永远无法再否认、永远无法再抹去。 小妗,小妗……如今,苍茫海里的踯躅花已经开了一年又一年,然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山长水远,天地茫茫,[恐怕是再也相见无期了。 原来,人这一生中,唯独“离别”,才是真正永远的。 ————猫于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晚二十二点二十八分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无良增补版 |
-
— 本帖被 路小透。 从 品书评文 移动到本区(2013-03-18) —[ 此贴被燕歌既远。在2010-04-28 00:39重新编辑 ]
- 倒序阅读 只看楼主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