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朝,丙辰年正月十六,正当人们依旧沉浸在元夕的喜庆氛围之时,天空的西北角却无故出现了一道诡异的黑色裂痕。起初裂痕像细线一般,只是隐约可见并不真切,而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张,俨然已成了一个庞大的黑洞。
黑洞向四周辐射出死沉沉的邪气。西北边塞本就是一个荒凉异常的地方,受邪气影响,那些仅有的动植物大都死去枯萎,很多人也受到影响,一个接一个魂归西天。遍地都是尸体残骸。当地居民异常恐慌地搬离故居,驻边军士也向东南连退数百里,一直退守至天机城。
天地异变,人心惶惶!
帝国朝史上最具才能的帝王武辰迅速派出十**师前往西北进行调查,同时对那股邪气进行封印。即便如此,那股邪气还是源源不断地从黑洞中涌出,凶戾异常,而其波及范围之广更是骇人,绝非那十几个半身入土的老者所能应付的。
封印随时都可能被冲破,而其连带效应更是无法想象!
武辰为这事已有十数日未曾好好休息,原本魁梧的身躯日渐消瘦。他想不明白,为何在这太平盛世会惊现此等异变?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他没有良好的对策解决此事,第一次他觉得自己很无力。难道帝国数百年基业就要毁在自己手中吗?
帝都东北二十里云龙山。此山虽邻帝都,却清静异常,山林清秀幽美,草木四季长青,花卉终年不败,飞禽走兽生活自得颇具灵性。山腰而上云缭雾绕,更生有罕见的灵芝瑶草。山顶坐落着一座破旧却颇具庄严气势的道观—清虚观。据说此建筑始建于帝国初期,已有数百年历史,是历任国师居所。原本帝王见其破旧,多次想翻新重修,只是国师怕扰了这清静之地,便一直保持着原样。
国师在帝国朝的地位是极其尊贵的,虽无实权,却有能直接接触帝王的特权。有时甚至帝王也要让其三分。按祖训,每年年初帝王都要上山见国师,据说是为了通达天意,以明晓自己在治国之道上是否出现了差池。可是国师毕竟只是凡人。
此时云龙山下停驻了大队人马,皆是身批坚执锐的军士。士兵门列队整齐,气势威武。带队将军更是身着银色明铠,手持青铜长剑,左手时刻握着剑柄,神情严肃,谨慎二小心。
整支队伍都处在严密戒备、时刻准备战斗的紧张状态中。
云龙山腰,幽幽曲径,一白袍男子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山上走去。那人面目清秀,目光如炬,眉宇间自然流露出一股霸气,然而却满面忧愁。一席装束皆为上等锦缎织品,腰间配着的龙凤绿玉双环,更是世间极品。他从山脚登至山腰,却呼吸如初,而其脚步亦是沉稳有力,其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越往上云雾越浓,而景色也越发异丽。白袍男子却无暇欣赏这等美景,直往山顶而去。不出半个时辰,男子已立于清虚观前,他长袖一摆,恭敬地弯腰作揖道:“武氏第十五代子孙前来领教虚云国师法旨。”他低眉颔首,静候回音。
尔后,只听“吱呀”一声,清虚观大门缓缓打开。男子抬头,双手提着长袍下摆极其小心地走上台阶进入观内。大门后面是一处庭院,院内满是奇花异草,莺飞蝶舞,鸟啭啁啾。这番静致与这破道观,甚至是寒冬时节的人世,实有天壤之别。
男子快步穿过庭院,轻车熟路地到了正堂。正堂摆设极其简单,没有世俗道观的鼎盛香火,便是那几根朱漆红木也已斑驳陆离。此时一老者坐于蒲团之上,双目微闭,白发白须,面色慈祥,着一身墨绿道袍,眉宇间透着十足的精神。真有一番仙风道骨!
男子虽显急切,却也不敢扰了老者清修,静静地立于一侧。不多时,老者睁开双眼,看了一下男子,起身作揖道:“陛下远来,恕贫道未能接待。”
男子无心这般客套,“国师还是不要这般拘于礼节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谈正事吧。”
二人随意在蒲团上落坐,虚云看着武辰,道:“陛下这般匆匆而来,是为了西北边塞‘天裂’一事吧?”见武辰没有说话,他继续道,“不知陛下以为这是天灾呢还是人祸?”
“这正是孤王所要弄清之事,不知国师有何高见?”武辰满面愁容,看着虚云。
“陛下登基以来,治国有道,国泰民安,路无流民,民无饥者。自然不该是天灾。”
“那国师的意思是人祸喽?可是我不明白有谁有那么大的能力,能使天裂?”
“陛下可还记得两年前黑骨之匣失踪一事吗?”武辰听了这话脸色骤变,虚云继续道,“黑骨之匣是数百年前狼人一族召唤妖灵军团之物,当年圣帝统一全国后将其封印在王族禁地,以免再生祸端。而两年前此物神秘失踪,至今追查无果。陛下还记得《帝国史》对黑骨之匣召唤妖灵军团场面的描述吗?”
武辰脸色再变,许久才道:“天裂?”
“不错,正是西北边塞的异象。”虚云肯定地说道。
武辰面色苍白,半晌才稍稍恢复平静,“那么,国师可有什么良策?”
“只能肖仿当年圣帝的做法了。”虚云缓缓说道。
“那我立刻派人取出净灵珠,然后赶去天机城。”
“不,此事只可托付于至信之人。望陛下恕贫道擅作主张之罪,贫道已派人取出净灵珠,此刻应已在去往天机城的路上了。”虚云拱手请罪。
武辰微微皱眉,却不好发作,“国师所派何人?可信否?”
“若此人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人。陛下尽管放心。”
“真有这样的人吗?他是谁?”
“云从龙,风从虎。陛下以为如何呢?”
武辰听后淡淡一笑,“国师到底是国师,果真有先见之明。”
无双镇,朋来客栈。临近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雪,屋顶街道都披了一层白色冰衣,整个小镇都显得格外祥和宁静。店小二福安穿着厚厚的棉袄,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打烊,他可不想在这寒夜独自赏雪。
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撕破了夜的寂静,然后是勒马的吁声,安静片刻后,便听到了响亮的敲门声。福安本不想开门的,但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一家客栈,让人在这样的夜晚露宿,他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他很不耐烦地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一个身着锦袍的魁梧男子,他身高八尺有余,双眉粗浓,双目亮而有神,而让福安尤其留意的是,即便受到寒气侵袭,他依旧面色红润,很有精神。
他淡淡一笑,呼出一口热气:“我要一间上等客房。”
福安习惯性地笑道:“客官来得真是时候,小店正要打烊呢,您要错过了,只怕就要露宿野外了。小的现在就带你去看房。”说着,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男子进了屋,顿时觉得暖了许多,他又回头说道:“对了,麻烦小二哥替我安排一下外面的马。”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了福安。
福安接过银子,嘴里却客套地说道:“诶,客官,您瞧您,这可真不好意思了。”然后他领着男子上楼,带他看了房间。临下楼时,福安神秘兮兮地嘱咐了男子一句:“客官,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走出房间,不然……”他没往下说就下楼去安排马了。
朋来客栈对面的小巷里,一双眼睛一直盯着客栈,直到他看着福安出来牵马,才向黑暗深处退去,完全消失在了黑夜里。
帝都。
无情的烈火吞吐着毒舌,似乎要将景王府的一砖一瓦都给吞噬,火势异常庞大,黑夜被映照得如同白昼,火舌吞吐,只把空中的浮云舔得通红,浓烈的黑烟伴着火光直冲上天。原本豪华的府邸毁灭起来竟也这般壮观。
人人避火不及,身着铠甲的男子却直往大火深处冲去。他狂奔着,在地上一具具烧得焦黑的尸体间搜寻着,但他找不到要找的那个人。他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只觉得天旋地转,从未流过泪的双眼再也抵挡不住感情的冲击。他绝望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任由火苗窜到铠甲上。他双拳猛击地面,显得非常懊恼和后悔。
“咳咳……”众多尸体中传来一阵低弱的咳嗽声。男子抬头,像寻找救命稻草一般四处找寻。终于,他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然后他跌跌撞撞地奔过去,像中了邪一般,视线始终没有偏移过。
十多米的距离却似慢慢长途,来到那个角落,男子看着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单膝跪了下来。他扶起幸存者,将他的头枕在自己的手臂上,挤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没事了,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带你出去……”他说着哽咽了。
幸存者穿着与男子一样的铠甲,他满身是伤,一支利箭自左胸口贯穿而过,血还在不断地流出。他咳出一口血,艰难地说道:“甄…士忠,他…他是…景王的人,我…我们都…中计了……”男子握着他的手,泪无声地流落。“替我…报……”幸存者突然瞪大了双眼,手无力地从男子手中滑落。男子满脸的悲痛,将他紧紧搂在怀中,完全忘却了身边的危险。一根带着火的柱子在他背后直直地倒了下来……
“啊!”一声惊叫,男子猛地从床上坐起。他大口喘着粗气,面色苍白,浑身冰冷,额头不住地沁出冷汗,后背也湿了好大一块。这个梦自武辰登位之时就困扰他至今。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接受这次的任务,所谓的拯救苍生的大义对他来说根本一文不值。他也不相信会有英雄,更不觉得自己会是英雄。他摸摸后脖颈的左下侧,那里是一道长而丑陋的疤,那就是想当英雄的代价。
下床,给自己倒了杯早已冰冷的茶,一饮而尽,一股冰凉的感觉由咽喉直贯而下,脑袋顿时清醒了许多。
“苍天裂,群魔出;帝国覆,众生灭。”这时窗外隐约传来一阵低沉的吟唱,声音沙哑而冗长,由远及近,渐渐清晰。男子微微皱眉,这可是大逆不道之言,谁敢大胆如斯?他迅速闪身至窗边,将窗轻轻地推开一条缝。一股寒气迎面袭来,外面北风正紧,细雪纷乱地凌舞。
男子毫不顾虑从衣领灌入的寒气,仔细观察外边的动静。下一秒,他瞪大了双眼,显得异常惊愕。大街上没有半个人影,可他透过黑暗却看到雪地上被踩出了一排整齐的脚印,而这脚印似乎比人的大出好几倍。更诡异的是,脚印还在向前延伸!吟唱声渐渐远去,在雪地上留下一阵低弱悠长的回声。
男子半晌回过神,刚要追出去一探究竟,却感到门外有个人影在窥探。于是一个健步掠至门口,等了一会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房门。然而,门口半个人影也没有,过道上静悄悄的,只有朱漆已落的木椽在幽幽的黑暗中嘲笑着他的过分敏感。
男子苦笑,许真是自己太多虑了。他关了门,退回屋内。
房梁上,一条黑影轻轻跃至地面,便迅速离开了。方才若非他完全屏住气息,定被发现,而交起手来,亦是败多胜少。
清晨,下了一个晚上的雪终于停歇了,几缕阳光穿透云层给人世传递着温暖,几只卧巢已久的麻雀也难得地露了面。
锦袍男子下楼准备吃早饭,在楼梯上听到店主的训斥:“什么?盐又被偷了?我养你干嘛的?你干什么吃的,保管盐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啊?”福安唯唯诺诺地应承着。
楼下客人不多,很多桌子上摆着的凳子还没拿下来。锦袍男子拣了张桌子,正要翻凳,旁边一男子喊道:“兄台何必费力?小弟一人独酌未能尽兴,不如过来一同畅饮。”
锦袍男子看过去,那人面带微笑,也不看他,自顾自地喝着酒,身上透露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不知为何,锦袍男子竟想过去和他打打交道。“如此甚好,作伴相饮,醉了亦有照顾。”他走过去,坐下,要了一壶热酒,还有几个菜。
“知己者相饮,不醉不休,非知己者,小饮即可。”男子笑道。
不一会儿,福安将酒和菜送上了桌子,一脸的沮丧,几个难看的笑容也是强挤出来的。“你们店里经常丢盐吗?刚才你们老板骂得很凶啊。”锦袍男子随意问道。
“唉,别提了,现在小偷不偷钱,就偷盐。”说着,他摇着头去忙自己的事去了。
“兄台很在意这件事吗?”那男子问道。锦袍男子摇了摇头,其实他真正在意的是昨晚夜里看到的那一幕。
“兄台,你我于此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小弟姓杨单名一个逸字。”他故意停下,等着锦袍男子自我介绍。
“萧龙。”锦袍男子简单地吐出两个字,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兄台真是比这天气还冷啊。”杨逸自嘲般地笑道,“诶,对了,兄台昨晚可曾听到一些奇怪的动静?”
萧龙怔了一下,他偷偷打量着杨逸。萧龙不了解他,也许他是来套自己话的,而他又有重任在身,不得不提防着。“没什么奇怪的,我睡得很香。怎么这么问?难道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吗?”
杨逸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两人静静地喝着酒,很快一壶酒便没了,萧龙结了账正要离开。便在这时,十几个人向着店门口集中过来。他们双目无神,步伐机械而呆板。萧龙皱了皱眉,看来要离开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天机城西南三十里,这里原本是一座香火颇盛的庙宇,后来渐渐没落破败,如今成了人们安置棺椁尸骸的阴森之地。破庙内杂草丛生,石阶上青苔遍布,角落里尽是蛛丝,歪倒在一旁的佛像上满是灰尘,洞开的窗户向屋内灌注着冷风,引得房梁上悬吊着的白凌猎猎飘动。破败的大堂内七七八八地摆着许多棺木,表面木漆脱落,积满了厚厚的尘土,显得斑驳而丑陋。但是其中有两具紫红色的檀木棺材不但一尘不染,反而光鲜锃亮,闪动着幽幽的诡异光芒,在这阴暗的环境下给人一种不寒而栗之感,棺盖两头各贴了一张血红色符咒,上面看似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奇怪的图案。
尚未透亮的天空,几颗星辰幽幽地闪烁着黯淡的光芒,黑夜盖不住的大地渐渐散发活力,东方欲晓,黑夜将逝。
风声呼呼,一条黑影在空中一闪而过,稳稳地落在了破庙外的草地上,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响动。没有任何犹豫地,黑影径直走进了破庙,而此时在光所不及的黑暗角落里,不知从何处冒出了四个人影,见黑影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淡淡地笑笑,声音极尽儒雅地说道:“怎么去了这么久?难道遇到麻烦了吗?”
黑影看向对方,平静地反问道:“帝都王宫我都能来去自如,区区一个将军府又如何能难住我?”出人意料地,竟然是一个柔媚的女声。黑暗里的男人似乎并不因她的狂妄冒犯而恼怒,依然只是淡淡地笑,似乎在等着女人的下文。“接着,这就是天机城布防图。”说着,女人左手一扬,将手中的一个竹筒抛向了对方。
男人稳稳地接住,很随意地收进了怀中。“朱雀,单单一个布防图用不了你这么多时间吧,说说看,你带回了什么惊喜?”
“青龙,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派了眼线跟踪我?”朱雀娇媚地调笑道。被称为青龙的男人毫不介意,在他们几个人之间从来都不存在怀疑。收敛了笑容,朱雀一本正经地说道:“的确有一份意外收获,某种程度上或许比布防图更有用。”边说边走近青龙,朱雀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后者充满好奇地接过,拆开看了一下,渐渐地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笑容,这的确是一份价值不菲的收获。“**,飞鸽传书给王爷,让他派五千兵马过来。另外,召集那些狼人,皮糙肉厚的他们可是难得的攻城利器。”青龙还是那般人畜无害地笑着,冷静地对身后的一人下着命令。
这时,一只白鸽扑扇着翅膀停在了窗沿,朱雀轻轻招手,却见白鸽听话地飞过来落在了她手上。取下密函看了看,朱雀微蹙细眉道:“是白煞的密函,他说有一个气度不凡的男子进入了无双镇,从其步履来看是个身手不凡的高手,很可能是冲着天机城来的。”
“哦?这么说是帝国派来的人了。单熗匹马吗?武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种时候就派了一个人过来,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我看未必,也许是他无人可派。”青龙身后又响起一个声音,“自十年前的景王之乱后,武辰对身边的人都不是完全信任的,面临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向谨慎的他是不会草率行事的。那个人如果真是武辰派来的,那么我想就只有他了。”黑暗中看不清说话人的面容,只有闪烁着精芒的眼睛里透露出的森寒戾气。
“玄武,看你如此兴奋,此人该是你的故交了,那你代我们去好生招待他一番吧。”青龙头也不回,感到玄武身上散发的一股暴虐气息。
玄武嘴角闪过一个嗜血的冷笑,然后也不见他如何动作,便悄无声息地隐去了身影。破庙外的林间,只有黎明前的冷风“嗖嗖”刮过。
“砰!”一个人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狠狠地砸在雪地上滑出数米远。杨逸看着萧龙毫不留情地三拳两脚将一群人打趴在地,不禁暗暗咋舌。这个一席白衣的男子还真如其外表一般冷酷,对这些百姓出手竟也如此毒辣。
萧龙看也不看昏倒在地的众人,径直走向自己的马。此时,几道凌厉的破空声从背后呼啸而来,下意识地侧身俯首,脚步轻挪闪至一边。却听一声痛苦的马嘶响彻天际,只见马肚上正汩汩地留淌着鲜血,彪悍的骏马被一股霸道的力量打翻在地。
攻击接踵而来,萧龙不断挪移改变位置,一边暗暗观察对手。白雪覆盖的街道上,三个彪形大汉两前一后地对萧龙形成夹攻之势,而且他们所立方位正好弥补了同伴看不到的死角,无论萧龙躲到哪里,攻击都如附骨之蛆随之而来。
萧龙暗骂一声,如此受制于人,根本发挥不了自己近身狙杀的能力,如果手里有一柄剑就好了。骂归骂,萧龙还是冷静地思忖着对策,很明显这三人都是高手,如果从正面突破,一方面要对付两个人,同时还要提防背后的袭击,而如果从背后寻找出路,虽然被偷袭成功的可能性大了很多,但如果一口气攻过去,脱出的可能也极大。
权衡再三,萧龙一边躲闪,一边不动声色地向背后的敌人逼近,渐渐靠近,似乎没被看出意图,看准时机后,猛地提拳击向对方面门。本以为这一击必中,不料对方后仰迅速出掌,生生地接了这一拳,牢牢地抓住了萧龙的拳头,同时另一只手握拳反击,拳风凌厉,带起一阵气旋。萧龙手腕一扭,将拳头抽出,迅速后退,脚轻点地面,腾空而起,双脚在对方胸口连蹬数下,借着反震的力量,拉开了与对手的距离。刚一落地,背后又传来了呼呼的风声,萧龙回身硬接了其他两人的攻击,在这瞬间的工夫,另一人也欺身而近。萧龙在三人的连番攻击下却显得轻松自若,只是面对着三个狼人,这么僵持下去自己绝对没好果子吃。
就在刚才一个照面的时候,萧龙明显看到对方眼中闪烁的如鬼火一般的绿光,双脚踢在他的身上只是让他稍稍颤抖了一下,联想到如此巨大的身躯却有这般迅捷的速度,这只能是狼人了。
有一柄剑就好了。萧龙苦笑地想到。就在这时,似乎是回应了他的想法,“咻”的一声,一道寒芒在空中一晃而过,萧龙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下意识地顺手一抄,一柄闪耀着青芒的长剑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他手里。
三个狼人眼看萧龙有了武器,更是凶猛地攻来。萧龙冷冷地一笑,手腕轻抖,身体原地一旋,长剑在空中划出一个森寒的圆,如霜剑气竟似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狼人身形明显一滞,下一刻,血光飞溅,六条手臂齐齐飞向空中,凄厉的惨叫声中,肩关节处如泉水一般喷着鲜血的狼人缓缓地软倒在了地上,萧龙的白袍上竟没染上一滴血!
收起剑,萧龙轻轻抚着剑身,看着手里十年未见的老友,显然很激动,他看也不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狼人,缓缓举剑,指向了一直在一旁观战的杨逸,眼中透露着无尽的寒意。
如果说一开始的萧龙只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看似凶猛实则并无多大危害,那么现在这头猛虎单凭一双利爪便能撕碎一切。这就是杨逸此刻的感受。虽然他也见过世面,遇到过很多高手,还不至于惊讶得两腿发软冷汗直冒,但萧龙刚才的那一剑给他的震撼确实太大了。
三个狼人实力绝非一般,而且传说狼人体表坚硬,普通刀剑斩之不可伤其分毫,甚至会自折。可是,他们在拿到长剑的萧龙面前连一个照面都没走过,就被轻而易举地卸去了双臂。太强了!那一瞬间萧龙的气势一下子就凛冽了起来,似乎只凭气势就那压倒一切。而那一剑,杨逸甚至都没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
“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萧龙长剑直指杨逸,冷冷地问道。
“剑乃至凶之器,何况萧兄剑气如此强绝,小弟可抵挡不住,还是收起为好。”强压下心中的惊讶,杨逸佯装镇定地说道,却是顾左右而言他。
萧龙手腕轻轻一抖,长剑映射着阳光闪烁着淡淡的青芒,寒意胜雪直慑人心。“如果你不想和他们一样的话,就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其实他对杨逸并无多大敌意,只是他却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拿出了这柄剑,那就有些问题了。
杨逸收拢了笑容,身形一闪靠近萧龙,低声道:“无双镇耳目众多,不是说话的地方,萧兄只需记住,我不是你的敌人。”
“那也不一定是朋友吧,你刚才的身法可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
杨逸无奈地苦笑,他可不想什么都没做就误死在这个不该成为敌人的朋友剑下,虽然他的剑快得可以让人感觉不到痛苦。“那好吧,萧兄如果真想知道那就跟我来。”语毕,杨逸脚下用劲飙射而出,一下子跃至屋顶向远处窜去,萧龙也不犹豫,飞身而上紧跟了上去。
客栈一下子又恢复了平静,一早就躲起来的老板这才战战兢兢地走到门口,看向两人远去的方向早已没了身影,有些后怕又有些期待。(未完)
[ 此贴被浮沉。在2011-06-08 18:35重新编辑 ]

 【提醒中】天.裂
【提醒中】天.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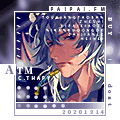














 多谢分享这本小说
多谢分享这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