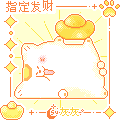“清明时节雨纷纷”作者存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写清明的诗以上面这首杜牧的七绝最为读者所熟知。它曾被选进《千家诗》,而这部诗选是旧时代四大启蒙课本“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千(《千家诗》)”之一,读过的人极多,即使是文盲和幼儿,因为常常听人念诵,也会知道,甚至可以随口背出,尤其是那前两句。
不过这首《清明》很可能不是晚唐大诗人杜牧的作品。杜牧的诗文集《樊川集》二十卷(前四卷是诗,后面是文)是杜牧病重时安排他外甥裴延翰编成的,流传至今,其中并没有这首诗;后来宋朝人搜罗杜牧的集外散佚之作,成《樊川别集》、《樊川外集》各一卷,也没有这首《清明》;直到南宋刘克庄、谢枋得先后编选《千家诗》,才出现这首署名杜牧的《清明》,而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杜牧名下仍然不收此诗。所以不少专家认为这首七绝并非杜牧所作,而是唐朝的许浑或别的什么诗人的作品(详见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32~1433页)。
但是也很难断言《樊川集》以及《别集》《外集》就将杜牧的作品搜罗净尽了,《全唐诗》也不是百分百地可以信赖,所以现在也还不能将这首《清明》彻底排除于杜牧的诗歌之外,从文学生活史的意义上来说就尤其是如此。
这确实是一首好诗。首句中“雨纷纷”三个字直截了当地写出了清明时节的主要特点,这时各地雨水皆多,诗人开门见山一举点出,深得人心,遂成名句。以下三句顺流而下,由行人之愁苦,进而写到途中有酒店,可以稍息,可见行路虽难,而仍然充满希望和慰藉,即使到达那里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也罢。全诗一气贯注,明白如话,很容易记住。只要是好诗,大家就喜欢,是什么人写的,普通读者不大在乎,他们总是相当洒脱,也可以说是持一种纯文学的态度。
牧童的形象因其热情指路而深得人心。牧童干这份轻松好玩的活儿,雨具总是常备的,他怕什么“雨纷纷”!
后来“杏花村”就成了名酒和酒店的一大品牌,至今仍是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以至成了争夺的热点,由此最可见此诗的魅力。
所谓文学生活史,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Lan-son,1857~1934)的意见,重点要研究作品的接受。既然作品是为读者而存在的,那么就要着重研究这样的问题:“读书的是怎样的人?他们读些什么?这是两个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把文学移置于生活之中。”(《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他主张“描写全国文学生活的图景,不仅包括执笔写作的知名之士,也包括阅读作品的无名群众的文明与活动的历史。”(同上第76页)既然工作的重点在此,那么将《清明》一诗继续暂挂在杜牧名下,亦未尝不可。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写清明的诗以上面这首杜牧的七绝最为读者所熟知。它曾被选进《千家诗》,而这部诗选是旧时代四大启蒙课本“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千(《千家诗》)”之一,读过的人极多,即使是文盲和幼儿,因为常常听人念诵,也会知道,甚至可以随口背出,尤其是那前两句。
不过这首《清明》很可能不是晚唐大诗人杜牧的作品。杜牧的诗文集《樊川集》二十卷(前四卷是诗,后面是文)是杜牧病重时安排他外甥裴延翰编成的,流传至今,其中并没有这首诗;后来宋朝人搜罗杜牧的集外散佚之作,成《樊川别集》、《樊川外集》各一卷,也没有这首《清明》;直到南宋刘克庄、谢枋得先后编选《千家诗》,才出现这首署名杜牧的《清明》,而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杜牧名下仍然不收此诗。所以不少专家认为这首七绝并非杜牧所作,而是唐朝的许浑或别的什么诗人的作品(详见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32~1433页)。
但是也很难断言《樊川集》以及《别集》《外集》就将杜牧的作品搜罗净尽了,《全唐诗》也不是百分百地可以信赖,所以现在也还不能将这首《清明》彻底排除于杜牧的诗歌之外,从文学生活史的意义上来说就尤其是如此。
这确实是一首好诗。首句中“雨纷纷”三个字直截了当地写出了清明时节的主要特点,这时各地雨水皆多,诗人开门见山一举点出,深得人心,遂成名句。以下三句顺流而下,由行人之愁苦,进而写到途中有酒店,可以稍息,可见行路虽难,而仍然充满希望和慰藉,即使到达那里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也罢。全诗一气贯注,明白如话,很容易记住。只要是好诗,大家就喜欢,是什么人写的,普通读者不大在乎,他们总是相当洒脱,也可以说是持一种纯文学的态度。
牧童的形象因其热情指路而深得人心。牧童干这份轻松好玩的活儿,雨具总是常备的,他怕什么“雨纷纷”!
后来“杏花村”就成了名酒和酒店的一大品牌,至今仍是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以至成了争夺的热点,由此最可见此诗的魅力。
所谓文学生活史,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Lan-son,1857~1934)的意见,重点要研究作品的接受。既然作品是为读者而存在的,那么就要着重研究这样的问题:“读书的是怎样的人?他们读些什么?这是两个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把文学移置于生活之中。”(《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他主张“描写全国文学生活的图景,不仅包括执笔写作的知名之士,也包括阅读作品的无名群众的文明与活动的历史。”(同上第76页)既然工作的重点在此,那么将《清明》一诗继续暂挂在杜牧名下,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