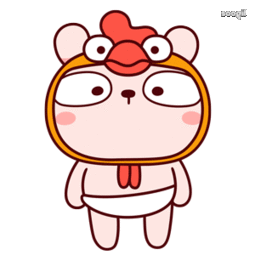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起因:日本觊觎朝鲜已久
这场仗是指爆发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是这场战争中清方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具体看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之前,先要知道这场战争是怎样打起来的。
在诱因上,甲午战争和10年前的中法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战争的蓄意挑起方利用了清朝与有关国家(分别为朝鲜和越南)的“宗藩关系”问题。就甲午战争来说,是日本利用了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此事也历经了多年的过程。
早在前边述及的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来华议约、换约的时候,它就别有用心地向清政府探询它对中朝关系所持态度。对日方的目的以及隐伏的祸患,当时李鸿章即有比较敏锐的觉察,他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体之患,倭侵高丽则为辽京根本之忧”{1}。的确,日本觊觎朝鲜决不是单单限于朝鲜,更在于将它作为跳板入侵中国。在实施步骤上则是环环紧扣,步步进逼。1875年秋,日本军舰擅自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进行挑衅,最后竟攻毁朝鲜防军炮台,并登陆滋扰,此即所谓“江华岛事件”。鉴于传统上中朝“宗藩关系”存在的事实,事后日方派员来与清朝交涉,旨在否定前不久订立的《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杜绝清方对它染指朝鲜的干涉,甚至要中国“保全”它与朝鲜“交好”。总理衙门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李鸿章当时亦对此事密切关注,并且日本使者森有礼专门拜访了李鸿章,想说动他从而影响总理衙门。其间的谈话颇有可供揣摩的意蕴。
森有礼算不上是日本最高决策层的人物,只是一个“外务少辅”,但他那一副无赖嘴脸和一番歪理谬词,却可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日方的意态。而李鸿章的“义正词严”之中也掩不住不惜以妥协求息事宁人的倾向。早在这个时候,似乎已为十来年后大战中双方的基本情状提供了预示性的信号——
李鸿章当然也以前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为抵挡森有礼否认中朝“宗藩关系”的“法器”。但森有礼不买账,竟说:“依我看和约没甚用处。”李鸿章一听着急了,赶忙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森有礼不遮不拦,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以旧条约。”李鸿章直言反驳:“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并不服,说是“《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不能不有些愤然了,他道:“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又指着桌上的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这酒不教泛溢。”森有礼回答:“这个‘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李鸿章以“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责之,话题又直接落到《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上。森有礼说,代表日方签约的伊达宗城已经在野,“自来和约立约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鸿章反驳:“约书奉有谕旨,盖用国宝,两国臣民子子孙孙当世守之。”森有礼又说需要变通,李鸿章答以“未及十年换约之期不能议及变通”。接着又辩论起朝鲜是否中国“属国”,森有礼说不算,李鸿章坚持说算,是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外藩”。森有礼又说到朝鲜不肯与日本“和好”。李鸿章说,不是不肯与日本和好,“是他自知国小,所以谨守不敢应酬。其与各国皆然,不独日本”。
当时日本署理驻华公使郑永宁也在场,他帮腔说起“江华岛事件”中朝方开炮击伤日本舰船的事。李鸿章说,日方舰船本不该到朝鲜海域去,人家开炮事出有因。郑永宁说这次森有礼来到中国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中方不能保全日本与朝鲜要好的意思;二是总理衙门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国臣民知道中国的态度,定要与朝鲜打仗。李鸿章说,若真是要和好的话,总理衙门不会不明白,“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人能让过,天不让过。若天不怕地不怕,终不为天地所容”。可日方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说要与朝鲜议定三件事:一是让它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二是若有日本遭风船只到朝鲜它得代为照料;三是日本商船到朝鲜海域测量海礁它不能计较。并说若朝鲜不予议定,日本“必不能无事,定要动兵了”!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威胁。李鸿章则以“我们一洲自生疑心,岂不被欧罗巴笑话”劝解。森有礼说:“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郑永宁则说:“总要求总理衙门与李中堂设法令高丽(朝鲜)接待日本使臣。”李鸿章说朝鲜因“江华岛事件”正在气头上,旁人说也无益,劝日本暂且缓议此事。说着说着,森有礼突然冒出了一句“试思日本就得了高丽有何益处,原是怄气不过”的感叹话,李鸿章赶紧因势利导地附和,并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在末尾还特别添写“忠告”二字送给日方。日方还是要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劝说”朝鲜与日本建立关系,李鸿章答复:“总署回复你的节略明是无可设法,但你既托我转说,我必将这话达到。”{1}
李鸿章与日方人员的这次晤谈,地点是在保定直隶总督衙署,时间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历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就要过传统年节的时候,李鸿章还在为“国事”忙碌,起码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礼的“无礼”、郑永宁的“不宁”,难免让李鸿章着急上火,但森有礼那句“有何益处”的感叹,似乎让李鸿章突然看到了“转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后对日方的承诺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马就做的事情,赶紧与总理衙门沟通消息,建议将日方的意思通过礼部转行朝鲜,说是这样“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借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②。
作用还真是“立竿见影”。面对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软处“劝说”,朝鲜在2月末即被迫与日本签定了《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所谓“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过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而它却强行染指朝鲜的掩饰而已,日本为侵朝而首先从“法理”上铺路扫障的一步做成了。接下来,自然便是变本加厉,步步进逼。
李鸿章他们如何应对呢?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列强也议定条约,以求形成对日本的牵制,制约日本对朝鲜动武。接下来的几年中,先是由美国,后有英、德等国接踵与朝鲜缔约。在李鸿章辈,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实际后果上,是朝鲜更遭受多头控制,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诱因上,甲午战争和10年前的中法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战争的蓄意挑起方利用了清朝与有关国家(分别为朝鲜和越南)的“宗藩关系”问题。就甲午战争来说,是日本利用了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此事也历经了多年的过程。
早在前边述及的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来华议约、换约的时候,它就别有用心地向清政府探询它对中朝关系所持态度。对日方的目的以及隐伏的祸患,当时李鸿章即有比较敏锐的觉察,他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体之患,倭侵高丽则为辽京根本之忧”{1}。的确,日本觊觎朝鲜决不是单单限于朝鲜,更在于将它作为跳板入侵中国。在实施步骤上则是环环紧扣,步步进逼。1875年秋,日本军舰擅自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进行挑衅,最后竟攻毁朝鲜防军炮台,并登陆滋扰,此即所谓“江华岛事件”。鉴于传统上中朝“宗藩关系”存在的事实,事后日方派员来与清朝交涉,旨在否定前不久订立的《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杜绝清方对它染指朝鲜的干涉,甚至要中国“保全”它与朝鲜“交好”。总理衙门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李鸿章当时亦对此事密切关注,并且日本使者森有礼专门拜访了李鸿章,想说动他从而影响总理衙门。其间的谈话颇有可供揣摩的意蕴。
森有礼算不上是日本最高决策层的人物,只是一个“外务少辅”,但他那一副无赖嘴脸和一番歪理谬词,却可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日方的意态。而李鸿章的“义正词严”之中也掩不住不惜以妥协求息事宁人的倾向。早在这个时候,似乎已为十来年后大战中双方的基本情状提供了预示性的信号——
李鸿章当然也以前订《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为抵挡森有礼否认中朝“宗藩关系”的“法器”。但森有礼不买账,竟说:“依我看和约没甚用处。”李鸿章一听着急了,赶忙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森有礼不遮不拦,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以旧条约。”李鸿章直言反驳:“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并不服,说是“《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不能不有些愤然了,他道:“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又指着桌上的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这酒不教泛溢。”森有礼回答:“这个‘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李鸿章以“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责之,话题又直接落到《中日修好条规》中关于中朝关系的规定上。森有礼说,代表日方签约的伊达宗城已经在野,“自来和约立约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鸿章反驳:“约书奉有谕旨,盖用国宝,两国臣民子子孙孙当世守之。”森有礼又说需要变通,李鸿章答以“未及十年换约之期不能议及变通”。接着又辩论起朝鲜是否中国“属国”,森有礼说不算,李鸿章坚持说算,是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外藩”。森有礼又说到朝鲜不肯与日本“和好”。李鸿章说,不是不肯与日本和好,“是他自知国小,所以谨守不敢应酬。其与各国皆然,不独日本”。
当时日本署理驻华公使郑永宁也在场,他帮腔说起“江华岛事件”中朝方开炮击伤日本舰船的事。李鸿章说,日方舰船本不该到朝鲜海域去,人家开炮事出有因。郑永宁说这次森有礼来到中国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中方不能保全日本与朝鲜要好的意思;二是总理衙门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国臣民知道中国的态度,定要与朝鲜打仗。李鸿章说,若真是要和好的话,总理衙门不会不明白,“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人能让过,天不让过。若天不怕地不怕,终不为天地所容”。可日方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说要与朝鲜议定三件事:一是让它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二是若有日本遭风船只到朝鲜它得代为照料;三是日本商船到朝鲜海域测量海礁它不能计较。并说若朝鲜不予议定,日本“必不能无事,定要动兵了”!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威胁。李鸿章则以“我们一洲自生疑心,岂不被欧罗巴笑话”劝解。森有礼说:“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郑永宁则说:“总要求总理衙门与李中堂设法令高丽(朝鲜)接待日本使臣。”李鸿章说朝鲜因“江华岛事件”正在气头上,旁人说也无益,劝日本暂且缓议此事。说着说着,森有礼突然冒出了一句“试思日本就得了高丽有何益处,原是怄气不过”的感叹话,李鸿章赶紧因势利导地附和,并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在末尾还特别添写“忠告”二字送给日方。日方还是要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劝说”朝鲜与日本建立关系,李鸿章答复:“总署回复你的节略明是无可设法,但你既托我转说,我必将这话达到。”{1}
李鸿章与日方人员的这次晤谈,地点是在保定直隶总督衙署,时间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历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就要过传统年节的时候,李鸿章还在为“国事”忙碌,起码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礼的“无礼”、郑永宁的“不宁”,难免让李鸿章着急上火,但森有礼那句“有何益处”的感叹,似乎让李鸿章突然看到了“转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后对日方的承诺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马就做的事情,赶紧与总理衙门沟通消息,建议将日方的意思通过礼部转行朝鲜,说是这样“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借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②。
作用还真是“立竿见影”。面对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软处“劝说”,朝鲜在2月末即被迫与日本签定了《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所谓“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过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而它却强行染指朝鲜的掩饰而已,日本为侵朝而首先从“法理”上铺路扫障的一步做成了。接下来,自然便是变本加厉,步步进逼。
李鸿章他们如何应对呢?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列强也议定条约,以求形成对日本的牵制,制约日本对朝鲜动武。接下来的几年中,先是由美国,后有英、德等国接踵与朝鲜缔约。在李鸿章辈,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实际后果上,是朝鲜更遭受多头控制,局势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