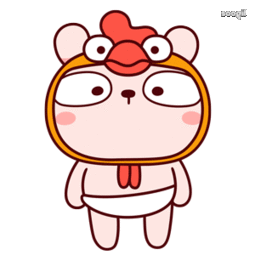沈祖棻的轶事趣闻有哪些?生平事迹又是怎样的
在风云变幻的上个世纪曾有一个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奇女子辈出的“黄金时代”,一批传奇女子似一颗颗明星闪耀于文学的星空,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吕碧城……而在这批传奇女子中有一位女先生如兰芬芳,曾得汪东、吴梅、黄侃等一众大师瞩目,她便是沈祖棻。
提到沈先生,知道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正如朱光潜先生曾赞她“易安而后见斯人”。而她跟李清照确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曾在战乱中饱尝颠沛流离;都出生于诗书世家;都有着与丈夫有志趣相投、尽情酬唱的佳话;也都有非凡的诗词才华。沈先生也被学者们推崇为上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吴宓曾盛赞:“棻品性纯淑端和,宓所见女士中第一”。
王国维先生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从烈火中获得新生的过程中,先生这位以才智气识证明自身价值的女子,却也在炼狱中历尽了苦难。
1932年,那时的先生只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却以一阕《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一篇《辩才禅师》已与老舍的名篇《月牙儿》《断魂熗》等同列,她可能便是那时“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生机勃勃的登上文坛”的一个。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出当代大师之门,为世间才子之妇”,一时传为佳话。 新婚不到一月,日寇逼近,沈先生不得不与程千帆先生暂时分别,走上了逃难之路,从此这乱离播迁的生活,使她更与南渡逃亡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认同。 《涉江词》在鼙鼓声中揭开扉页,三稿历历记录了流离之苦、重逢之喜、重庆避难、雅安养疴、乐山山居、成都执教……无常的生命历程,其间无数的苦痛悲欢,先生用自己的词一点点的记下。
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先生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历经磨难: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
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沈先生在诗中感叹“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先生却于1977年不幸逝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 沈祖棻1944年给汪东的信中曾说:抗战中躲避日机轰炸期间,自己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词稿。“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 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而一句“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却也令人动人。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 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先生在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那时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 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只是那种“美好有致”的日子,在先生的一生里很奢侈,年轻时的李清照倒是有福气消受过。当然,命运也没有自始至终垂青李清照,靖康之难令她家破人亡,也让她的后期作品增添了沉郁、凝重、深厚。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却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 再回顾沈先生的一生,正为那一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作下了注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生坎坷,先生依旧如芙蓉高洁,似兰草芬芳,“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千年前的诗人,似乎早已预言。 “有斜阳处有春愁”,千载犹是;而斗转星移,自艰难中磨砺而出的词人也在文学的星空里光辉不灭……
提到沈先生,知道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正如朱光潜先生曾赞她“易安而后见斯人”。而她跟李清照确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曾在战乱中饱尝颠沛流离;都出生于诗书世家;都有着与丈夫有志趣相投、尽情酬唱的佳话;也都有非凡的诗词才华。沈先生也被学者们推崇为上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吴宓曾盛赞:“棻品性纯淑端和,宓所见女士中第一”。
王国维先生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从烈火中获得新生的过程中,先生这位以才智气识证明自身价值的女子,却也在炼狱中历尽了苦难。
1932年,那时的先生只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却以一阕《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一篇《辩才禅师》已与老舍的名篇《月牙儿》《断魂熗》等同列,她可能便是那时“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生机勃勃的登上文坛”的一个。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出当代大师之门,为世间才子之妇”,一时传为佳话。 新婚不到一月,日寇逼近,沈先生不得不与程千帆先生暂时分别,走上了逃难之路,从此这乱离播迁的生活,使她更与南渡逃亡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认同。 《涉江词》在鼙鼓声中揭开扉页,三稿历历记录了流离之苦、重逢之喜、重庆避难、雅安养疴、乐山山居、成都执教……无常的生命历程,其间无数的苦痛悲欢,先生用自己的词一点点的记下。
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先生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历经磨难: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
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沈先生在诗中感叹“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先生却于1977年不幸逝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 沈祖棻1944年给汪东的信中曾说:抗战中躲避日机轰炸期间,自己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词稿。“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 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而一句“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却也令人动人。
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 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先生在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那时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 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只是那种“美好有致”的日子,在先生的一生里很奢侈,年轻时的李清照倒是有福气消受过。当然,命运也没有自始至终垂青李清照,靖康之难令她家破人亡,也让她的后期作品增添了沉郁、凝重、深厚。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却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 再回顾沈先生的一生,正为那一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作下了注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生坎坷,先生依旧如芙蓉高洁,似兰草芬芳,“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千年前的诗人,似乎早已预言。 “有斜阳处有春愁”,千载犹是;而斗转星移,自艰难中磨砺而出的词人也在文学的星空里光辉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