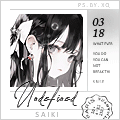我的成长乐谱中,三奶奶是一个很轻微,但是很动人的和音。她是温柔而慈爱的,身上有美丽的女人味,眼睛非常宽容,身体很瘦。她是爷爷的亲姐妹,我从没见过我爷爷,但能从她的面孔中想象到我的爷爷一定是一个很温柔,很有趣的帅老头。
她特别瘦,因此皱纹很深。但这些皱纹也让她看起来很美。我很难形容这种美,这是一种旧式的女人味。我印象里,她瘦削的身体上套着羊绒衫,腿很长,裤子很修身,能看出年轻时的匀称。她以前喜欢赤脚站在地板上,脚背很瘦很窄,后来她总是穿一双一样瘦窄的拖鞋,走路不带声音。她走路慢,说话也有些含糊,明明九十多岁了,但还是有一双少女般的眼睛。她麻将打得不好,但是喜欢。小辈们变着法子输给她,她知道大家的小把戏,输也欢喜,赢也欢喜。她有一种永远快乐的面孔,快乐在眼角,在心的深处,在她所在的每一寸空气里。有一次家庭聚会,她的后辈们向我们开玩笑,说三奶奶牌算得稀里糊涂,但是还是喜欢玩,她穿着高领的毛衣,坐在一侧,笑得像一个羞涩腼腆的少女,她被后辈们宠爱着,因此永远年轻。
三奶奶是我的爷爷的姐妹,是奶奶的小姑子。也是奶奶关系最好的闺蜜。每一年或者两年,奶奶会过去上海和她住,或者她跑到乡下和奶奶住,老两姐妹睡在一张床上,能够讲话到天明。我一向和奶奶睡,但三奶奶来了,我也很乐意把床铺的另一半让给她,到小房间去住。每天早上,我冲进她们的卧室,两个老人的面孔在阳光中显得很温暖,那个瞬间可以描述为快乐。临行前奶奶整理行装,都会忍不住笑出来。这种快乐捂不住,像是苍老的躯壳中生发的嫩绿芽尖。
老人的年纪到了一个阶段,衰老就像是被冻结了。我从记事起,三奶奶就是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但是十多年来她没有改变过,大概是皱纹已经密布,所以再不能增添一条,头发依然银白,时光爬升只使这光泽更明亮。她很高,走路不便,但是不显得佝偻,她很瘦,但是特别有气质。时间是静止的,越靠近她,便越觉得安宁。有一次听到长辈讲的一个故事,八七年是我们家的多事之秋,爷爷病重,小爹车祸,人事不顺。一天早上,爸爸打开院门,发现她正倚靠在门口。原来,她从上海到乡下来探望,赶了一整天的路,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正是凌晨四五点。舍不得吵醒亲人,她便一直静静站在门口等待……辛波斯卡说“我的灵魂朴素,如梅子的核”,凌晨寂静的村庄里,院墙之外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姑娘,她有着一颗梅子一样朴素的灵魂。
村庄里有很多这样朴素的灵魂,但苦难从不另眼相待。更早几年,贫穷和饥荒熬干了村庄的骨髓,什么都要用票,什么都没有。奶奶派一个儿子,拎着一筐蛋,走路几公里到海子,在滩涂中坐船去上海找三奶奶。船要开一天,有时开,有时半路还得折返。周周折折,到达已经是第二天。三奶奶总是省出许多饭菜,温着等待到访的孩子。那年头穷困到吃饭都感到羞怯,爸爸说他吃了一碗,不好意思再添,三奶奶温柔又强硬的再给他盛了一碗,说“孩子吃,到姑姑这里,一定给你吃饱”。我经常听这个类型的故事,每每听到都有触动。奶奶是一个非常坚强和倔强的人,从不诉苦,也不喜欢提旧事中灰暗的一面。她给我讲的故事都很温暖––––她小的时候,日军来轰炸,漫天飞弹片,家里人把两张八仙桌拼起来,上面铺上两层几十年的旧棉被。她并不渲染气氛的紧张,只告诉我一家人躲在桌子底下多有趣。
打断这种时间停滞般的安宁的,往往是一场大病,或是安静的死亡。三奶奶的离开没有什么动静,很轻很轻,消息在我们的心上冲突,撞了一圈。她的灵魂大概被一阵风送回了村庄,变成一颗小草,或者一棵树。
我想起好几年前,我和爸爸到山中扫墓,下山的时候被山火困住了。火苗在身边的树丛里蹿,照亮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坟堆。人活在世是如此的轻与薄,多么细微和渺小,来来往往,留不下什么踪迹。山火照亮了一个两个墓碑上被涂黑的名字,也许我下山的脚步,便携带了他们存在的证据。温柔的三奶奶,当她站在院墙外的故事被我听闻,我就分得了她灵魂的片缕,哪天我变成了一朵小花,一棵树,也会托一只燕子,或是一缕风,传递我的音讯。
她特别瘦,因此皱纹很深。但这些皱纹也让她看起来很美。我很难形容这种美,这是一种旧式的女人味。我印象里,她瘦削的身体上套着羊绒衫,腿很长,裤子很修身,能看出年轻时的匀称。她以前喜欢赤脚站在地板上,脚背很瘦很窄,后来她总是穿一双一样瘦窄的拖鞋,走路不带声音。她走路慢,说话也有些含糊,明明九十多岁了,但还是有一双少女般的眼睛。她麻将打得不好,但是喜欢。小辈们变着法子输给她,她知道大家的小把戏,输也欢喜,赢也欢喜。她有一种永远快乐的面孔,快乐在眼角,在心的深处,在她所在的每一寸空气里。有一次家庭聚会,她的后辈们向我们开玩笑,说三奶奶牌算得稀里糊涂,但是还是喜欢玩,她穿着高领的毛衣,坐在一侧,笑得像一个羞涩腼腆的少女,她被后辈们宠爱着,因此永远年轻。
三奶奶是我的爷爷的姐妹,是奶奶的小姑子。也是奶奶关系最好的闺蜜。每一年或者两年,奶奶会过去上海和她住,或者她跑到乡下和奶奶住,老两姐妹睡在一张床上,能够讲话到天明。我一向和奶奶睡,但三奶奶来了,我也很乐意把床铺的另一半让给她,到小房间去住。每天早上,我冲进她们的卧室,两个老人的面孔在阳光中显得很温暖,那个瞬间可以描述为快乐。临行前奶奶整理行装,都会忍不住笑出来。这种快乐捂不住,像是苍老的躯壳中生发的嫩绿芽尖。
老人的年纪到了一个阶段,衰老就像是被冻结了。我从记事起,三奶奶就是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但是十多年来她没有改变过,大概是皱纹已经密布,所以再不能增添一条,头发依然银白,时光爬升只使这光泽更明亮。她很高,走路不便,但是不显得佝偻,她很瘦,但是特别有气质。时间是静止的,越靠近她,便越觉得安宁。有一次听到长辈讲的一个故事,八七年是我们家的多事之秋,爷爷病重,小爹车祸,人事不顺。一天早上,爸爸打开院门,发现她正倚靠在门口。原来,她从上海到乡下来探望,赶了一整天的路,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正是凌晨四五点。舍不得吵醒亲人,她便一直静静站在门口等待……辛波斯卡说“我的灵魂朴素,如梅子的核”,凌晨寂静的村庄里,院墙之外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姑娘,她有着一颗梅子一样朴素的灵魂。
村庄里有很多这样朴素的灵魂,但苦难从不另眼相待。更早几年,贫穷和饥荒熬干了村庄的骨髓,什么都要用票,什么都没有。奶奶派一个儿子,拎着一筐蛋,走路几公里到海子,在滩涂中坐船去上海找三奶奶。船要开一天,有时开,有时半路还得折返。周周折折,到达已经是第二天。三奶奶总是省出许多饭菜,温着等待到访的孩子。那年头穷困到吃饭都感到羞怯,爸爸说他吃了一碗,不好意思再添,三奶奶温柔又强硬的再给他盛了一碗,说“孩子吃,到姑姑这里,一定给你吃饱”。我经常听这个类型的故事,每每听到都有触动。奶奶是一个非常坚强和倔强的人,从不诉苦,也不喜欢提旧事中灰暗的一面。她给我讲的故事都很温暖––––她小的时候,日军来轰炸,漫天飞弹片,家里人把两张八仙桌拼起来,上面铺上两层几十年的旧棉被。她并不渲染气氛的紧张,只告诉我一家人躲在桌子底下多有趣。
打断这种时间停滞般的安宁的,往往是一场大病,或是安静的死亡。三奶奶的离开没有什么动静,很轻很轻,消息在我们的心上冲突,撞了一圈。她的灵魂大概被一阵风送回了村庄,变成一颗小草,或者一棵树。
我想起好几年前,我和爸爸到山中扫墓,下山的时候被山火困住了。火苗在身边的树丛里蹿,照亮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坟堆。人活在世是如此的轻与薄,多么细微和渺小,来来往往,留不下什么踪迹。山火照亮了一个两个墓碑上被涂黑的名字,也许我下山的脚步,便携带了他们存在的证据。温柔的三奶奶,当她站在院墙外的故事被我听闻,我就分得了她灵魂的片缕,哪天我变成了一朵小花,一棵树,也会托一只燕子,或是一缕风,传递我的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