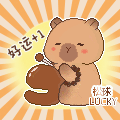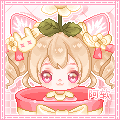—
(浅浅笑语)
优秀帖
(2023-10-18 16:28)
—
【中篇】
【书名】《共白首》
【作者】一朵一
【小说类型】 浪漫言情
【授权类型】【B 级授权】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合法人,并承诺主动在派派小说论坛原创文学版块内进行作品更新。在不发生重复授权的前提下,我保留个人向其他媒体投稿的权利,并将信息及时反馈给派派小说论坛。未经派派小说论坛或本人同意,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总字数】 7508字
梁宁悠出生在清水镇,取名宁悠,想的是让女儿一生顺遂,安宁无忧。父亲是镇上的秀才,凡事家里有点余钱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父亲的私塾来启蒙,如果家境贫寒一些,父亲也让孩子在旁边听读,也不收束脩。庄户人家,不求孩子能有多大出息,但凡能识点字也是好的。平时还会替人写写书信和状纸,补贴一下家用。
母亲本是小户人家的庶女,嫁个父亲以后,夫妻恩爱,平时在家里绣绣花,打理一下家事,家里就还剩一户人家的帮佣,钱婆婆帮忙料理一下家里的粗活和厨房的活计,张管事就成天跟着父亲在外走动,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小翠,比梁宁悠大了五岁了,从小当就小玩伴陪她长大。
家里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夫妻和美,梁宁悠也是在千娇万宠中长大的。平日里,母亲在内宅教她绣花,父亲也在闲暇时刻手把手的教她写字,人生的前七年里,梁宁悠过的很是顺遂。
七岁那年,隔壁搬来了张寡妇一家,她就就一个孩子张思君。张寡妇手里还有点闲钱,就把孩子送到梁宁悠父亲的私塾里读书。张思君眉目清俊,才思敏捷,甚是得梁父的喜爱,在私塾中也是百般照料。
梁母见张思君孤儿寡母的可怜,平日是也是多相走动,带着张母一起绣花,然后送达县里去售卖,补贴家用。
张思君十岁时,去考取了童生,童生放榜那天,张寡妇还特意的摆了一桌酒来庆贺。
宴席上,酒至半酣,思量这张思君少年得意,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小小年纪就能考取童生,也算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就算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小子也万不敢欺辱了宁悠去。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给梁宁悠和张思君定了亲。约定梁宁悠及笄时,双方成亲。
张思君见宁悠,小小年纪,眉目秀美,知书达理,端庄持重,隐隐是给小美人胚子,心里更是欢喜万分,面上不显,平日里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梁家多待上一阵,在县上买上一些女生喜欢的小玩意,有时候是根糖葫芦,有时候是釵环,让张母帮忙带给了宁悠。
宁悠收到礼物也甚是喜欢,见张母也亲切,帮忙做一些手工帕子或者衣服鞋帽带给了张思君,宁悠只觉得,隔壁的思君哥是个顶好的人,未来也值得依靠。两年间,两人情愫暗生。
好景不长,两年后的一天,梁母将绣品送给绣房时,遇到了县令家的公子,王公子瞧着梁母容貌秀美,身段婀娜,起了色心,一声令下,就强撸了梁母进了府衙。
梁父在家等了两天,一直等不到梁母回来。多方打听,才知晓梁母被县衙强撸了去,便只身前往县衙讨要人去。王公子从小就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纨绔做派,县令也是管不住的,梁父还没走到县衙的门口,被七八个护院直接拦在了半路,一顿乱棍之下,梁父被打的口吐鲜血。
等梁父晚上被抬回清水镇的时候,已经是进的气少,出的气多了,没撑到三更,便撒手人寰,徒留梁宁悠趴在梁父身上哭泣。张母从隔壁赶来,帮宁悠一起料理了丧事,张思君听闻此事,也是气愤不已,于情,他与宁悠定下婚事,他们是未婚夫妻,不能置之不理,与理,梁父是他的启蒙恩师,此仇不报,乃是不忠不孝,直接一纸诉状告到了知府了。
接到了诉状,知府马上通知了县令,县令本就是他管辖领域的人,如果县令出事,上峰怕是治他一个管理无能的罪过,影响他的升迁。奈何知府和县令本是一丘之貉,县令听闻自己儿子强撸民妇。直接将其痛骂一通,怪他不知道好歹,做事不分轻重闹出了人命,又挑选了几样礼品加以重金,一起送到了知府衙门,望知府能转圜一二。
知府收到了银票,以无实证和认证为由,判他诬告官员,杖责了二十棍张思君。
县令后宅,梁母听闻夫君讨人被人打死,张思君又被杖责,苦闷不已,王公子还拿着这事不停的讽刺贱民多作怪,自寻死路。梁母想着夫君已逝,自己清白已失,趁着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拿出发簪直接刺死了王公子,自己则自悬东南枝,自我了断了去。
张思君下半身是血的抬回了清水镇,他面容惨败,嘴唇干裂出血,整个人被打的半死不活的,张母和梁宁悠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是张县令从中作怪,奈何他们官官相护,思君才考取童生,梁父已逝,根本就无法与他们抗衡,只能另想他法。梁宁悠在梁家和张家走动,照顾张思君,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第三日凌晨,钱衙役本想着梁夫子平日与人为善,自家的小弟在私塾中,梁父也多加照料。趁着天黑,偷偷来到了清水镇,敲了敲梁家的门,告之宁悠,梁母自缢,尸体被扔在了乱葬岗,县令现在正带着其他人来清水镇抓人,让他们早些逃跑。
宁悠得知这个消息,赶紧去了张家一起讨论下面怎么办。张思君苦死良久。
“清水镇是不能待下去了,县令和知府官官相护,就算能上告,也告不赢,梁夫子的仇眼下只能委屈阿宁隐忍,待我日后考取功名,必将给梁夫子讨回公道。”
“那现下我们如何是好,县令带人要抓我们回去。”
“现在我们只能先走,趁着天还没大亮,我们收拾一点细软,先走,梁夫人的遗骸让钱婆婆他们帮忙收一下,眼下保命要紧,县令不会放过我们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阿宁节哀,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当天,张母带着张思君和宁悠一起前往了后山,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一直到了风起县才安定了下来。
县令到了清水镇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梁家就剩下钱婆婆一家,没法找梁宁悠偿命。只能在屋里一通打砸后,就回了县上。
在风起县,张母一行人人生地不熟的,找了一房小院住下,张思君和宁悠以兄妹相称呼,张母平日帮周围的人浆洗衣物,张思君去县里的私塾上学,每日早出晚归,晚上帮人抄书度日,宁悠别无长技,打理一下家务,平日里绣绣花,想着补贴家用,从家里带出来的银两所剩无几。
日复一日,张母身体每况日下,半年后的一天,她将宁悠和张思君一起叫到了床前。
“君儿,你可知为何你唤思君吗?我和你父本是青梅竹马,媒妁之言,父母之令,我和你父成亲后,你父日夜苦读,三年后,你父去京里科考,我才发现我怀孕了,但是你父去此去杳无音信,我日夜思念,给你起名思君。我托人去了京里问询,也没有丝毫回音,十几年来,我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我怕是等不到他回来了。现在我怕是不行了,你和宁悠还小,也没人能托付,县令还在搜寻我们,你们北上试试,去京城看看,一来可以找一下你生父,而来,躲一下狗县令,我走后,你两相互扶持,切莫生了嫌隙,以后你们才是最亲的人了。”
言罢,过了几日,张母也撒手人寰,他们安顿了后事,一起北上。
这年,张思君14岁,梁宁悠11岁。
他们带着仅剩的银两,一路上餐风露宿,饿了就吃早就准备的干粮,困了就找间破庙栖身,一路走走停停,鞋子不知道走破了多少双,走了大半年才到京城,此时,他们身上的衣服破败不堪,守卫更是将当他们当做乞儿驱逐。
在城外的破庙里,他们梳洗一番,换上稍微整洁一点的衣物,一起去城里打听。银钱不多,宁悠就在城里找了一个浆洗衣物的活计,冬天的水又冷又冰,手指都被冻成了萝卜,肿的厉害。有时候,衣物多的洗不完,连饭也顾不得吃,拿着干硬的干粮,吞的狼吐虎咽的,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冻疮化开,手指又痒又疼,溃疡流脓,洗衣服的时候,血肉模糊,张思君看着的宁悠的手,眼底氤氲着寒霜,凝结成冰,又有不舍,只是在夜里,一次又一次的握着她的手,谁知道,两年前这手还能绣花写字。
白日张思君在城里多方打听,夜里就回到破庙里栖身,破庙里还有一些乞儿在,半夜总是觉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宁悠看,张思君便半倚着廊柱,合着眼假寐。
他们不停的在问,京中可有张姓的人家,张是大姓,他们一户一户的打听,一户一户的走访,半年里,他们寻遍的张姓的京城人家,现在就只有一家从四品的礼部张侍郎还没确认。
张侍郎听闻是十五年前的探花郎,那时他风华正茂,文采斐然,出榜的当天,就被赵尚书揽为女婿,将膝下独女许配给了探花郎,婚后,张侍郎一心一意的对待赵小姐,两人夫妻和美,相敬如宾,连个通房丫头都不曾有,两人孕育一子一女,这十五年里,张侍郎凭借着赵尚书的人脉的,长袖善舞的能耐,一步一步的官至侍郎。
从四品官员的的官邸根本就进不去,张思君只能在他每日下朝的必经之路上等,终于在三日后的傍晚,等到了下衙回家的张侍郎。
张思君站在金乌街的接到上,对着轿子中的人到“小生张思君,前来给大人请安,大人可知晓清水县的张家村的张秦氏?”
轿子中的人迟迟没有回应,半晌才抬起轿帘上下大量了他一眼道
“本官虽然也是清水镇人士,但是从未知晓什么张秦氏。”
张思君看着张侍郎和他眉目如出一辙,但是听闻他的言语,不由得一窒,这片刻时间,张侍郎早就起轿走了。
张思君浑浑噩噩的回到了破庙,思量了张侍郎的眉眼和五官,明明就和他是一个莫子刻出来的,怎么不肯能不是他父亲。如今,京城里的张姓人家都遍寻了一遍,如果他不是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如果他就是呢!!分明是为了攀附权贵,抛妻弃子,如今,张侍郎他矢口否认,也别无他法。
梁宁悠坐在他身边的破草席上,见他神思黯然,只得安慰他,或许我们还有遗漏的地方,我明天再去酒肆那边打听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张姓人家去了外地。
月明星稀,午夜时刻,一身黑衣的张侍郎来到了破庙,摇了摇还在假寐中的张思君,将他唤到了庙外。
看着张思君的眉目,张侍郎问“你娘如今可还好?你多大了?叫什么?”
“我娘已经仙去,我叫张思君,15岁了,可怜我娘临终时,还对你念念不忘,没想到你早就停妻另娶,不认我们母子,你现在来作甚?”
张侍郎从怀中拿出一叠银票,塞到了张思君怀里。
“是我对不起你娘,你还小,你不懂,你拿着这些钱,这里足够你下半辈子安稳无恙,赶紧走,不要再来京城了,到外面也别说你是我的儿子,就当我们父子从未见过。”
说完,转身回去了,张思君看着人影远去,不明白他既然不认他们母子,又何必假惺惺的送来银票,又当又立,当真是虚伪的很。
第二日,张思君将昨夜张侍郎找他的事,一五一十的告知了梁宁悠,两人商议一番,觉得这几日去京中购置一些干粮,买些衣物,然后回到风起镇去,有了这笔钱,张思君可以安定的在私塾里读书,考取功名后,他们也不会太过艰难,两人相互扶持,总有大仇得报的一天。
当晚,五六个黑衣人劲直闯进了破庙,直奔张思君而来,手起刀落之间,张思君下半身已血流如注,张思君从睡梦中痛醒,捂着下半身的痛的直不起腰。
“记住,张家的一切都和你无关,你再敢肖想,小心的你的小命!”黑衣人丢下这句话,直接离开了破庙。
梁宁悠扶着张思君,看着黑衣人,恨自己新单影只,恨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连冲上去给思君哥报仇的勇气也没有,城门一关,京城请郎中根本不可能,只能去郊外的的望京村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大夫能给张思君医治。
趁着月色,梁宁悠深一脚浅一脚拉着板车跑向了望京村,万幸村里有赤脚游医,等游医止住了血,煎了药,服侍张思君喝下后,梁宁悠才觉得自己手上火辣辣的疼,一看,手上早就磨破了口子。张思君的血虽然止住了,勉强保下了一条命,但是下半身就无能为力了。
次日醒来,梁宁悠一直不停的围着张思君说话,就盼他能回上一两句,但张思君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梁家蒙冤枉,大仇未报,思君哥,昨天的那些也是冲着你来的,你起来,我们一起报仇去,我陪你好吗,你应我一下的啊,思君哥。”
梁宁悠握着张思君的手,张思君仿若睡着了一样,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有垂下的眼睫颤动了一下。此后半月,梁宁悠一直小心的照料着张思君,开始张思君始终一言不发。突然有一天,等梁宁悠煎药回来的时候,床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只留了一封书信在床上。
阿宁,这辈子我只能是你的思君哥,你也只能是我的阿宁了,娘亲临终时将你交付与我,事到如今,我只能辜负她的期望,银钱我全部留在枕头下,你重新找个人嫁了吧,我们的婚约到此为止。如果有下半辈子,我们下辈子再续前缘。
梁宁悠拿着书信追了出去,可是空无一人。枕头下,是他们所有的银两,也就是说,张思君身无分文的走了,如今,他新伤刚愈,他能去哪里?
是夜,张侍郎一脚踹开了住宅的房门,张赵氏正坐在梳妆台前,两个小丫头正服侍拆卸头上的釵环,张赵氏一看张侍郎一脸的怒意,也明白他怒从何来,挥了挥手,让两个小丫头退了下去,自己慢悠悠的起身里坐到了床前。
“老爷这般生气为何?还为那小杂种生气呢?”
“赵氏,我已经答应你不去找秦氏母子了,你怎么还对思君下手?他怎么说也是我亲身的孩子,你怎么能废了他?”
“老爷,慎言啊,你当初为了攀附我尚书房,可是说并未娶亲生子,除了我生下锦儿和玉儿,你哪来的孩子?”
“你!”
“张之唯,做了我尚书府的女婿,收起你那些心思,你若识好歹不去找那秦氏母子,我也没去动手,怪就怪你自己不识趣,非去见那个小畜生,这张府的一切,以后都是我锦儿的,锦儿也是你的亲生孩子,何必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生气呢?况且我只是废了那小子,给他留了一条命,为的也只是让他不能喝锦儿相争罢了。”
一番软硬兼施下来,张侍郎也只能叹息。尚书府家大业大,在朝廷只手遮天,怪也只怪那孩子命不好。如果安安生生的在清水镇一辈子,也没有这无妄之灾。
三个月后,梁宁悠重新见到了张思君。
那日天晴,梁宁悠拿着自己绣好的帕子去绣房售卖,遇到了齐王的仪仗,浩浩荡荡的二三十人行至路边,中间一青衣小厮跪趴在的地上,齐王踩着他的背上了马匹,小厮起立的时候,与梁宁悠四目相对,梁宁悠认出来了,他就是张思君,张思君难堪的侧过脸,跑着追上了齐王的马匹
梁宁悠怔怔的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她知道,他要报仇,他要权利,但是没想到的是他走了这么一条路。
梁宁悠回去后,回到了望京村收拾了一下细软,就在京里拿着之前的银两,在城里租了一房小院,她给张思君缝制了衣衫,还准备了一些吃食,拿到了齐王府的后门,托人带给张思君,可是门房把东西全部都退了回来,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可那天他明明就看见他了,他不认她了。
梁宁悠每天都送,可是一直都被退了回来,一来二去,门房也烦了,哪怕是塞了银子给他,也不代送东西了。梁宁悠没办法,只能每天守在后门,期待能见到张思君。
终于在一个月后,梁宁悠终于堵到了外出办事的张思君。张思君视而不见,直接略过了梁宁悠,仿若从未见过。
梁宁悠没办法,拿着剩余的银钱,在齐王府的斜对面,支了一个小铺子,售卖一些手帕香囊,梁宁悠看着张思君一步一步的从牵马小厮,到齐王的贴身小厮,他越来越忙,有时候回来时,衣衫上都带着血迹,她不知道他帮齐王做了什么,只能日复一日的蹲守在齐王府的门前。
三年后,梁宁悠及笄了,她拦住回府的张思君。
“思君哥,我及笄了,你什么时候来娶我?”
“荒唐。”
“可是这是父母之命,我们订过亲的。”
“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现在的状况?”
“我知道。”
张思君盯着梁宁悠看了许久,终究还是转身回去了。
半年后的一天,张思君半夜来到了梁宁悠的住处,此时已失隆冬时节,张思君披星戴月的干了过来,头上和肩上都是落雪。梁宁悠看着张思君很是欢喜,连忙起身给张思君端茶倒水。张思君沉默了一会说:“清水镇的知府和县令,我帮你处理了,你回去吧,回去帮我夫子告罪,是我无能,才让他们的大仇现在才报。回去好好祭拜一下他们,你也找个好人家嫁了,别等我了。”
“不,我不走,我夫君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不用说,你现在是用什么立场来管我呢?”
张思君沉默的看着梁宁悠,梁宁悠已经及笄了,像她娘一样出落的貌美如花,这几年她在齐王府旁边摆摊,不知道招惹了多少地痞流氓,都是他暗中找人收拾了,这才没有人生事。如今他在京城步步为营,替齐王处理不能在明面上的事情,明刀暗箭的,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耐护住她。而且齐王前几日就试探的问过,门口的梁宁悠和他是什么关系,他道是之前订过亲,齐王这才按下了话题,没说什么。梁宁悠不能在京里待下去了。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想的处境,齐王已经向我提过你了,你不能再呆在这里了。”
“那您娶我不就好了,他也不会觊觎我了。”
“不可能,我不能耽误你了,宁悠,你是个好姑娘,值得更好的人,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听话好吗,走吧,离开京城,别回来了。”
“不,这辈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夫君,我娘从小就告诉我从一而终,我们定过亲的,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
张思君见梁宁悠冥顽不灵,也无可奈何,趁着夜色回去了。
此后五年,张思君再也没有踏足这个院子,梁宁悠渐渐的从街边支个小摊,后来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在边上盘了一家小店,开起了绣房。日日夜夜的在齐王府门口守望。
老皇帝年岁渐长,底下的几个皇子都蠢蠢欲动,齐王府在这片腥风血雨种终于杀出来重围,齐王登基了,张思君陪着齐王登基,靠着从龙之功,摇身一变,成为了首领太监。
晚秋的一天,张思君又来到了梁宁悠的小院,看着宁悠依旧梳着少女的发髻,她今年已经是21岁的老姑娘了,一直都云英未嫁,索性这几年张思君一直都没有联系宁悠,她对朝堂之事也是一无所知,他帮着新帝做了太多不能放在明面上的事,事关朝廷,新帝多疑,如今他自己亦是伴君如伴虎。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周遭虎视眈眈,不知道有多少人躲在暗处想把他拉下位。
“梁姑娘,今天来这里,咱家就有话直说了,念着好歹同乡情谊,咱家安排人送你出京,以后你是回清水镇也好,去其他地方也罢,就是不能出现在京里了,这银票你拿着,管你下半生无忧,梁姑娘,你别不识趣啊。”
说着,旁边的人就递上了一个木盒,里面满满当当的一摞银票。听着张思君叫自己梁姑娘,宁悠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涩,什么时候了,他们变得这么的生疏,总角之年相识相知,金钗之年相互扶持依靠,及笄之年的守望,如今自己已过桃李年华,换来他的一声梁姑娘,也罢,人与人的缘分,有些人是越来越近,而自己与他相携相远,现下他是大权总揽的首领太监,自己不过是个小掌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那,谢过张公子。”
梁宁悠接过木盒,诚心道谢。收拾了一下细软,在两个护卫的守护下,梁宁悠出了京城。
不过三日时间,京城便发生了一件大事,据说赵尚书私铸银钱,卖官鬻爵,被刑部收押,张侍郎更是贪污受贿,府中抄出的金银更是不计其数,赵尚书一党被查抄的干净,男的被判斩首或流放,女子充入教坊司。
梁宁悠在望京村听闻消息的时候,替张思君感到高兴,他终于为自己报仇了。不过仅仅一个月之后,梁宁悠又听闻宫中张思君以下犯上,欺君罔上,判凌迟处死,尸体也被仍在了乱葬岗。等梁宁悠收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七八日。
等她赶到乱葬岗的时候,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一点也看不出他生前丰神俊朗的样子。她替张思君收敛了尸骨,一把火烧成了灰,装在一个小罐子里,在冬日里,抱着罐子南下。
终于在年前回到了清水镇,她把张思君安葬在了她爹娘的旁边,回家的时候,家里就剩下了大她五岁的小翠,钱婆婆和张叔早在前几年过失了,小翠现在已经嫁人,还剩了一个女儿。
梁宁悠站在儿时的院子里,回想自己的一生,冬日雪纷纷扬扬,大雪落满了梁宁悠的头发,十二年前,你带着我来到了京城,十二年后,我带你回家,你看这雪,像不像我们儿时在清水镇时候下雪,那时候,大雪淋了我们满头,白了头发,原来我们的这一辈子是这么短。这辈子,你未娶,我也未嫁,但是曾白首过。这辈子我爹娘与人为善,却不得善终,我自问无愧天地,漂泊半生,如今也是孤家寡人一个,现在大仇得报,也该寻另一半了。
除夕夜,梁宁悠自悬而亡。
【书名】《共白首》
【作者】一朵一
【小说类型】 浪漫言情
【授权类型】【B 级授权】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合法人,并承诺主动在派派小说论坛原创文学版块内进行作品更新。在不发生重复授权的前提下,我保留个人向其他媒体投稿的权利,并将信息及时反馈给派派小说论坛。未经派派小说论坛或本人同意,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总字数】 7508字
梁宁悠出生在清水镇,取名宁悠,想的是让女儿一生顺遂,安宁无忧。父亲是镇上的秀才,凡事家里有点余钱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父亲的私塾来启蒙,如果家境贫寒一些,父亲也让孩子在旁边听读,也不收束脩。庄户人家,不求孩子能有多大出息,但凡能识点字也是好的。平时还会替人写写书信和状纸,补贴一下家用。
母亲本是小户人家的庶女,嫁个父亲以后,夫妻恩爱,平时在家里绣绣花,打理一下家事,家里就还剩一户人家的帮佣,钱婆婆帮忙料理一下家里的粗活和厨房的活计,张管事就成天跟着父亲在外走动,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小翠,比梁宁悠大了五岁了,从小当就小玩伴陪她长大。
家里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夫妻和美,梁宁悠也是在千娇万宠中长大的。平日里,母亲在内宅教她绣花,父亲也在闲暇时刻手把手的教她写字,人生的前七年里,梁宁悠过的很是顺遂。
七岁那年,隔壁搬来了张寡妇一家,她就就一个孩子张思君。张寡妇手里还有点闲钱,就把孩子送到梁宁悠父亲的私塾里读书。张思君眉目清俊,才思敏捷,甚是得梁父的喜爱,在私塾中也是百般照料。
梁母见张思君孤儿寡母的可怜,平日是也是多相走动,带着张母一起绣花,然后送达县里去售卖,补贴家用。
张思君十岁时,去考取了童生,童生放榜那天,张寡妇还特意的摆了一桌酒来庆贺。
宴席上,酒至半酣,思量这张思君少年得意,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小小年纪就能考取童生,也算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就算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小子也万不敢欺辱了宁悠去。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给梁宁悠和张思君定了亲。约定梁宁悠及笄时,双方成亲。
张思君见宁悠,小小年纪,眉目秀美,知书达理,端庄持重,隐隐是给小美人胚子,心里更是欢喜万分,面上不显,平日里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梁家多待上一阵,在县上买上一些女生喜欢的小玩意,有时候是根糖葫芦,有时候是釵环,让张母帮忙带给了宁悠。
宁悠收到礼物也甚是喜欢,见张母也亲切,帮忙做一些手工帕子或者衣服鞋帽带给了张思君,宁悠只觉得,隔壁的思君哥是个顶好的人,未来也值得依靠。两年间,两人情愫暗生。
好景不长,两年后的一天,梁母将绣品送给绣房时,遇到了县令家的公子,王公子瞧着梁母容貌秀美,身段婀娜,起了色心,一声令下,就强撸了梁母进了府衙。
梁父在家等了两天,一直等不到梁母回来。多方打听,才知晓梁母被县衙强撸了去,便只身前往县衙讨要人去。王公子从小就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纨绔做派,县令也是管不住的,梁父还没走到县衙的门口,被七八个护院直接拦在了半路,一顿乱棍之下,梁父被打的口吐鲜血。
等梁父晚上被抬回清水镇的时候,已经是进的气少,出的气多了,没撑到三更,便撒手人寰,徒留梁宁悠趴在梁父身上哭泣。张母从隔壁赶来,帮宁悠一起料理了丧事,张思君听闻此事,也是气愤不已,于情,他与宁悠定下婚事,他们是未婚夫妻,不能置之不理,与理,梁父是他的启蒙恩师,此仇不报,乃是不忠不孝,直接一纸诉状告到了知府了。
接到了诉状,知府马上通知了县令,县令本就是他管辖领域的人,如果县令出事,上峰怕是治他一个管理无能的罪过,影响他的升迁。奈何知府和县令本是一丘之貉,县令听闻自己儿子强撸民妇。直接将其痛骂一通,怪他不知道好歹,做事不分轻重闹出了人命,又挑选了几样礼品加以重金,一起送到了知府衙门,望知府能转圜一二。
知府收到了银票,以无实证和认证为由,判他诬告官员,杖责了二十棍张思君。
县令后宅,梁母听闻夫君讨人被人打死,张思君又被杖责,苦闷不已,王公子还拿着这事不停的讽刺贱民多作怪,自寻死路。梁母想着夫君已逝,自己清白已失,趁着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拿出发簪直接刺死了王公子,自己则自悬东南枝,自我了断了去。
张思君下半身是血的抬回了清水镇,他面容惨败,嘴唇干裂出血,整个人被打的半死不活的,张母和梁宁悠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是张县令从中作怪,奈何他们官官相护,思君才考取童生,梁父已逝,根本就无法与他们抗衡,只能另想他法。梁宁悠在梁家和张家走动,照顾张思君,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第三日凌晨,钱衙役本想着梁夫子平日与人为善,自家的小弟在私塾中,梁父也多加照料。趁着天黑,偷偷来到了清水镇,敲了敲梁家的门,告之宁悠,梁母自缢,尸体被扔在了乱葬岗,县令现在正带着其他人来清水镇抓人,让他们早些逃跑。
宁悠得知这个消息,赶紧去了张家一起讨论下面怎么办。张思君苦死良久。
“清水镇是不能待下去了,县令和知府官官相护,就算能上告,也告不赢,梁夫子的仇眼下只能委屈阿宁隐忍,待我日后考取功名,必将给梁夫子讨回公道。”
“那现下我们如何是好,县令带人要抓我们回去。”
“现在我们只能先走,趁着天还没大亮,我们收拾一点细软,先走,梁夫人的遗骸让钱婆婆他们帮忙收一下,眼下保命要紧,县令不会放过我们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阿宁节哀,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当天,张母带着张思君和宁悠一起前往了后山,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一直到了风起县才安定了下来。
县令到了清水镇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梁家就剩下钱婆婆一家,没法找梁宁悠偿命。只能在屋里一通打砸后,就回了县上。
在风起县,张母一行人人生地不熟的,找了一房小院住下,张思君和宁悠以兄妹相称呼,张母平日帮周围的人浆洗衣物,张思君去县里的私塾上学,每日早出晚归,晚上帮人抄书度日,宁悠别无长技,打理一下家务,平日里绣绣花,想着补贴家用,从家里带出来的银两所剩无几。
日复一日,张母身体每况日下,半年后的一天,她将宁悠和张思君一起叫到了床前。
“君儿,你可知为何你唤思君吗?我和你父本是青梅竹马,媒妁之言,父母之令,我和你父成亲后,你父日夜苦读,三年后,你父去京里科考,我才发现我怀孕了,但是你父去此去杳无音信,我日夜思念,给你起名思君。我托人去了京里问询,也没有丝毫回音,十几年来,我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我怕是等不到他回来了。现在我怕是不行了,你和宁悠还小,也没人能托付,县令还在搜寻我们,你们北上试试,去京城看看,一来可以找一下你生父,而来,躲一下狗县令,我走后,你两相互扶持,切莫生了嫌隙,以后你们才是最亲的人了。”
言罢,过了几日,张母也撒手人寰,他们安顿了后事,一起北上。
这年,张思君14岁,梁宁悠11岁。
他们带着仅剩的银两,一路上餐风露宿,饿了就吃早就准备的干粮,困了就找间破庙栖身,一路走走停停,鞋子不知道走破了多少双,走了大半年才到京城,此时,他们身上的衣服破败不堪,守卫更是将当他们当做乞儿驱逐。
在城外的破庙里,他们梳洗一番,换上稍微整洁一点的衣物,一起去城里打听。银钱不多,宁悠就在城里找了一个浆洗衣物的活计,冬天的水又冷又冰,手指都被冻成了萝卜,肿的厉害。有时候,衣物多的洗不完,连饭也顾不得吃,拿着干硬的干粮,吞的狼吐虎咽的,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冻疮化开,手指又痒又疼,溃疡流脓,洗衣服的时候,血肉模糊,张思君看着的宁悠的手,眼底氤氲着寒霜,凝结成冰,又有不舍,只是在夜里,一次又一次的握着她的手,谁知道,两年前这手还能绣花写字。
白日张思君在城里多方打听,夜里就回到破庙里栖身,破庙里还有一些乞儿在,半夜总是觉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宁悠看,张思君便半倚着廊柱,合着眼假寐。
他们不停的在问,京中可有张姓的人家,张是大姓,他们一户一户的打听,一户一户的走访,半年里,他们寻遍的张姓的京城人家,现在就只有一家从四品的礼部张侍郎还没确认。
张侍郎听闻是十五年前的探花郎,那时他风华正茂,文采斐然,出榜的当天,就被赵尚书揽为女婿,将膝下独女许配给了探花郎,婚后,张侍郎一心一意的对待赵小姐,两人夫妻和美,相敬如宾,连个通房丫头都不曾有,两人孕育一子一女,这十五年里,张侍郎凭借着赵尚书的人脉的,长袖善舞的能耐,一步一步的官至侍郎。
从四品官员的的官邸根本就进不去,张思君只能在他每日下朝的必经之路上等,终于在三日后的傍晚,等到了下衙回家的张侍郎。
张思君站在金乌街的接到上,对着轿子中的人到“小生张思君,前来给大人请安,大人可知晓清水县的张家村的张秦氏?”
轿子中的人迟迟没有回应,半晌才抬起轿帘上下大量了他一眼道
“本官虽然也是清水镇人士,但是从未知晓什么张秦氏。”
张思君看着张侍郎和他眉目如出一辙,但是听闻他的言语,不由得一窒,这片刻时间,张侍郎早就起轿走了。
张思君浑浑噩噩的回到了破庙,思量了张侍郎的眉眼和五官,明明就和他是一个莫子刻出来的,怎么不肯能不是他父亲。如今,京城里的张姓人家都遍寻了一遍,如果他不是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如果他就是呢!!分明是为了攀附权贵,抛妻弃子,如今,张侍郎他矢口否认,也别无他法。
梁宁悠坐在他身边的破草席上,见他神思黯然,只得安慰他,或许我们还有遗漏的地方,我明天再去酒肆那边打听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张姓人家去了外地。
月明星稀,午夜时刻,一身黑衣的张侍郎来到了破庙,摇了摇还在假寐中的张思君,将他唤到了庙外。
看着张思君的眉目,张侍郎问“你娘如今可还好?你多大了?叫什么?”
“我娘已经仙去,我叫张思君,15岁了,可怜我娘临终时,还对你念念不忘,没想到你早就停妻另娶,不认我们母子,你现在来作甚?”
张侍郎从怀中拿出一叠银票,塞到了张思君怀里。
“是我对不起你娘,你还小,你不懂,你拿着这些钱,这里足够你下半辈子安稳无恙,赶紧走,不要再来京城了,到外面也别说你是我的儿子,就当我们父子从未见过。”
说完,转身回去了,张思君看着人影远去,不明白他既然不认他们母子,又何必假惺惺的送来银票,又当又立,当真是虚伪的很。
第二日,张思君将昨夜张侍郎找他的事,一五一十的告知了梁宁悠,两人商议一番,觉得这几日去京中购置一些干粮,买些衣物,然后回到风起镇去,有了这笔钱,张思君可以安定的在私塾里读书,考取功名后,他们也不会太过艰难,两人相互扶持,总有大仇得报的一天。
当晚,五六个黑衣人劲直闯进了破庙,直奔张思君而来,手起刀落之间,张思君下半身已血流如注,张思君从睡梦中痛醒,捂着下半身的痛的直不起腰。
“记住,张家的一切都和你无关,你再敢肖想,小心的你的小命!”黑衣人丢下这句话,直接离开了破庙。
梁宁悠扶着张思君,看着黑衣人,恨自己新单影只,恨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连冲上去给思君哥报仇的勇气也没有,城门一关,京城请郎中根本不可能,只能去郊外的的望京村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大夫能给张思君医治。
趁着月色,梁宁悠深一脚浅一脚拉着板车跑向了望京村,万幸村里有赤脚游医,等游医止住了血,煎了药,服侍张思君喝下后,梁宁悠才觉得自己手上火辣辣的疼,一看,手上早就磨破了口子。张思君的血虽然止住了,勉强保下了一条命,但是下半身就无能为力了。
次日醒来,梁宁悠一直不停的围着张思君说话,就盼他能回上一两句,但张思君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梁家蒙冤枉,大仇未报,思君哥,昨天的那些也是冲着你来的,你起来,我们一起报仇去,我陪你好吗,你应我一下的啊,思君哥。”
梁宁悠握着张思君的手,张思君仿若睡着了一样,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有垂下的眼睫颤动了一下。此后半月,梁宁悠一直小心的照料着张思君,开始张思君始终一言不发。突然有一天,等梁宁悠煎药回来的时候,床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只留了一封书信在床上。
阿宁,这辈子我只能是你的思君哥,你也只能是我的阿宁了,娘亲临终时将你交付与我,事到如今,我只能辜负她的期望,银钱我全部留在枕头下,你重新找个人嫁了吧,我们的婚约到此为止。如果有下半辈子,我们下辈子再续前缘。
梁宁悠拿着书信追了出去,可是空无一人。枕头下,是他们所有的银两,也就是说,张思君身无分文的走了,如今,他新伤刚愈,他能去哪里?
是夜,张侍郎一脚踹开了住宅的房门,张赵氏正坐在梳妆台前,两个小丫头正服侍拆卸头上的釵环,张赵氏一看张侍郎一脸的怒意,也明白他怒从何来,挥了挥手,让两个小丫头退了下去,自己慢悠悠的起身里坐到了床前。
“老爷这般生气为何?还为那小杂种生气呢?”
“赵氏,我已经答应你不去找秦氏母子了,你怎么还对思君下手?他怎么说也是我亲身的孩子,你怎么能废了他?”
“老爷,慎言啊,你当初为了攀附我尚书房,可是说并未娶亲生子,除了我生下锦儿和玉儿,你哪来的孩子?”
“你!”
“张之唯,做了我尚书府的女婿,收起你那些心思,你若识好歹不去找那秦氏母子,我也没去动手,怪就怪你自己不识趣,非去见那个小畜生,这张府的一切,以后都是我锦儿的,锦儿也是你的亲生孩子,何必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生气呢?况且我只是废了那小子,给他留了一条命,为的也只是让他不能喝锦儿相争罢了。”
一番软硬兼施下来,张侍郎也只能叹息。尚书府家大业大,在朝廷只手遮天,怪也只怪那孩子命不好。如果安安生生的在清水镇一辈子,也没有这无妄之灾。
三个月后,梁宁悠重新见到了张思君。
那日天晴,梁宁悠拿着自己绣好的帕子去绣房售卖,遇到了齐王的仪仗,浩浩荡荡的二三十人行至路边,中间一青衣小厮跪趴在的地上,齐王踩着他的背上了马匹,小厮起立的时候,与梁宁悠四目相对,梁宁悠认出来了,他就是张思君,张思君难堪的侧过脸,跑着追上了齐王的马匹
梁宁悠怔怔的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她知道,他要报仇,他要权利,但是没想到的是他走了这么一条路。
梁宁悠回去后,回到了望京村收拾了一下细软,就在京里拿着之前的银两,在城里租了一房小院,她给张思君缝制了衣衫,还准备了一些吃食,拿到了齐王府的后门,托人带给张思君,可是门房把东西全部都退了回来,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可那天他明明就看见他了,他不认她了。
梁宁悠每天都送,可是一直都被退了回来,一来二去,门房也烦了,哪怕是塞了银子给他,也不代送东西了。梁宁悠没办法,只能每天守在后门,期待能见到张思君。
终于在一个月后,梁宁悠终于堵到了外出办事的张思君。张思君视而不见,直接略过了梁宁悠,仿若从未见过。
梁宁悠没办法,拿着剩余的银钱,在齐王府的斜对面,支了一个小铺子,售卖一些手帕香囊,梁宁悠看着张思君一步一步的从牵马小厮,到齐王的贴身小厮,他越来越忙,有时候回来时,衣衫上都带着血迹,她不知道他帮齐王做了什么,只能日复一日的蹲守在齐王府的门前。
三年后,梁宁悠及笄了,她拦住回府的张思君。
“思君哥,我及笄了,你什么时候来娶我?”
“荒唐。”
“可是这是父母之命,我们订过亲的。”
“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现在的状况?”
“我知道。”
张思君盯着梁宁悠看了许久,终究还是转身回去了。
半年后的一天,张思君半夜来到了梁宁悠的住处,此时已失隆冬时节,张思君披星戴月的干了过来,头上和肩上都是落雪。梁宁悠看着张思君很是欢喜,连忙起身给张思君端茶倒水。张思君沉默了一会说:“清水镇的知府和县令,我帮你处理了,你回去吧,回去帮我夫子告罪,是我无能,才让他们的大仇现在才报。回去好好祭拜一下他们,你也找个好人家嫁了,别等我了。”
“不,我不走,我夫君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不用说,你现在是用什么立场来管我呢?”
张思君沉默的看着梁宁悠,梁宁悠已经及笄了,像她娘一样出落的貌美如花,这几年她在齐王府旁边摆摊,不知道招惹了多少地痞流氓,都是他暗中找人收拾了,这才没有人生事。如今他在京城步步为营,替齐王处理不能在明面上的事情,明刀暗箭的,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耐护住她。而且齐王前几日就试探的问过,门口的梁宁悠和他是什么关系,他道是之前订过亲,齐王这才按下了话题,没说什么。梁宁悠不能在京里待下去了。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想的处境,齐王已经向我提过你了,你不能再呆在这里了。”
“那您娶我不就好了,他也不会觊觎我了。”
“不可能,我不能耽误你了,宁悠,你是个好姑娘,值得更好的人,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听话好吗,走吧,离开京城,别回来了。”
“不,这辈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夫君,我娘从小就告诉我从一而终,我们定过亲的,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
张思君见梁宁悠冥顽不灵,也无可奈何,趁着夜色回去了。
此后五年,张思君再也没有踏足这个院子,梁宁悠渐渐的从街边支个小摊,后来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在边上盘了一家小店,开起了绣房。日日夜夜的在齐王府门口守望。
老皇帝年岁渐长,底下的几个皇子都蠢蠢欲动,齐王府在这片腥风血雨种终于杀出来重围,齐王登基了,张思君陪着齐王登基,靠着从龙之功,摇身一变,成为了首领太监。
晚秋的一天,张思君又来到了梁宁悠的小院,看着宁悠依旧梳着少女的发髻,她今年已经是21岁的老姑娘了,一直都云英未嫁,索性这几年张思君一直都没有联系宁悠,她对朝堂之事也是一无所知,他帮着新帝做了太多不能放在明面上的事,事关朝廷,新帝多疑,如今他自己亦是伴君如伴虎。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周遭虎视眈眈,不知道有多少人躲在暗处想把他拉下位。
“梁姑娘,今天来这里,咱家就有话直说了,念着好歹同乡情谊,咱家安排人送你出京,以后你是回清水镇也好,去其他地方也罢,就是不能出现在京里了,这银票你拿着,管你下半生无忧,梁姑娘,你别不识趣啊。”
说着,旁边的人就递上了一个木盒,里面满满当当的一摞银票。听着张思君叫自己梁姑娘,宁悠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涩,什么时候了,他们变得这么的生疏,总角之年相识相知,金钗之年相互扶持依靠,及笄之年的守望,如今自己已过桃李年华,换来他的一声梁姑娘,也罢,人与人的缘分,有些人是越来越近,而自己与他相携相远,现下他是大权总揽的首领太监,自己不过是个小掌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那,谢过张公子。”
梁宁悠接过木盒,诚心道谢。收拾了一下细软,在两个护卫的守护下,梁宁悠出了京城。
不过三日时间,京城便发生了一件大事,据说赵尚书私铸银钱,卖官鬻爵,被刑部收押,张侍郎更是贪污受贿,府中抄出的金银更是不计其数,赵尚书一党被查抄的干净,男的被判斩首或流放,女子充入教坊司。
梁宁悠在望京村听闻消息的时候,替张思君感到高兴,他终于为自己报仇了。不过仅仅一个月之后,梁宁悠又听闻宫中张思君以下犯上,欺君罔上,判凌迟处死,尸体也被仍在了乱葬岗。等梁宁悠收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七八日。
等她赶到乱葬岗的时候,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一点也看不出他生前丰神俊朗的样子。她替张思君收敛了尸骨,一把火烧成了灰,装在一个小罐子里,在冬日里,抱着罐子南下。
终于在年前回到了清水镇,她把张思君安葬在了她爹娘的旁边,回家的时候,家里就剩下了大她五岁的小翠,钱婆婆和张叔早在前几年过失了,小翠现在已经嫁人,还剩了一个女儿。
梁宁悠站在儿时的院子里,回想自己的一生,冬日雪纷纷扬扬,大雪落满了梁宁悠的头发,十二年前,你带着我来到了京城,十二年后,我带你回家,你看这雪,像不像我们儿时在清水镇时候下雪,那时候,大雪淋了我们满头,白了头发,原来我们的这一辈子是这么短。这辈子,你未娶,我也未嫁,但是曾白首过。这辈子我爹娘与人为善,却不得善终,我自问无愧天地,漂泊半生,如今也是孤家寡人一个,现在大仇得报,也该寻另一半了。
除夕夜,梁宁悠自悬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