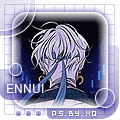公元前323年,纵横家公孙衍策划了一场“相王”运动,也就是召集许多国家共同会盟,彼此承认各自国君的王号。
“称王”是战国中期兴起的风潮。此前各诸侯的称号都是某某公、某某侯,天下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王只有周天子,楚、吴、越等国尽管早就自行称王,但中原诸侯一直视他们为蛮夷,不肯承认这些王号。如今,随着各国实力的膨胀,诸侯们终于按捺不住同样的野心,纷纷迈出僭越的最后一步,周天子由此失去最后一丝颜面。
公元前344年,最强大的魏国率先称王,国君魏侯罃正是魏惠王。此后20年里,齐、秦、韩几国也相继称王,首任称王的国君分别被称为齐威王、秦惠文王、韩宣惠王,眼下这次相王则是为了承认天下最后几个大国燕、赵、中山的王号。
作为会盟的发起者,魏惠王很难不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逢泽之会,当年他打着朝觐天子的名义召集天下十二诸侯,却又依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涂红梁柱,立起天子才能用的九斿七星之旟,还乘坐夏车、自称夏王,连名号都与天子平级,那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光辉伴随着阴影,魏国在逢泽之会十年前就已显露出颓势。公元前354年,魏国在桂陵之战中首败于齐国;同年,通过商鞅变法走上强国之路的秦国也在元里大败魏军,并夺取河西地区的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两年后(前352),秦军又在大良造商鞅的率领下攻入魏国河东,一度夺取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次年又围攻固阳,迫使其归降。
逢泽之会后,更多的败战接踵而至。公元前342年,魏国在马陵之战再次被齐国重创,“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公元前341年,齐将田盼包围魏国的平阳(今河南滑县南)。公元前340年,商鞅再度领军攻魏,用诈谋俘虏了魏将公子卬、乘势击败魏军。公元前338年,秦军又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市西)击败魏军,虏获魏军主将魏错……
公元前369年凭运气登上君位时,魏惠王从祖父文侯、父亲武侯手中继承的是一个独霸天下的强大魏国,半个世纪过去,却成功地凭实力葬送了这份霸业。他晚年向孟子回顾这一连串失败时叹:“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既源于魏惠王本人的各种决策失误,也与魏国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作为魏国的三晋伙伴、战国中后期的难兄难弟,韩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韩氏从山西平阳起家,三家分晋后把势力扩张到黄河以南,灭亡郑国后又将国都迁至新郑,统治中心由此南移。据《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在战国中期的国土“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大体包括今山西南部的一部分,以国都新郑为中心的豫东平原一带。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作为魏、韩统治核心区域的大梁、新郑都无可争议地位于当时天下的中心。众所周知,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把当时的天下分为山东、山西两部分,连通两大地理单元主要是靠两条交通要道:
第一条是黄河南岸的豫西通道,也就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水南岸东行,过华阴,入桃林、崤函之塞,过陕、焦、曲沃等城邑,经洛阳、成皋、荥阳至管城(今河南郑州),到达豫东平原。
第二条是黄河北岸的晋南-豫北通道,也就是由渭水北岸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翻越王屋山,从轵(今河南济源西北)穿过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进入冀南平原。
两条通道沿途的主要城邑,基本被魏、韩两国所分别掌握,甚至连南北向的要道也是如此。想要从燕赵之地南下入楚,最便利的路线是先到达魏国的邺、朝歌,渡过黄河后,经韩国的管城、新郑,再抵达楚国的方城。此外,魏惠王还修建了鸿沟,以沟通整个中原的水系。
正是因此,魏、韩两国一直享有“天下之枢”“天下之胸腹”的称号,同样是张仪在《战国策》中的描述:“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此后,张仪对魏国的命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几乎是对由盛转衰的魏惠王时代的总结: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会盟并不顺利,先是齐威王看不起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不屑与它并列为王,还断绝了与中山国的外交关系;此后赵国又主动放弃称王,国君给出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他便是后人熟悉的赵武灵王,不过这个称呼其实是追封的谥号。再后来,原本的盟友楚国又插手魏国立太子一事,翻脸攻打起魏国。总之,最后是魏、韩、燕、赵、中山五国参与了相王,这次会盟也被称为“五国相王”。随着这次会盟,一个新时代——合纵连横的时代到来了。
连遭惨败后,魏国很快因自己的地理位置四面受敌,魏惠王再也无力像从前那样肆意出击,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仔细揣摩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以便结交和依托其他强国,谋求生存发展。早在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就变服折节,拉上韩国一同在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侯因齐、尊他为王,这就是“徐州相王”,显然是五国相王的预演。之后的许多年里,魏国以及和它位置、地位皆相仿的韩、周,更是以出产纵横家而闻名,张仪、公孙衍、苏秦三兄弟,范雎、姚贾,无不出自这一地区,太史公因此有了“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的论断。
第一波合纵与连横的对抗主要发生在秦、魏这对老冤家之间,两位主角是公孙衍(又名犀首)、张仪,《史记·苏秦列传》把公孙衍误记为苏秦。他们都是魏人,也都先后在秦、魏两国为官;无论在哪里,两人只要一碰面就少不了明争暗斗,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就好像DNA的双螺旋,始终在交错缠绕,直到把整个天下都拖入战局。
起初是公孙衍来到秦国担任大良造,率领秦军攻打母国魏国,夺取阴晋。很快张仪入秦,排挤公孙衍,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没计较他领兵攻魏的事,依旧重用了他。在公孙衍的促使下,魏国与齐、楚初步结成合纵同盟,之后就是“五国相王”。
“五国相王”谈不上成功,但已经给秦国敲响了警钟。次年(前322),秦国一边攻取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一边派张仪出使魏国,张仪又一次排挤走了公孙衍,第二年(前321)还同时在秦、魏两国为相。不过很快他也受了挫,前320年,秦国假道魏、韩进攻齐国,却被齐将匡章击败,魏惠王马上变了脸,又把张仪赶回秦国,重新任命公孙衍为魏相,回到合纵的老路上。
公元前319年,公孙衍在列国之间奔走游说,终于说服各国国君,组织起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合纵,楚、魏、赵、韩、燕五国都加入进来,公孙衍甚至还说动义渠国从后方进攻秦国。这便是人们熟悉的“六国合纵”的历史原型,其实整个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从没有在同一次合纵中共同出现过,总是会少一两个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合纵,魏惠王都应该是盟主的不二之选,不幸的是,他刚好在这一年去世,剩下四国的国君当中,以楚怀王威望最高,于是由他担任盟主,称为“纵约长”。在他的统领下,声势浩大的联军进逼秦国东大门函谷关;同时,义渠国也在秦国后方蠢蠢欲动。
这一战的结果大大出乎六国所料,也使他们第一次对天险函谷关的地形有了深刻体验。“函谷”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外形——一条藏在连绵山地中的狭长山谷,号称两辆车无法并行,就像漫漫峡谷中抽出一支狭长的木函。联军难以在此施展兵力,结果秦军刚一出击,他们就向东败退。次年,秦军又乘胜追击,名将樗里疾一直反击到韩国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俘虏韩将申差,击败赵国的公子渴、韩国的太子奂,一口气斩首了8.2万人。第一次合纵攻秦就这样失败了。
公孙衍剩余的纵横家生涯依旧在失败中度过。为维持魏、韩、齐之间的联合,他推荐齐国孟尝君担任魏相,自己则前往韩国任相,但秦国通过公元前315、314年的浊泽、岸门两战接连大败韩国,公孙衍只得临阵脱逃,这在《秦本纪》 《魏世家》中都有记载:“其将犀首走”“走犀首岸门”。此后魏、韩两国面对秦国的强大军力,不得不再次回到连横的老路上。
不过作为合纵路线的代表人物,公孙衍依旧得到许多人的推崇,《孟子》记载了景春的评价,尽管孟子本人并不认可:“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这是魏国的第一次合纵,几乎也是它最后一次在战国时代担纲主角。此后魏国便和韩国一样,或是沦为白起等秦国名将的经验包,或是成为秦、齐、楚等大国轮流争夺的对象。
在战国中期后的一连串战争中,齐、楚、秦等国谁能联合并控制魏、韩,谁就更容易取得胜利:
公元前313年,秦国联合魏、韩,与齐、楚、宋作战;秦国利用魏国抵挡齐、宋的攻势,并反击到濮水。韩国则助秦国攻楚。有了它们的牵制,秦得以在丹阳之战大败楚军。次年,秦楚又在蓝田交战,魏、韩袭击楚国后方,迫使楚国撤兵。
公元前303-前299年,齐国联合魏、韩攻楚,在垂沙之役中大胜楚军,杀其将唐蔑,攻占楚国宛、叶以北的大片领土。
公元前298-前296年,齐国联合魏、韩大举攻秦,甚至攻破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归还前所侵占的韩魏之河外、封陵、武遂等地。
公元前288-前287年,齐国主持五国伐秦,秦不敢应战,退地以求和,齐国趁机灭宋。
公元前285-前284年,秦国联合魏、韩,出兵攻占齐国九城,更操纵五国联军伐齐,几乎灭亡齐国,使之彻底退出争霸的行列。
除直接进行武力征服,秦、齐、楚还利用各种外交手段操纵魏、韩两国。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置相,也就是派遣本国的重臣到魏、韩出任相邦、丞相,以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如前所述,张仪就曾同时在秦、魏担任丞相,樗里疾代表秦国、公孙衍代表魏国、昭献代表楚国,都曾经相韩;到了战国后期,苏秦也在燕、齐先后任相。更著名的是孟尝君,他之前在齐国任相,秦国为拉拢齐国,于公元前299年邀请他赴秦任相,于是有了狡兔三窟、鸡鸣狗盗等故事。一年后他从秦国逃走,又在魏国任相,并组织合纵联军掉头攻破秦国的函谷关。
这种“相”到底是什么性质,学者们争论不休,因为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外邦人“空降”到某国后,就能立刻对该国进行有效治理,也很难想象他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同时治理两个以上的国家,甚至不排除泄露该国核心机密的可能。因此有学者推测,这类“相”应该近似客卿或外交官,不涉及内政,只涉及外交,也并不能完全决定所在国的外交策略。张仪相魏之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可见魏王并没有视他为心腹大臣,《战国策·魏策一》更明确指出魏惠王此举的目的:“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
迫使魏韩派遣质子、扶植某位公子为储也是常见的手段。魏惠王在马陵之战失败、失去太子申之后,被迫把新太子鸣(推测为太子嗣)派到齐国为质,楚国则企图扶植公子高为魏太子,以便和齐国争夺魏国。韩国也曾把太子仓派到秦国、公子虮虱派到楚国当人质,等到原本的太子婴去世,在楚国为质的公子虮虱又和公子咎争夺太子之位,楚国立即支持起公子虮虱,为的自然是虮虱即位后,自己能从韩国得到好处。
当然,秦、齐、楚等国也经常以实际利益为饵,拉拢魏、韩追随自己出战,许诺在胜利后一同瓜分土地,有时甚至会主动把占领的城邑土地归还对方。秦国是这方面的高手,公元前329年,秦国攻占魏国的汾阴、皮氏、曲沃和焦,后来又把曲沃与焦归还了魏国。公元前328年,公子华、张仪逼降魏国蒲阳,张仪随后通过游说,迫使魏惠王与秦修好,并向魏国归还了上郡、少梁。公元前308年,秦国攻克韩国的重镇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为防止韩国倒向齐、楚,把武遂退给韩国,三年后重新夺了回来。
不过,同样是争夺魏、韩,齐楚两国远没有秦国那样热心。
魏国衰落之后,齐国看起来是最适合继承霸主之位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国势蒸蒸日上,齐湣王前期更是达到顶峰,齐国对秦国组织过两次成功的合纵,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次是孟尝君统领齐、魏、韩联军,一度攻破秦国的函谷关;另一次是联合赵、魏、韩、楚再次逼近函谷关,秦国慑于兵锋,主动求和。
但这两次合纵并没给齐国带来多少好处,对秦国的打击也十分有限。齐国的地理位置就已决定,它对抗秦不会有多少热情。六国之中,齐国居于最东,距离秦国最远,不必像魏、韩那样终日担忧秦军的威胁;反过来,齐国即便攻占了秦国的土地城邑也无法守住,徒然为魏、韩作嫁衣。更有甚者,如果把秦国削弱太多,倒容易让魏、韩这两个近邻强大起来,那样反而对自己构成威胁。齐国真正在意的是淮北、泗上流域的土地,尤其是富庶的宋国,五国联军进逼函谷关的那次合纵,齐湣王正是企图让其他四国拖住秦国,自己趁机灭宋。
楚国也打着和齐国一样的算盘。春秋战国之交,楚国相继夺取江淮间的大片领土,战国前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泗水流域,这不可避免地与齐国产生利益冲突。
站在齐、楚当时的立场,争夺淮泗流域显得顺理成章,这一带小国林立又繁华富庶,既容易攻占又能获得巨大利益。但如果从天下局势着眼,淮泗流域对于争霸乃至统一,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当年魏惠王召集十二诸侯举行逢泽之会,商鞅就告诉他:如今大王召集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小国,它们固然可以供魏国驱使,魏国却不足以凭这些小国而称王于天下。
然而齐、楚两国终究还是没能忍住贪婪,尤其是齐湣王。他一意孤行,连续三次攻宋,最终独吞了整个宋国,付出的代价却是几乎得罪所有大国,引来乐毅统领的五国伐齐,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帝”只经历两次败战就滑落到灭国的边缘,齐湣王仓皇出逃,也死于非命。
楚国争霸的希望更加渺茫。因为缺乏魏、秦那样深入彻底的变法,进入战国时代,它逐渐失去春秋时那种强悍凶蛮的进取精神,变得暮气沉沉,在中原面对魏韩、在商洛面对秦国,基本都采取守势。更重要的是,楚国对纵横局势的误判同样严重,首先就是低估了秦国的威胁。楚怀王心目中的秦国,应该还是那个从春秋时代就保持着良好互动的邻邦,因此未对张仪的欺诈多加提防,直到张仪自食其言,楚怀王才恼羞成怒,两次出师伐秦,结果接连遭遇惨败。
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之处是,楚国同样忽视了韩国。韩国虽弱,但毗邻楚国的北部门户——方城隘口。秦楚蓝田之战、齐楚垂沙之战,魏、韩都是助秦、齐进攻宛、邓地区,导致楚国左支右绌而落败。如张仪所言:“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此后又有楚怀王被秦扣留、水灌鄢城、火烧夷陵等一系列堪称国耻的事件,楚国从此彻底衰败下去。
相比齐、楚的摇摆不定,秦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清晰,就是要踏入中原、向全天下伸展扩张,这几乎是从秦穆公时代就确立的国策。只是那时,秦国被强大的晋国死死堵在关中,三家分晋后,继承晋国的魏国更是把处于低谷的秦国挤压到华山以西。通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后,秦国先是逐步收复河西,又开始全力打通东出之路,而主要作战目标正是魏、韩,如《战国策·魏策三》所言:“夫秦强国也,而魏、韩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
公元前324年,张仪领兵攻陷魏国的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公元前314年,重新占领焦、曲沃。这几座城邑都位于函谷关外,秦国从此将触角伸向中原,主攻目标也由魏国转为韩国。公元前308年的宜阳之战在《史记》《战国策》中只留下只言片语,但对秦国的东出战略至关重要。历经整整五个月的激战,秦国终于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从韩国手中夺过这座重镇,完全掌握了豫西通道的西段。公元前294年,秦国更是在伊阙大败魏、韩联军,斩首24万,战神白起一战成名。从那以后,魏、韩的命运再无悬念,《魏世家》《韩世家》唯一值得记录的内容,几乎只剩“某某年,秦国攻占我某某城,斩首某某万”而已。
公元前257年,信陵君盗取虎符、暗杀晋鄙,统领魏军北上,解救了被围困近三年的赵国,也为奄奄一息的山东六国续了一口气;10年后(前247年),他又率领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国,这成为六国合纵的回光返照。很快,信陵君就因秦国的反间计而被魏安釐王解除兵权,自己也郁郁而终。公元前241年,五国在赵将庞煖的率领下最后一次伐秦,仍然草草收场,最终逐一亡于秦国。
回首这100年,始终在合纵连横中保持着清晰目标和灵活手腕,是秦国成为最后赢家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齐、楚的短视还是魏、韩的摇摆,也都决定了它们的失败。
“称王”是战国中期兴起的风潮。此前各诸侯的称号都是某某公、某某侯,天下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王只有周天子,楚、吴、越等国尽管早就自行称王,但中原诸侯一直视他们为蛮夷,不肯承认这些王号。如今,随着各国实力的膨胀,诸侯们终于按捺不住同样的野心,纷纷迈出僭越的最后一步,周天子由此失去最后一丝颜面。
公元前344年,最强大的魏国率先称王,国君魏侯罃正是魏惠王。此后20年里,齐、秦、韩几国也相继称王,首任称王的国君分别被称为齐威王、秦惠文王、韩宣惠王,眼下这次相王则是为了承认天下最后几个大国燕、赵、中山的王号。
作为会盟的发起者,魏惠王很难不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逢泽之会,当年他打着朝觐天子的名义召集天下十二诸侯,却又依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涂红梁柱,立起天子才能用的九斿七星之旟,还乘坐夏车、自称夏王,连名号都与天子平级,那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光辉伴随着阴影,魏国在逢泽之会十年前就已显露出颓势。公元前354年,魏国在桂陵之战中首败于齐国;同年,通过商鞅变法走上强国之路的秦国也在元里大败魏军,并夺取河西地区的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两年后(前352),秦军又在大良造商鞅的率领下攻入魏国河东,一度夺取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次年又围攻固阳,迫使其归降。
逢泽之会后,更多的败战接踵而至。公元前342年,魏国在马陵之战再次被齐国重创,“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公元前341年,齐将田盼包围魏国的平阳(今河南滑县南)。公元前340年,商鞅再度领军攻魏,用诈谋俘虏了魏将公子卬、乘势击败魏军。公元前338年,秦军又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市西)击败魏军,虏获魏军主将魏错……
公元前369年凭运气登上君位时,魏惠王从祖父文侯、父亲武侯手中继承的是一个独霸天下的强大魏国,半个世纪过去,却成功地凭实力葬送了这份霸业。他晚年向孟子回顾这一连串失败时叹:“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既源于魏惠王本人的各种决策失误,也与魏国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诸侯会盟像”雕塑,位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
天下之胸腹
作为魏国的三晋伙伴、战国中后期的难兄难弟,韩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韩氏从山西平阳起家,三家分晋后把势力扩张到黄河以南,灭亡郑国后又将国都迁至新郑,统治中心由此南移。据《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在战国中期的国土“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大体包括今山西南部的一部分,以国都新郑为中心的豫东平原一带。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作为魏、韩统治核心区域的大梁、新郑都无可争议地位于当时天下的中心。众所周知,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把当时的天下分为山东、山西两部分,连通两大地理单元主要是靠两条交通要道:
第一条是黄河南岸的豫西通道,也就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水南岸东行,过华阴,入桃林、崤函之塞,过陕、焦、曲沃等城邑,经洛阳、成皋、荥阳至管城(今河南郑州),到达豫东平原。
第二条是黄河北岸的晋南-豫北通道,也就是由渭水北岸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翻越王屋山,从轵(今河南济源西北)穿过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进入冀南平原。
两条通道沿途的主要城邑,基本被魏、韩两国所分别掌握,甚至连南北向的要道也是如此。想要从燕赵之地南下入楚,最便利的路线是先到达魏国的邺、朝歌,渡过黄河后,经韩国的管城、新郑,再抵达楚国的方城。此外,魏惠王还修建了鸿沟,以沟通整个中原的水系。
正是因此,魏、韩两国一直享有“天下之枢”“天下之胸腹”的称号,同样是张仪在《战国策》中的描述:“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此后,张仪对魏国的命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几乎是对由盛转衰的魏惠王时代的总结: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战国时期列国货币,现藏河南博物院
失败的合纵
会盟并不顺利,先是齐威王看不起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不屑与它并列为王,还断绝了与中山国的外交关系;此后赵国又主动放弃称王,国君给出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他便是后人熟悉的赵武灵王,不过这个称呼其实是追封的谥号。再后来,原本的盟友楚国又插手魏国立太子一事,翻脸攻打起魏国。总之,最后是魏、韩、燕、赵、中山五国参与了相王,这次会盟也被称为“五国相王”。随着这次会盟,一个新时代——合纵连横的时代到来了。
连遭惨败后,魏国很快因自己的地理位置四面受敌,魏惠王再也无力像从前那样肆意出击,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仔细揣摩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以便结交和依托其他强国,谋求生存发展。早在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就变服折节,拉上韩国一同在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侯因齐、尊他为王,这就是“徐州相王”,显然是五国相王的预演。之后的许多年里,魏国以及和它位置、地位皆相仿的韩、周,更是以出产纵横家而闻名,张仪、公孙衍、苏秦三兄弟,范雎、姚贾,无不出自这一地区,太史公因此有了“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的论断。
第一波合纵与连横的对抗主要发生在秦、魏这对老冤家之间,两位主角是公孙衍(又名犀首)、张仪,《史记·苏秦列传》把公孙衍误记为苏秦。他们都是魏人,也都先后在秦、魏两国为官;无论在哪里,两人只要一碰面就少不了明争暗斗,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就好像DNA的双螺旋,始终在交错缠绕,直到把整个天下都拖入战局。
起初是公孙衍来到秦国担任大良造,率领秦军攻打母国魏国,夺取阴晋。很快张仪入秦,排挤公孙衍,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没计较他领兵攻魏的事,依旧重用了他。在公孙衍的促使下,魏国与齐、楚初步结成合纵同盟,之后就是“五国相王”。
“五国相王”谈不上成功,但已经给秦国敲响了警钟。次年(前322),秦国一边攻取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一边派张仪出使魏国,张仪又一次排挤走了公孙衍,第二年(前321)还同时在秦、魏两国为相。不过很快他也受了挫,前320年,秦国假道魏、韩进攻齐国,却被齐将匡章击败,魏惠王马上变了脸,又把张仪赶回秦国,重新任命公孙衍为魏相,回到合纵的老路上。
公元前319年,公孙衍在列国之间奔走游说,终于说服各国国君,组织起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合纵,楚、魏、赵、韩、燕五国都加入进来,公孙衍甚至还说动义渠国从后方进攻秦国。这便是人们熟悉的“六国合纵”的历史原型,其实整个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从没有在同一次合纵中共同出现过,总是会少一两个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合纵,魏惠王都应该是盟主的不二之选,不幸的是,他刚好在这一年去世,剩下四国的国君当中,以楚怀王威望最高,于是由他担任盟主,称为“纵约长”。在他的统领下,声势浩大的联军进逼秦国东大门函谷关;同时,义渠国也在秦国后方蠢蠢欲动。
河南三门峡市函谷关景区,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
这一战的结果大大出乎六国所料,也使他们第一次对天险函谷关的地形有了深刻体验。“函谷”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外形——一条藏在连绵山地中的狭长山谷,号称两辆车无法并行,就像漫漫峡谷中抽出一支狭长的木函。联军难以在此施展兵力,结果秦军刚一出击,他们就向东败退。次年,秦军又乘胜追击,名将樗里疾一直反击到韩国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俘虏韩将申差,击败赵国的公子渴、韩国的太子奂,一口气斩首了8.2万人。第一次合纵攻秦就这样失败了。
公孙衍剩余的纵横家生涯依旧在失败中度过。为维持魏、韩、齐之间的联合,他推荐齐国孟尝君担任魏相,自己则前往韩国任相,但秦国通过公元前315、314年的浊泽、岸门两战接连大败韩国,公孙衍只得临阵脱逃,这在《秦本纪》 《魏世家》中都有记载:“其将犀首走”“走犀首岸门”。此后魏、韩两国面对秦国的强大军力,不得不再次回到连横的老路上。
不过作为合纵路线的代表人物,公孙衍依旧得到许多人的推崇,《孟子》记载了景春的评价,尽管孟子本人并不认可:“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如何控制韩魏?
这是魏国的第一次合纵,几乎也是它最后一次在战国时代担纲主角。此后魏国便和韩国一样,或是沦为白起等秦国名将的经验包,或是成为秦、齐、楚等大国轮流争夺的对象。
在战国中期后的一连串战争中,齐、楚、秦等国谁能联合并控制魏、韩,谁就更容易取得胜利:
公元前313年,秦国联合魏、韩,与齐、楚、宋作战;秦国利用魏国抵挡齐、宋的攻势,并反击到濮水。韩国则助秦国攻楚。有了它们的牵制,秦得以在丹阳之战大败楚军。次年,秦楚又在蓝田交战,魏、韩袭击楚国后方,迫使楚国撤兵。
公元前303-前299年,齐国联合魏、韩攻楚,在垂沙之役中大胜楚军,杀其将唐蔑,攻占楚国宛、叶以北的大片领土。
公元前298-前296年,齐国联合魏、韩大举攻秦,甚至攻破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归还前所侵占的韩魏之河外、封陵、武遂等地。
公元前288-前287年,齐国主持五国伐秦,秦不敢应战,退地以求和,齐国趁机灭宋。
公元前285-前284年,秦国联合魏、韩,出兵攻占齐国九城,更操纵五国联军伐齐,几乎灭亡齐国,使之彻底退出争霸的行列。
除直接进行武力征服,秦、齐、楚还利用各种外交手段操纵魏、韩两国。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置相,也就是派遣本国的重臣到魏、韩出任相邦、丞相,以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如前所述,张仪就曾同时在秦、魏担任丞相,樗里疾代表秦国、公孙衍代表魏国、昭献代表楚国,都曾经相韩;到了战国后期,苏秦也在燕、齐先后任相。更著名的是孟尝君,他之前在齐国任相,秦国为拉拢齐国,于公元前299年邀请他赴秦任相,于是有了狡兔三窟、鸡鸣狗盗等故事。一年后他从秦国逃走,又在魏国任相,并组织合纵联军掉头攻破秦国的函谷关。
这种“相”到底是什么性质,学者们争论不休,因为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外邦人“空降”到某国后,就能立刻对该国进行有效治理,也很难想象他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同时治理两个以上的国家,甚至不排除泄露该国核心机密的可能。因此有学者推测,这类“相”应该近似客卿或外交官,不涉及内政,只涉及外交,也并不能完全决定所在国的外交策略。张仪相魏之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可见魏王并没有视他为心腹大臣,《战国策·魏策一》更明确指出魏惠王此举的目的:“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
迫使魏韩派遣质子、扶植某位公子为储也是常见的手段。魏惠王在马陵之战失败、失去太子申之后,被迫把新太子鸣(推测为太子嗣)派到齐国为质,楚国则企图扶植公子高为魏太子,以便和齐国争夺魏国。韩国也曾把太子仓派到秦国、公子虮虱派到楚国当人质,等到原本的太子婴去世,在楚国为质的公子虮虱又和公子咎争夺太子之位,楚国立即支持起公子虮虱,为的自然是虮虱即位后,自己能从韩国得到好处。
当然,秦、齐、楚等国也经常以实际利益为饵,拉拢魏、韩追随自己出战,许诺在胜利后一同瓜分土地,有时甚至会主动把占领的城邑土地归还对方。秦国是这方面的高手,公元前329年,秦国攻占魏国的汾阴、皮氏、曲沃和焦,后来又把曲沃与焦归还了魏国。公元前328年,公子华、张仪逼降魏国蒲阳,张仪随后通过游说,迫使魏惠王与秦修好,并向魏国归还了上郡、少梁。公元前308年,秦国攻克韩国的重镇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为防止韩国倒向齐、楚,把武遂退给韩国,三年后重新夺了回来。
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以及青铜胄,现藏河南博物院
秦国东出的主要作战目标
不过,同样是争夺魏、韩,齐楚两国远没有秦国那样热心。
魏国衰落之后,齐国看起来是最适合继承霸主之位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国势蒸蒸日上,齐湣王前期更是达到顶峰,齐国对秦国组织过两次成功的合纵,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次是孟尝君统领齐、魏、韩联军,一度攻破秦国的函谷关;另一次是联合赵、魏、韩、楚再次逼近函谷关,秦国慑于兵锋,主动求和。
但这两次合纵并没给齐国带来多少好处,对秦国的打击也十分有限。齐国的地理位置就已决定,它对抗秦不会有多少热情。六国之中,齐国居于最东,距离秦国最远,不必像魏、韩那样终日担忧秦军的威胁;反过来,齐国即便攻占了秦国的土地城邑也无法守住,徒然为魏、韩作嫁衣。更有甚者,如果把秦国削弱太多,倒容易让魏、韩这两个近邻强大起来,那样反而对自己构成威胁。齐国真正在意的是淮北、泗上流域的土地,尤其是富庶的宋国,五国联军进逼函谷关的那次合纵,齐湣王正是企图让其他四国拖住秦国,自己趁机灭宋。
楚国也打着和齐国一样的算盘。春秋战国之交,楚国相继夺取江淮间的大片领土,战国前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泗水流域,这不可避免地与齐国产生利益冲突。
站在齐、楚当时的立场,争夺淮泗流域显得顺理成章,这一带小国林立又繁华富庶,既容易攻占又能获得巨大利益。但如果从天下局势着眼,淮泗流域对于争霸乃至统一,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当年魏惠王召集十二诸侯举行逢泽之会,商鞅就告诉他:如今大王召集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小国,它们固然可以供魏国驱使,魏国却不足以凭这些小国而称王于天下。
然而齐、楚两国终究还是没能忍住贪婪,尤其是齐湣王。他一意孤行,连续三次攻宋,最终独吞了整个宋国,付出的代价却是几乎得罪所有大国,引来乐毅统领的五国伐齐,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帝”只经历两次败战就滑落到灭国的边缘,齐湣王仓皇出逃,也死于非命。
楚国争霸的希望更加渺茫。因为缺乏魏、秦那样深入彻底的变法,进入战国时代,它逐渐失去春秋时那种强悍凶蛮的进取精神,变得暮气沉沉,在中原面对魏韩、在商洛面对秦国,基本都采取守势。更重要的是,楚国对纵横局势的误判同样严重,首先就是低估了秦国的威胁。楚怀王心目中的秦国,应该还是那个从春秋时代就保持着良好互动的邻邦,因此未对张仪的欺诈多加提防,直到张仪自食其言,楚怀王才恼羞成怒,两次出师伐秦,结果接连遭遇惨败。
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之处是,楚国同样忽视了韩国。韩国虽弱,但毗邻楚国的北部门户——方城隘口。秦楚蓝田之战、齐楚垂沙之战,魏、韩都是助秦、齐进攻宛、邓地区,导致楚国左支右绌而落败。如张仪所言:“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此后又有楚怀王被秦扣留、水灌鄢城、火烧夷陵等一系列堪称国耻的事件,楚国从此彻底衰败下去。
相比齐、楚的摇摆不定,秦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清晰,就是要踏入中原、向全天下伸展扩张,这几乎是从秦穆公时代就确立的国策。只是那时,秦国被强大的晋国死死堵在关中,三家分晋后,继承晋国的魏国更是把处于低谷的秦国挤压到华山以西。通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后,秦国先是逐步收复河西,又开始全力打通东出之路,而主要作战目标正是魏、韩,如《战国策·魏策三》所言:“夫秦强国也,而魏、韩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
战国跽坐人漆绘铜灯,战国,1975 年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地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公元前324年,张仪领兵攻陷魏国的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公元前314年,重新占领焦、曲沃。这几座城邑都位于函谷关外,秦国从此将触角伸向中原,主攻目标也由魏国转为韩国。公元前308年的宜阳之战在《史记》《战国策》中只留下只言片语,但对秦国的东出战略至关重要。历经整整五个月的激战,秦国终于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从韩国手中夺过这座重镇,完全掌握了豫西通道的西段。公元前294年,秦国更是在伊阙大败魏、韩联军,斩首24万,战神白起一战成名。从那以后,魏、韩的命运再无悬念,《魏世家》《韩世家》唯一值得记录的内容,几乎只剩“某某年,秦国攻占我某某城,斩首某某万”而已。
公元前257年,信陵君盗取虎符、暗杀晋鄙,统领魏军北上,解救了被围困近三年的赵国,也为奄奄一息的山东六国续了一口气;10年后(前247年),他又率领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国,这成为六国合纵的回光返照。很快,信陵君就因秦国的反间计而被魏安釐王解除兵权,自己也郁郁而终。公元前241年,五国在赵将庞煖的率领下最后一次伐秦,仍然草草收场,最终逐一亡于秦国。
回首这100年,始终在合纵连横中保持着清晰目标和灵活手腕,是秦国成为最后赢家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齐、楚的短视还是魏、韩的摇摆,也都决定了它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