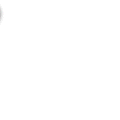一 白朗起义:背景
进入20世纪,时值清末民初,中华大地,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特别是本就不富裕的中原地区,更是雪上加霜,《河南省志·经济卷》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豫中田赋每顷征银增至四两八钱,较光绪初年增两倍有余。农民终岁劳苦,所得不足完粮纳税。"(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87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民国建立,但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乱政,广大人民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河南宝丰县,1912年《河南官报》披露:"每石小麦市价三元,而官定折色竟作价五元,浮收之数倍于正供。"(《河南官报》1912年第14期)时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在致袁世凯的密电中承认:"豫省连年歉收,今岁尤甚。饥民载道,流离满目,各属呈报灾情之文日必数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档号1011-236)1913年夏,豫西暴雨成灾,《申报》记者实地采访记载:"汝河暴涨,两岸田庐尽成泽国。灾民采树皮充饥,有鬻妻女于市者,价不过铜元百枚。"(《申报》1913年7月23)。
在这样的情况下,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仅不想办法改善民生,反而变本加厉,压榨百姓。起义亲历者王凌霄在《白狼祸豫记》中回忆:"新官到任,首事钱粮。县知事月俸二百元,而到任三月即置田百亩,其来路不问可知。"(王凌霄,1915年,第12页)1913年《时报》揭露:"豫省各县警备队,名为维持治安,实则白昼劫掠。鲁山某乡一日被劫七次,报官竟遭鞭笞。"(《时报》1913年4月17日),河南人民反抗的怒火不断燃烧,英国驻汉口领事艾斯顿在1913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河南境内约有三十股土匪活动,最大者不过百人。但自白朗出现后,这些分散的力量正在快速集结。"(FO228/2458,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路起义军或土匪开始集结在一起,白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白朗,又名白狼,是此次起义的领袖,关于其生平与早年经历,模糊不详,1915年吕咎予在《狼 祸述闻》中说道:“白朗人格及历史,道听途说,纷传不一:或谓白狼姓白,名 朗斋,河南汝阳人;或谓白姓,永丞其名;或谓姓冯;或谓姓李;或谓姓萧;或 谓曾在郑州为小官;或谓为故六镇吴禄贞部下;或谓在在谢宝胜总戎前充戈什(哈)。”据大公报记载“白狼名朗,河 南宝丰县人也,夙系寒族,其父以六博营业,守祖遗产百余亩,及狼生时,家资 荡尽矣。欲耕无产,欲贾无财,游手好闲,从未入塾读书,目不识丁,殆下流社 会人物也。”“有中人户,轻侠滥交,盖徐海石达开流也””《甘宁青史略》中说“白匪者,河南宝丰人,名阆斋,盖陆军学生,多以字 行之”《白狼猖獗记》中说“白狼者,回人也。原名朗,世人化传以为白狼。关于其生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白朗出身不高,早年混迹草莽,行走江湖,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喜欢结交豪杰,号召力强,有一定军旅或当差经验,约光绪初年生人,这些是可以确定的。
据《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白朗遭同村王姓地主陷害,被捕入狱,几乎散尽家产,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常有“愤愤不平之志”,宣统二年(1910),绿林大盛,抢劫肆虐。白朗的母亲为避免家中财务被抢, 将家中财物打点后托人送往城中女儿家中。然而途中遭遇官府清乡军队,财物被 抢,送财物的两人被视为土匪装在站箱里囚死。随后白朗的姐姐家也因白朗“土 匪嫌疑犯”的身份被怀疑与土匪勾通而遭到抄家。至此,朗已无路可退,忍无可忍,干脆扯旗造反,终于 正式投入到了蹚将(土匪)的行列,并很快拉起了一支以自己为首的杆子(匪棒),许多江湖豪杰前来响应,队伍扩充到数十人。
二 白朗起义:早期
白朗起义的早期力量比较有限,跟小股土匪没什么差异。至宣统三年十二月,通过与附近杆子合并,才扩充到百余人左右。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率领队伍进攻鲁山县张官营。遭到寨内武装和官军的内外夹攻,损失惨 重。被打死及掩死的杆众达80余人,剩余十几人得以突围,白朗本 人受伤,几乎被擒。但随着饥荒加剧,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和流民走投无路,纷纷加入白朗队伍。据《宝丰县志》载:"民国元年三月,白朗聚众二十八人于姚店铺,劫富户张氏,得熗五支,银元三百。"(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年,第456页)民国元年(1912年)4月,白朗悍然绑架归乡途中的前宝丰县知事张礼堂,勒索财物,得快熗30支,财货不计其数,声名大震,队伍扩充至数百人,甚至敢于攻打县城,1912年秋,白郎攻克禹州,《禹县志》记载:"九月十五夜,白朗率众八百破西门而入,开仓放粮三日,携快熗二百余支而去。"(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36年,卷九)
1912年3月,张镇芳被袁世凯任为河南都督,开始“剿匪”,初战不利,同年秋,遂派陆军第六师师长 李纯带大兵进剿,北洋军诱杀白朗的盟友——杆子首领杜启斌,击溃宝丰,鲁山的各大杆子,大兵压境,白朗孤立无援,被迫转移,据报纸记载,白朗离开宝丰后南下“窜莲阪、尚店、王店等寨, 遂入泌阳境,与本地土匪刘老扒等合捻,直搞春水”在转移过程中,不断遭到官军攻击,仅剩27人,11月,白朗率残部撤退至人迹罕至,易守难攻的舞阳县境内母猪峡一带,进行修整。在此期间,白 朗“深沟高垒,作久居计”,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发展,至第二年春,与周围杆子合并,队伍又扩充至数百人。
4月19日经充分修整后的白朗,率部南下湖北随州劫掠田王寨,收获 颇丰,据当时报纸报道,闻“随匪等自劫杀八大团和戴寡妇、陈、台等三家后, 粮饱丰足,可以支持年余,土炮铳药更灵,机关熗共有七架,快熗一千余支,鸟铳杆刀不计其数”借助如此充足的给养,白朗击败了闻讯前来进剿的湖北第59团,并“得快熗一百余支,势力尤为猖獗”,实力大振的白朗部兵进湖北天 河口,试图攻占该城,后为避开湖北第三师王安澜部的进剿北上返豫。至此,开始了起义的高潮阶段。1913年5月31日,白朗攻占唐县,并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使队伍 再度扩大,此时“白狼一股已达二三千人”
三 白朗起义:高潮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白朗开始与革命党接触。并开始使用“革命党”和“黄兴北伐队”的旗号,至此,白朗由土匪匪帮转变为起义军。据当时报载,白朗于6月15日“直扑禹州,由奸人 启门迎入”。白朗占领禹州之后旋即退出,于“七月一日复破淅西坪,二日又“破荆紫”,接着进入湖北郧阳境内。面对前来围剿的各路北洋军,白朗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不与官军正面作战,反而绕道直取北洋军兵力薄弱的随州,枣阳一带,9月25日,白朗军攻破枣阳,大掠而还。《汉口新闻报》报道:"匪众约二万人,持快熗者过半,余执土炮刀矛。破城后焚烧县署,释放囚犯,开仓济贫。"(《汉口新闻报》1913年9月27日)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在报告中称:"白朗军装备德制毛瑟熗约三千支,日制三十年式步熗千余支,甚至拥有马克沁机熗两挺。"(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50344800)已成一支不容小觑的起义军。不久白朗由枣阳退出,转而 北上进攻新野、邓县,并分兵袭取唐县、桐柏、方城、卢氏、镇平。10月,陕西陆军团长王生歧率部参加起义军。入冬,起义军发展到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凯急忙调集三万人马进行“围剿”。起义军避实击虚,突围东进。1913年11月10日,白朗趁豫南重镇南阳城内仅有一个新兵旅驻守,兵力 空虚之际,率兵攻占南阳,并于中旬分路进攻信阳,威胁京汉铁路。袁世凯立即 命令黎元洪派遣军队镇压,白朗军与王占元师接战数次,于11月17日分两路从 信阳撤出,移至泌阳等地。据当时 报纸记载:“白匪蔓延益甚,陷南阳,攻信阳,守宝丰,叛军帮匪群起响应,汴鄂官军望风逃渍,有窜扰长江之势。”,1913年底,1914年初,起义军由转战豫东南,至潢川,光山一带,逼近袁世凯老家——项城。白朗军拟袭取项城, 揭毁袁世凯老家,当时,民间盛传起义军要挖袁世凯的祖坟,破其风水,袁世凯与张镇芳大为惶恐,调集重兵防御项城。鉴于此,白朗军旋即“由潢川分股南窜,至双树,各股 扑商城”白朗军从商城撤出,北上攻取息县、罗县。此时白朗军 兵锋正盛,无人可挡。据《申报》记载:“信阳来军,畏匪不敢前进,……最为 可异者,吾辈见许堵张镇芳,当日从信阳乘火车经过确山,车内装有护卫马、兵、 炮兵甚多,径行往北而去”此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白朗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袁世凯大怒,下令调集众军围剿,白朗见河南北洋军云集,开始转战安徽。
1月24日,白朗军击败守军王传禄营攻陷六安,县知事殷谋森逃跑。白朗与清末的许多底层民众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与洋人, 占据六安时,白朗军“致教堂焚毁,教士狀一人,掳二人”并开仓济贫,饥 民纷纷加入队伍,次日朗军“山六安窜扰霍邱附近,声势颇大”。政府军队 久久不能将白朗剿平,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据当时报纸报道:“白狼一土匪耳,豫督派兵剿之,中央派兵剿之,劳师糜饱,数月于兹,而白狼之势,反 愈猖獗,癣济之疾竟成心腹之患”,北洋政府颜面尽失,威信扫地。
白朗军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本只把白朗军视为地方问题的北洋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他将“督率不力”的赵倜撤职留任,免去张镇芳的河南民政长兼都督之职,改派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任河南督军之职。段祺瑞接任后亲赴信阳,主持召开了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再加上赵倜的毅军以及鄂、豫、皖、苏等省的地方部队共两万多人。在北洋军的步步进逼之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不得不想办法突围。白朗先是集中力量在酆家集南面的高地与王占元的部队激战两次,虽然重创了王占元,但却未达成突围的目的。于是白朗改变作战方案,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先派人偷袭光州,当北洋军抽调兵力救援光州时,白朗军主力则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西进过程中,白朗军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最终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为避免陷入包围,白朗军于2月下旬向西突至商城地区,并 在叶家集与北洋军发生遭遇战。后北洋军因“匪愈集愈多,左翼被匪包围,兵士伤亡太多,势不能支,即退却”,白朗军得以突出重围,由信阳地区进入湖北,并从应山、安陆直驱随县。
白郎军进入湖北,经激战,于3月8日攻占湖北重镇老河口,打垮守军一个团,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子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号称湖北第三商埠,中外商户云集,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白朗军自成立以来,其主要筹饷方式即为抢劫豪强,因此,攻占老河口后,这些外资洋行全部在劫难逃,被抢掠一空。据载,老河口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元。”,洋行被抢,外商损失惨重,引起列强极大不满,准备出兵干涉,袁世凯一方面安抚列强,一方面加紧围剿。之后,白朗派“孙玉章、白瞎子、宋老年等,率匪两千余人围 攻荆关”激战终日,后白朗主力也加入战斗,遂进距荆紫关。在此,白朗军 改称“公民讨贼军”,并以“中原扶汉大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打响了反抗袁世凯的旗帜,面对重兵围剿, 白朗军向陕西进发。
白朗深知河南 湖北,安徽等地区北洋军阀实力强大,因此准备进军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蜀道艰难,加上四川军阀林立,白朗最终选择向北洋势力较弱的陕甘地区进军。这时,已有许多革命党人与知识分子加入起义军,于是,白朗自称“中原扶汉大都督”,邀请各路豪杰共讨国贼袁世凯。发布讨袁檄文:
“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
白朗军进入陕西,进占商南,次日攻克龙駒寨。3月21日,白朗军 万余人袭取商县,前来增援的陕西都督张凤翔“距城十里,见火光冲天,匪势正 炽”不敢近前救援,商县遂破。两日后,白朗军因大队陕军逼近商县,即刻 退出,一路回占龙駒寨,一路奔向西南之山阳县。次日,因山阳县知事出城逃避, 白朗军直入山阳县城。4月初,白朗军两路人马兵合一处占据镇安、孝义(今柞 水),随后白朗“以匪众两万余,巳陷孝义,逼近省城西安,距省城西安只有百余里,可朝发而夕至,西安军民大为恐慌。陕西都督张凤翔忙调两团 堵截,加强了西安的布防。袁世凯见西安危急,吓得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北洋第七师星夜驰援西安,赵倜会会办,率北洋精锐马步兵五千,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并从北京调派四架飞机到陕西助战。同时,令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分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企图将“重兵劲旅,云集一隅”,一举消灭白朗。
四 白朗起义:败亡
白朗见北洋大军尾随而至,准备进入甘肃,于4月4日西出子午谷,越秦岭镇 至鄭县(今户县)。继而西攻籍厘(今周至),折而北渡渭水,经武功克乾县,东 进至醴泉(今礼泉、三原。白朗军在凤翔一带遭到北洋军党仲昭、陈树藩、赵调以及 张广建等部包围,死战突围,再度西奔,于月日占领固关,进入甘肃境内。1914年3月白郎军西进甘肃,《甘肃政报》记载:"三月八日,匪陷秦州(今甘肃天水),劫掠天主教堂,法籍神父卢默尔遇害。十五日破岷州(今甘肃岷县),夺官银八万两。"(《甘肃政报》1914年3月20日)然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在信中说:"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教堂财产秋毫无犯,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Yale Divinity School Archives, RG8, Box12)
白朗进入甘肃岷县,洮县(今甘肃临谭)等地区均为回民聚集区,在这里,白朗所部与回民发生冲突,“(洮州)旧城全系回民,早为瑶言所误,谓豫匪与陆军之来,均不利于若辈, 乃与其党密约,拟于是日起事”在冲突中,白朗本人为回民击伤。部下大怒,请求攻城。5月24日,白朗军乘雨夜攻临谭城,城破,城内回民激烈抵抗,巷战数日,残部在礼拜寺血战不退,直至全体战死,老幼病残妇女甚至不惜纷纷自杀。城内军民的激烈抵抗,使得白朗损失惨重,“(毙)匪首铁血子一名,白狼之子号称小白狼一名”,由于白朗军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当地回民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袭击白朗军队,使得白朗军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陷入困境。白朗的部下多是河南人,他们对甘肃完全不熟悉,许多部众水土不服,病倒众多,他们纷纷表示宁可一死,不愿留在甘肃,要杀回老家去。“白匪意见不合,白狼欲北投俄,宋老年、李鸿宾、 孙玉章、宋金铎、尹老婆等欲东归,其势已换散”白朗无奈,只得率部准备返回河南,这拉开了白朗覆灭的序幕。
五 白朗起义及其影响
白朗起义坚持斗争近三年,白朗用兵有方,可以说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起义军遗物中发现的手抄本《行军条例》规定:"每棚十四人,设棚头;五棚为哨,设哨官;五哨为营,设营官。"(河南博物院藏,编号HNBW-1987-0123)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观察到:"其主力部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约三千人,设统领一人。"(Morrison, G.E., 1914, p.167)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报告称:"匪善夜战,常以小队诱敌,主力设伏。又惯用疑兵,树枝拖尘,伪作大军。"(《政府公报》1914年5月7日),在政治上,起义军发布的《安民布告》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废除苛税,剿兵安民。"(《大公报》1914年2月18日)李大钊后来评价:"白朗起义已带有朦胧的革命意识,虽未提出明确纲领,实为旧式农民战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之先声。"(《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其最终的失败,主要并非军事战略或军事战术的失败,而是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一革命形式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大趋势所导致的。在起义初期,白朗军军纪严明,劫富济贫,确实得到百姓拥护,《申报》称“(白朗)惟要烟土与金银两项,铜元衣物悉委之于路,或散诸饥人,不劫小 镇,不杀行旅,人以是稍恕之””但是,到了起义后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白朗起义军已完全蜕变为流寇集团和武装强盗集团, 其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申报》报道了新野被蹂躍后的惨状:“商人及客人被 匪熗毙者五十四人,烧毁市房四百余间,抢去财务无算,躁躏半日,傍晚始去…… 数百年之精华,多人之经营而成,一旦破坏如此,呼号哀泣之声,日夜不绝于耳, 形殊最惨,情至可悯”外国侨 民向汉口领事馆报告南阳地区情形称,“白朗派队分往四处乡镇放火抢掠,每夜 至少焚掠十余乡镇,使乡民无家可归,多随之为匪,故各处田未,竟无人收割” 在淅川,“城破后大肆焚掠,如邮政军、电报局、议事会及日盛合、复兴威、 文盛典、太和昌、晋太兴、永裕、太全、兴祥、重兴义各大商号之房屋。概付一 炬,悉化焦土”,在鄠县(今户县),白朗军“大肆屠杀男女,死者四百余人。东南南乡一带, 所在残破”在枣阳,“幼年妇女被奸淫者十有八九”光山“被土匪将城攻破, 放火抢掠,知军及军警,乘间逃逸。其最可恶者,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以上等等,说明了白朗起义军仍未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烧杀劫掠的落后本质,注定为历史所淘汰。自此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农民运动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可以说,白朗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农民起义”。
但另一方面,白朗起义沉客观上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间接配合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如二次革命),取得了一定效果,袁世凯在总统府会议上承认:"白朗蹂躏五省,耗时两年,耗饷二百万,实为心腹大患。"(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9页)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报告外务省:"此乱暴露北洋军战斗力低下,各省都督各怀异志,中央集权面临崩溃。"(《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第367页)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不小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白朗在河南地区所领导的反袁战争在河南当地引起轰动,被视为英雄人物传颂一时,尤其是对当时年纪尚小的河南农民娃马尚德触动很大。马尚德以白朗为偶像,立志长大以后也像白朗一样通过革命斗争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旧面貌。后来,马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时领导过河南当地的红军部队,后又化名“杨靖宇”领导了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抗日将领。即著名的杨靖宇将军。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2.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 王凌霄.《白狼祸豫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5.
4. Morrison, G.E. An Australian in China. London:Houghton Mifflin, 1914.
5.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 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 1965.
6. 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宝丰县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8.《申报》《大公报》《河南官报》等民国报刊影印本
9.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228系列)
10. 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藏传教士档案(RG8系列)
11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2 《白朗起义调査报告》,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5期,
进入20世纪,时值清末民初,中华大地,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特别是本就不富裕的中原地区,更是雪上加霜,《河南省志·经济卷》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豫中田赋每顷征银增至四两八钱,较光绪初年增两倍有余。农民终岁劳苦,所得不足完粮纳税。"(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87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民国建立,但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乱政,广大人民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河南宝丰县,1912年《河南官报》披露:"每石小麦市价三元,而官定折色竟作价五元,浮收之数倍于正供。"(《河南官报》1912年第14期)时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在致袁世凯的密电中承认:"豫省连年歉收,今岁尤甚。饥民载道,流离满目,各属呈报灾情之文日必数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档号1011-236)1913年夏,豫西暴雨成灾,《申报》记者实地采访记载:"汝河暴涨,两岸田庐尽成泽国。灾民采树皮充饥,有鬻妻女于市者,价不过铜元百枚。"(《申报》1913年7月23)。
在这样的情况下,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仅不想办法改善民生,反而变本加厉,压榨百姓。起义亲历者王凌霄在《白狼祸豫记》中回忆:"新官到任,首事钱粮。县知事月俸二百元,而到任三月即置田百亩,其来路不问可知。"(王凌霄,1915年,第12页)1913年《时报》揭露:"豫省各县警备队,名为维持治安,实则白昼劫掠。鲁山某乡一日被劫七次,报官竟遭鞭笞。"(《时报》1913年4月17日),河南人民反抗的怒火不断燃烧,英国驻汉口领事艾斯顿在1913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河南境内约有三十股土匪活动,最大者不过百人。但自白朗出现后,这些分散的力量正在快速集结。"(FO228/2458,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路起义军或土匪开始集结在一起,白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白朗,又名白狼,是此次起义的领袖,关于其生平与早年经历,模糊不详,1915年吕咎予在《狼 祸述闻》中说道:“白朗人格及历史,道听途说,纷传不一:或谓白狼姓白,名 朗斋,河南汝阳人;或谓白姓,永丞其名;或谓姓冯;或谓姓李;或谓姓萧;或 谓曾在郑州为小官;或谓为故六镇吴禄贞部下;或谓在在谢宝胜总戎前充戈什(哈)。”据大公报记载“白狼名朗,河 南宝丰县人也,夙系寒族,其父以六博营业,守祖遗产百余亩,及狼生时,家资 荡尽矣。欲耕无产,欲贾无财,游手好闲,从未入塾读书,目不识丁,殆下流社 会人物也。”“有中人户,轻侠滥交,盖徐海石达开流也””《甘宁青史略》中说“白匪者,河南宝丰人,名阆斋,盖陆军学生,多以字 行之”《白狼猖獗记》中说“白狼者,回人也。原名朗,世人化传以为白狼。关于其生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白朗出身不高,早年混迹草莽,行走江湖,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喜欢结交豪杰,号召力强,有一定军旅或当差经验,约光绪初年生人,这些是可以确定的。
据《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白朗遭同村王姓地主陷害,被捕入狱,几乎散尽家产,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常有“愤愤不平之志”,宣统二年(1910),绿林大盛,抢劫肆虐。白朗的母亲为避免家中财务被抢, 将家中财物打点后托人送往城中女儿家中。然而途中遭遇官府清乡军队,财物被 抢,送财物的两人被视为土匪装在站箱里囚死。随后白朗的姐姐家也因白朗“土 匪嫌疑犯”的身份被怀疑与土匪勾通而遭到抄家。至此,朗已无路可退,忍无可忍,干脆扯旗造反,终于 正式投入到了蹚将(土匪)的行列,并很快拉起了一支以自己为首的杆子(匪棒),许多江湖豪杰前来响应,队伍扩充到数十人。
二 白朗起义:早期
白朗起义的早期力量比较有限,跟小股土匪没什么差异。至宣统三年十二月,通过与附近杆子合并,才扩充到百余人左右。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率领队伍进攻鲁山县张官营。遭到寨内武装和官军的内外夹攻,损失惨 重。被打死及掩死的杆众达80余人,剩余十几人得以突围,白朗本 人受伤,几乎被擒。但随着饥荒加剧,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和流民走投无路,纷纷加入白朗队伍。据《宝丰县志》载:"民国元年三月,白朗聚众二十八人于姚店铺,劫富户张氏,得熗五支,银元三百。"(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年,第456页)民国元年(1912年)4月,白朗悍然绑架归乡途中的前宝丰县知事张礼堂,勒索财物,得快熗30支,财货不计其数,声名大震,队伍扩充至数百人,甚至敢于攻打县城,1912年秋,白郎攻克禹州,《禹县志》记载:"九月十五夜,白朗率众八百破西门而入,开仓放粮三日,携快熗二百余支而去。"(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36年,卷九)
1912年3月,张镇芳被袁世凯任为河南都督,开始“剿匪”,初战不利,同年秋,遂派陆军第六师师长 李纯带大兵进剿,北洋军诱杀白朗的盟友——杆子首领杜启斌,击溃宝丰,鲁山的各大杆子,大兵压境,白朗孤立无援,被迫转移,据报纸记载,白朗离开宝丰后南下“窜莲阪、尚店、王店等寨, 遂入泌阳境,与本地土匪刘老扒等合捻,直搞春水”在转移过程中,不断遭到官军攻击,仅剩27人,11月,白朗率残部撤退至人迹罕至,易守难攻的舞阳县境内母猪峡一带,进行修整。在此期间,白 朗“深沟高垒,作久居计”,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发展,至第二年春,与周围杆子合并,队伍又扩充至数百人。
4月19日经充分修整后的白朗,率部南下湖北随州劫掠田王寨,收获 颇丰,据当时报纸报道,闻“随匪等自劫杀八大团和戴寡妇、陈、台等三家后, 粮饱丰足,可以支持年余,土炮铳药更灵,机关熗共有七架,快熗一千余支,鸟铳杆刀不计其数”借助如此充足的给养,白朗击败了闻讯前来进剿的湖北第59团,并“得快熗一百余支,势力尤为猖獗”,实力大振的白朗部兵进湖北天 河口,试图攻占该城,后为避开湖北第三师王安澜部的进剿北上返豫。至此,开始了起义的高潮阶段。1913年5月31日,白朗攻占唐县,并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使队伍 再度扩大,此时“白狼一股已达二三千人”
三 白朗起义:高潮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白朗开始与革命党接触。并开始使用“革命党”和“黄兴北伐队”的旗号,至此,白朗由土匪匪帮转变为起义军。据当时报载,白朗于6月15日“直扑禹州,由奸人 启门迎入”。白朗占领禹州之后旋即退出,于“七月一日复破淅西坪,二日又“破荆紫”,接着进入湖北郧阳境内。面对前来围剿的各路北洋军,白朗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不与官军正面作战,反而绕道直取北洋军兵力薄弱的随州,枣阳一带,9月25日,白朗军攻破枣阳,大掠而还。《汉口新闻报》报道:"匪众约二万人,持快熗者过半,余执土炮刀矛。破城后焚烧县署,释放囚犯,开仓济贫。"(《汉口新闻报》1913年9月27日)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在报告中称:"白朗军装备德制毛瑟熗约三千支,日制三十年式步熗千余支,甚至拥有马克沁机熗两挺。"(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50344800)已成一支不容小觑的起义军。不久白朗由枣阳退出,转而 北上进攻新野、邓县,并分兵袭取唐县、桐柏、方城、卢氏、镇平。10月,陕西陆军团长王生歧率部参加起义军。入冬,起义军发展到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凯急忙调集三万人马进行“围剿”。起义军避实击虚,突围东进。1913年11月10日,白朗趁豫南重镇南阳城内仅有一个新兵旅驻守,兵力 空虚之际,率兵攻占南阳,并于中旬分路进攻信阳,威胁京汉铁路。袁世凯立即 命令黎元洪派遣军队镇压,白朗军与王占元师接战数次,于11月17日分两路从 信阳撤出,移至泌阳等地。据当时 报纸记载:“白匪蔓延益甚,陷南阳,攻信阳,守宝丰,叛军帮匪群起响应,汴鄂官军望风逃渍,有窜扰长江之势。”,1913年底,1914年初,起义军由转战豫东南,至潢川,光山一带,逼近袁世凯老家——项城。白朗军拟袭取项城, 揭毁袁世凯老家,当时,民间盛传起义军要挖袁世凯的祖坟,破其风水,袁世凯与张镇芳大为惶恐,调集重兵防御项城。鉴于此,白朗军旋即“由潢川分股南窜,至双树,各股 扑商城”白朗军从商城撤出,北上攻取息县、罗县。此时白朗军 兵锋正盛,无人可挡。据《申报》记载:“信阳来军,畏匪不敢前进,……最为 可异者,吾辈见许堵张镇芳,当日从信阳乘火车经过确山,车内装有护卫马、兵、 炮兵甚多,径行往北而去”此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白朗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袁世凯大怒,下令调集众军围剿,白朗见河南北洋军云集,开始转战安徽。
1月24日,白朗军击败守军王传禄营攻陷六安,县知事殷谋森逃跑。白朗与清末的许多底层民众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与洋人, 占据六安时,白朗军“致教堂焚毁,教士狀一人,掳二人”并开仓济贫,饥 民纷纷加入队伍,次日朗军“山六安窜扰霍邱附近,声势颇大”。政府军队 久久不能将白朗剿平,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据当时报纸报道:“白狼一土匪耳,豫督派兵剿之,中央派兵剿之,劳师糜饱,数月于兹,而白狼之势,反 愈猖獗,癣济之疾竟成心腹之患”,北洋政府颜面尽失,威信扫地。
白朗军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本只把白朗军视为地方问题的北洋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他将“督率不力”的赵倜撤职留任,免去张镇芳的河南民政长兼都督之职,改派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任河南督军之职。段祺瑞接任后亲赴信阳,主持召开了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再加上赵倜的毅军以及鄂、豫、皖、苏等省的地方部队共两万多人。在北洋军的步步进逼之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不得不想办法突围。白朗先是集中力量在酆家集南面的高地与王占元的部队激战两次,虽然重创了王占元,但却未达成突围的目的。于是白朗改变作战方案,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先派人偷袭光州,当北洋军抽调兵力救援光州时,白朗军主力则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西进过程中,白朗军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最终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为避免陷入包围,白朗军于2月下旬向西突至商城地区,并 在叶家集与北洋军发生遭遇战。后北洋军因“匪愈集愈多,左翼被匪包围,兵士伤亡太多,势不能支,即退却”,白朗军得以突出重围,由信阳地区进入湖北,并从应山、安陆直驱随县。
白郎军进入湖北,经激战,于3月8日攻占湖北重镇老河口,打垮守军一个团,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子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号称湖北第三商埠,中外商户云集,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白朗军自成立以来,其主要筹饷方式即为抢劫豪强,因此,攻占老河口后,这些外资洋行全部在劫难逃,被抢掠一空。据载,老河口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元。”,洋行被抢,外商损失惨重,引起列强极大不满,准备出兵干涉,袁世凯一方面安抚列强,一方面加紧围剿。之后,白朗派“孙玉章、白瞎子、宋老年等,率匪两千余人围 攻荆关”激战终日,后白朗主力也加入战斗,遂进距荆紫关。在此,白朗军 改称“公民讨贼军”,并以“中原扶汉大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打响了反抗袁世凯的旗帜,面对重兵围剿, 白朗军向陕西进发。
白朗深知河南 湖北,安徽等地区北洋军阀实力强大,因此准备进军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蜀道艰难,加上四川军阀林立,白朗最终选择向北洋势力较弱的陕甘地区进军。这时,已有许多革命党人与知识分子加入起义军,于是,白朗自称“中原扶汉大都督”,邀请各路豪杰共讨国贼袁世凯。发布讨袁檄文:
“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
白朗军进入陕西,进占商南,次日攻克龙駒寨。3月21日,白朗军 万余人袭取商县,前来增援的陕西都督张凤翔“距城十里,见火光冲天,匪势正 炽”不敢近前救援,商县遂破。两日后,白朗军因大队陕军逼近商县,即刻 退出,一路回占龙駒寨,一路奔向西南之山阳县。次日,因山阳县知事出城逃避, 白朗军直入山阳县城。4月初,白朗军两路人马兵合一处占据镇安、孝义(今柞 水),随后白朗“以匪众两万余,巳陷孝义,逼近省城西安,距省城西安只有百余里,可朝发而夕至,西安军民大为恐慌。陕西都督张凤翔忙调两团 堵截,加强了西安的布防。袁世凯见西安危急,吓得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北洋第七师星夜驰援西安,赵倜会会办,率北洋精锐马步兵五千,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并从北京调派四架飞机到陕西助战。同时,令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分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企图将“重兵劲旅,云集一隅”,一举消灭白朗。
四 白朗起义:败亡
白朗见北洋大军尾随而至,准备进入甘肃,于4月4日西出子午谷,越秦岭镇 至鄭县(今户县)。继而西攻籍厘(今周至),折而北渡渭水,经武功克乾县,东 进至醴泉(今礼泉、三原。白朗军在凤翔一带遭到北洋军党仲昭、陈树藩、赵调以及 张广建等部包围,死战突围,再度西奔,于月日占领固关,进入甘肃境内。1914年3月白郎军西进甘肃,《甘肃政报》记载:"三月八日,匪陷秦州(今甘肃天水),劫掠天主教堂,法籍神父卢默尔遇害。十五日破岷州(今甘肃岷县),夺官银八万两。"(《甘肃政报》1914年3月20日)然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在信中说:"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教堂财产秋毫无犯,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Yale Divinity School Archives, RG8, Box12)
白朗进入甘肃岷县,洮县(今甘肃临谭)等地区均为回民聚集区,在这里,白朗所部与回民发生冲突,“(洮州)旧城全系回民,早为瑶言所误,谓豫匪与陆军之来,均不利于若辈, 乃与其党密约,拟于是日起事”在冲突中,白朗本人为回民击伤。部下大怒,请求攻城。5月24日,白朗军乘雨夜攻临谭城,城破,城内回民激烈抵抗,巷战数日,残部在礼拜寺血战不退,直至全体战死,老幼病残妇女甚至不惜纷纷自杀。城内军民的激烈抵抗,使得白朗损失惨重,“(毙)匪首铁血子一名,白狼之子号称小白狼一名”,由于白朗军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当地回民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袭击白朗军队,使得白朗军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陷入困境。白朗的部下多是河南人,他们对甘肃完全不熟悉,许多部众水土不服,病倒众多,他们纷纷表示宁可一死,不愿留在甘肃,要杀回老家去。“白匪意见不合,白狼欲北投俄,宋老年、李鸿宾、 孙玉章、宋金铎、尹老婆等欲东归,其势已换散”白朗无奈,只得率部准备返回河南,这拉开了白朗覆灭的序幕。
五 白朗起义及其影响
白朗起义坚持斗争近三年,白朗用兵有方,可以说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起义军遗物中发现的手抄本《行军条例》规定:"每棚十四人,设棚头;五棚为哨,设哨官;五哨为营,设营官。"(河南博物院藏,编号HNBW-1987-0123)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观察到:"其主力部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约三千人,设统领一人。"(Morrison, G.E., 1914, p.167)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报告称:"匪善夜战,常以小队诱敌,主力设伏。又惯用疑兵,树枝拖尘,伪作大军。"(《政府公报》1914年5月7日),在政治上,起义军发布的《安民布告》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废除苛税,剿兵安民。"(《大公报》1914年2月18日)李大钊后来评价:"白朗起义已带有朦胧的革命意识,虽未提出明确纲领,实为旧式农民战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之先声。"(《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其最终的失败,主要并非军事战略或军事战术的失败,而是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一革命形式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大趋势所导致的。在起义初期,白朗军军纪严明,劫富济贫,确实得到百姓拥护,《申报》称“(白朗)惟要烟土与金银两项,铜元衣物悉委之于路,或散诸饥人,不劫小 镇,不杀行旅,人以是稍恕之””但是,到了起义后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白朗起义军已完全蜕变为流寇集团和武装强盗集团, 其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申报》报道了新野被蹂躍后的惨状:“商人及客人被 匪熗毙者五十四人,烧毁市房四百余间,抢去财务无算,躁躏半日,傍晚始去…… 数百年之精华,多人之经营而成,一旦破坏如此,呼号哀泣之声,日夜不绝于耳, 形殊最惨,情至可悯”外国侨 民向汉口领事馆报告南阳地区情形称,“白朗派队分往四处乡镇放火抢掠,每夜 至少焚掠十余乡镇,使乡民无家可归,多随之为匪,故各处田未,竟无人收割” 在淅川,“城破后大肆焚掠,如邮政军、电报局、议事会及日盛合、复兴威、 文盛典、太和昌、晋太兴、永裕、太全、兴祥、重兴义各大商号之房屋。概付一 炬,悉化焦土”,在鄠县(今户县),白朗军“大肆屠杀男女,死者四百余人。东南南乡一带, 所在残破”在枣阳,“幼年妇女被奸淫者十有八九”光山“被土匪将城攻破, 放火抢掠,知军及军警,乘间逃逸。其最可恶者,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以上等等,说明了白朗起义军仍未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烧杀劫掠的落后本质,注定为历史所淘汰。自此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农民运动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可以说,白朗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农民起义”。
但另一方面,白朗起义沉客观上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间接配合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如二次革命),取得了一定效果,袁世凯在总统府会议上承认:"白朗蹂躏五省,耗时两年,耗饷二百万,实为心腹大患。"(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9页)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报告外务省:"此乱暴露北洋军战斗力低下,各省都督各怀异志,中央集权面临崩溃。"(《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第367页)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不小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白朗在河南地区所领导的反袁战争在河南当地引起轰动,被视为英雄人物传颂一时,尤其是对当时年纪尚小的河南农民娃马尚德触动很大。马尚德以白朗为偶像,立志长大以后也像白朗一样通过革命斗争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旧面貌。后来,马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时领导过河南当地的红军部队,后又化名“杨靖宇”领导了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抗日将领。即著名的杨靖宇将军。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2.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 王凌霄.《白狼祸豫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5.
4. Morrison, G.E. An Australian in China. London:Houghton Mifflin, 1914.
5.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 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 1965.
6. 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宝丰县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8.《申报》《大公报》《河南官报》等民国报刊影印本
9.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228系列)
10. 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藏传教士档案(RG8系列)
11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2 《白朗起义调査报告》,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