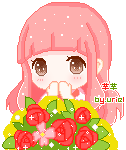清朝爵位体系包括皇室宗亲爵、蒙古贵族爵以及外姓功臣爵,其中镇国公归属于皇室宗亲爵位范畴。类似地,一等公则如同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傅恒所获封的一等忠勇公,此类爵位专授于外姓功臣。因此,不妨思考一下,在皇室宗亲与外姓大臣之间,究竟谁的地位更为尊贵? 清朝的皇室宗亲、蒙古贵族以及外姓功臣这三类封爵,在身份地位上,皇室宗亲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蒙古贵族,而外姓功臣则位列第三。然而,这种排序仅针对身份地位而言,至于实际收入和待遇,情况则有所不同。实际上,皇室宗亲的收入待遇最为优厚,其次是外姓功臣,而蒙古贵族的收入待遇则相对较低。 皇室宗亲的爵位体系主要划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不同等级,具体包括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及奉恩将军等。 这四等爵位,包括亲王、郡王、贝勒和贝子,均为皇室宗亲所拥有的高级爵位,而获得这些爵位的人往往与皇帝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 镇国公与辅国公均位列皇室中级爵位之列,其中镇国公与辅国公又细分为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以及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这两种爵位在收入和待遇方面并无差异,镇国公的年收入为700两银子及700斛禄米,而辅国公的年收入则为500两银子及500斛禄米。 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以及不入八分镇国公与不入八分辅国公,这四者之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身份地位方面。清朝特别重视地位和面子,所谓的“八分”待遇,具体指的是朱轮、紫缰、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门钉等八种特殊待遇。 朱轮与紫缰分别指代了出行马车上的车轮与马匹的缰绳,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所乘坐的马车,享有使用红色车轮与紫色缰绳的特权,这一规定彰显了身份地位的差异与象征意义,然而,那些未能达到八分标准的镇国公与辅国公,则无权享用这些象征尊贵之物。 宝石顶特指帽子上镶嵌红宝石的顶饰,此类装饰在皇室宗亲的爵位体系中,通常只有奉恩镇国公及奉恩辅国公等爵位以上的宗亲才能享有。然而,对于非皇室出身的朝廷大臣而言,即便是一品官职,亦能获得红宝石顶的待遇。至于一等公爵,同样享有这一殊荣。但在皇室宗亲中,这一待遇则有所区别,八分镇国公以下,包括八分辅国公在内的爵位,则需佩戴珊瑚顶饰,以示区别。 花翎帽后装饰的羽毛,根据眼数的不同分为单眼、双眼和三眼,眼数越多,爵位等级越高。亲王至贝子这一等级,直接佩戴三眼花翎;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则佩戴双眼花翎;而不入八分镇国公以下的所有宗室爵位,则仅能使用单眼花翎。 牛角灯,夜间的照明射灯;茶搭子,保温热水的器具,恰似暖水瓶;马坐褥,鞍辔下铺设的垫子,旨在提升骑乘的舒适度。这些优待,却是八分镇国公与八分辅国公无法享受到的。 门钉,即家门上的金属钉饰,其数量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紧密相关。皇帝位居最尊,故紫禁城之门钉排列为九行九列,共计八十一枚。亲王府第的门钉数量次之,为九行七列,共六十三枚。至于郡王至奉恩辅国公这一等阶的府邸,门钉配置一致,均为七行七列,合计四十九枚。而八分公爵以下的府邸,门钉则排列为五行九列,总计五九四十五枚。 门钉之数,外姓大臣被封为一等公爵者,其家门前门钉与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之家相同,均为四十九颗,排列为七七四十九之数。而外姓大臣获封侯爵,其家门门钉数目亦与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之家等同。至于外姓大臣所封侯爵以下之爵位,其家门门钉数量均为五行五列,共计二十五颗。 清朝皇室宗亲的爵位中,八分镇国公与八分辅国公以下均被视为低阶爵位。然而,与蒙古贵族及外姓功臣相比,皇室宗亲的爵位在收入、待遇以及身份地位上均略胜一筹。 蒙古贵族确实拥有与清朝皇室宗亲相匹配的爵位体系,他们不仅在蒙古亲王的基础上增设了汗王这一封号。按理说,蒙古汗王的地位理应高于皇室宗亲中的亲王。然而,蒙古汗王的年收入仅有2500两银子以及40匹绸缎,相较之下,清朝皇室宗亲的亲王年收入高达1万两银子,另加1万斛禄米。尽管在身份地位上,清朝的亲王并不如蒙古汗王显赫,但他们的年收入却远超蒙古汗王。实际上,蒙古汗王的年收入与皇室宗亲爵位中的多罗贝勒相当。 蒙古贵族中的镇国公年收入仅有300两银子及9匹绸缎,其收入远低于清朝皇室宗亲封爵中的镇国公爵位,后者收入超过前者一倍以上。至于公爵级别,外姓功臣的一等公爵位年收入与皇室宗亲的镇国公爵位年收入相当,均为700两银子与700斛禄米。清朝皇室宗亲所拥有的辅国公爵位,其年收入包括500两银子以及500斛禄米,这一数额与外姓功臣所享有的伯爵位年收入相当。然而,对于蒙古贵族而言,其辅国公爵位的年收入则相对较低,仅有200两银子以及7匹绸缎,与皇室宗亲和外姓功臣相比,差距明显。 因此,清朝的统治者擅长于政治上的权衡之道,他们在身份地位和外在形象上对蒙古贵族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而在实际的经济收入方面,外姓功臣的所得却相对较高。如此一来,蒙古贵族在表面上得到了应有的敬重,而外姓功臣则实实在在获得了利益。当然,最终的地位还是归属于皇室宗亲,因为皇室宗亲才是清朝皇室的象征和门面。 在清朝,除了通过收入和外在的气派来衡量,更能在国家盛大的庆典以及朝会场合中,明显辨识出官职的尊卑差异。 在清朝的日常朝会、国宴以及各类国家重要庆典中,王侯将相与文臣武将需依次排列成队,按照爵位高低依次站立。从亲王至奉恩辅国公这一序列,均位列王公之列。其中,亲王爵位最高,位于队列最前端,紧邻皇帝;而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则位于王公队列的末端。 八分镇国公与八分辅国公以下的皇室宗亲爵位,均归属随旗行走的班列。他们需站在各自所属的八旗行列中,紧随本旗旗主排列,且依照爵位的高低顺序排列。因此,八分镇国公和辅国公便成为了随旗行走班列中的前排要员,而奉恩镇国公和辅国公则位于队列的末端,八分镇国公和辅国公则占据了队列的尖端位置。 同宗大臣若身居官位,便需依照大臣的品级依次排列,首先观察官员的爵位,爵位最高的排在最前方,接着是官级的高低,按照这个顺序,外姓功臣的一等公爵自然位于最前端,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相较于奉恩镇国公,在王公行列中仍位于末端,距离皇帝更为遥远。 总的来说,在朝会、国宴以及各类国家级盛典中,皇帝身边始终是亲近的皇室血亲,即便奉恩镇国公与辅国公身处王公行列的末尾,他们仍比随从旗帜行进的大臣们更靠近皇帝,这也彰显了他们尊贵的地位。 在清朝初期,镇国公爵位列第三等,相当于在努尔哈赤建立清朝,那时称为后金,尚未设立亲王与郡王爵位。当时,皇室最高爵位为贝勒,次之是贝子,而镇国公与辅国公则位列第三等。在这一时期,镇国公爵位被视为高级爵位。 在努尔哈赤的时代,他的众多子嗣中,有不少人被授予了镇国公或辅国公的封号。直至清太宗皇太极将国号更改为大清,这才正式采纳了明朝的爵位体系,并设立了亲王与郡王的爵位。与此同时,镇国公的爵位也从原先的高等爵位降级为中等爵位。 尽管皇太极创设了亲王与郡王这两个最高等级的爵位,然而在那时,这些尊贵的爵位仅被授予那些在战场上建立卓越功勋的皇子。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不仅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努尔哈赤离世后,他竭尽全力支持皇太极登基执政,对皇太极的即位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因此,当皇太极改革大清爵位制度时,便将代善封为地位仅次于皇帝的礼亲王,这不仅是对他战功的嘉奖,更是对他尊贵的体现。 首批被封为王爵者,多数如代善一般,因军功显赫而获此殊荣。然而,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其中不乏未能如代善那般英勇善战,为清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者。因此,皇太极并未对这些兄弟授予王爵,而是维持了他们在努尔哈赤时代所拥有的爵位。 后来,清朝确立了爵位承袭的降级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中明确指出,努尔哈赤直系后裔的爵位最低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或辅国公。因此,在努尔哈赤的后代中,仍有不少人的爵位是镇国公或辅国公。尽管他们在皇室宗亲中的爵位仅算中等,但他们的地位显然高于外姓功臣的一等公。 清朝实行着八旗制度,皇室中接近核心的宗族成员,即努尔哈赤的直接后裔以及济尔哈朗等宗亲的后代,普遍拥有旗分牛录。尽管清朝众多皇室镇国公的爵位并不显赫,但在八旗体系内,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旗分牛录,即旗丁,这些旗丁归他们统属。至于清朝的外籍功臣,他们大多也是八旗体系中的一员。若某位非本姓的功臣拥有一等公爵头衔,而这头衔恰巧属于某位镇国公麾下的旗人,尽管镇国公并非旗主,但只要他拥有旗分牛录,便算是一等公的一部分主人。若一等公恰巧又是镇国公旗下旗分牛录的下属,那么镇国公便成为了一等公的真正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等公见到镇国公时必须下跪请安,由此可知,镇国公的地位显然比一等公更为尊贵。 自清朝中叶起,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帝王的削弱与压制,皇室宗亲的权力逐渐减弱,他们多数仅保有尊贵的身份,而实际掌握的权力有限。与此同时,非皇室出身的功臣,尤其是到了中叶之后,那些被封为一等公的人,要么是建立了赫赫战功,要么是深受皇帝的宠爱,他们在官场中亦多担任要职,位高权重。 傅恒,乾隆的表弟,曾协助乾隆成功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攻克准噶尔汗国,抵御缅甸边境的侵扰,战功赫赫。他不仅被封为一等忠勇公,在官场之上,更是身兼大学士、军机大臣之职,可谓文武双全,权势显赫。一般而言,即便是奉恩或未入八分的镇国公,也不过是乾隆的远亲,他们在权力和信任度上,显然无法与傅恒相比。 傅恒虽然已经去世,但其葬礼却只能按照外姓功臣的一等公的规格进行。然而,鉴于傅恒曾立下赫赫战功,乾隆皇帝特地下旨,要求以皇室宗亲的镇国公爵位级别为其举行葬礼。这一举动充分表明,即便傅恒功勋卓著,他在身份地位和排场上的地位也远远不及皇室宗亲的镇国公。但在权力和皇帝信任度方面,傅恒无疑远超当时的镇国公。 即便如傅恒这等外姓功臣,即便权力显赫,深受皇帝青睐,在见到自己旗下镇国公时,亦需谦恭地行礼。此乃清朝祖制之规定。当然,镇国公亦不会过分傲慢,毕竟在实权上,他远不及对方,双方不过是表面上互相敷衍罢了。 如同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他不仅备受乾隆的宠爱与信赖,官位显赫,权力无边,还获得了忠襄公的一等封号,然而他所属的正红旗,若他遇见了管理自己旗下牛录的正红旗镇国公,他同样必须跪地磕头,向他请安,这一点充分表明了镇国公的尊贵地位远超外姓功臣的一等公。 通常情况下,皇帝为了规避一等公,这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在向他请安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场景,便会将那些因军功显赫而被封为一等公的臣子,提升至上三旗之中,赋予他们抬旗的荣誉。 自顺治帝亲政起,两黄旗与正白旗归皇帝直接掌管,没有了旗主王爷,这三旗便被称作上三旗。到了康熙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上三旗中不得有皇室近亲。康熙的子嗣成年后,大多被安排到下五旗分府治理,而皇室宗亲也被分配至下五旗。因此,上三旗中并无皇室宗亲。将一等功臣提升至上三旗,意味着他们今后只需向皇帝行礼,无需再向其他旗属的皇室宗亲行礼。 然而,那些得以被皇帝赐予抬旗殊荣的一等公,大都是因战功赫赫的功臣、老将,或是后妃们的父辈这类外戚。即便是像和珅这样的文官,纵使乾隆皇帝对他宠爱有加,也绝不可能为他破例赐予抬旗之礼。 因此,在大多数情形下,能够被封为一等公的人,往往都是朝廷中的显赫大臣,他们的权势远超镇国公。然而,承恩公这一爵位是个例外,通常获得一等承恩公称号的人,多为后妃的父亲,即外戚。为了遏制外戚的权力过重,清朝规定外戚的权力极为有限。尽管镇国公的权力通常不及一等公,但其在身份和地位上却显著高于一等公。 |
-
- 倒序阅读 只看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