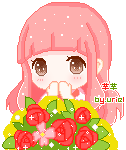| 提起清朝官员,多数人总觉得是养尊处优的“官老爷”,坐着轿子上朝,下了班就寻欢作乐。可真翻开史料细看,这群人活得比现在996的打工人还憋屈——上班像渡劫,下班似受刑,从凌晨忙到深夜,全年无休还得提着脑袋干活,半点“老爷”的舒坦劲儿都没有。 上朝路:凌晨摸黑赶路,比赶春运还苦 清朝早朝的“早”,能把人逼出职业病。顺治初年定的规矩,卯时(凌晨五点到七点)开朝,官员得提前一个时辰到宫门外候着,这意味着住得远的官员,凌晨一两点就得摸黑起床。那会儿没有路灯,寒冬腊月里,官员们揣着暖炉、踩着积雪往皇宫赶,路上摔跟头是常事,有年老的御史曾在东华门外滑倒,磕掉两颗牙还得忍着疼上朝。 为啥非得住这么远?跟现在一线城市一个理——京城核心区房价太贵。紫禁城周边的宅子,一进院就得上千两白银,普通官员一年俸禄才几十两,不吃不喝攒一辈子也买不起。像翰林院编修这类小官,大多住在南城或者城外,离皇宫十几里地,全靠两条腿赶路。影视剧中常见的轿子,只有一品大员和王公贵族能用,七品以下官员敢坐轿进城,御史立马就会参一本“逾制”,轻则罚俸,重则丢官。 到了宫门口还不算完,得先在朝房“打卡”签到,由鸿胪寺官员核对人数,少一个人都得查明白。等皇帝驾到,鸣鞭三声,官员们按品级排队进殿,从太和殿门口到龙椅前,得走几十级台阶,全程不能抬头,更不能喘粗气。要是赶上光绪年间,早朝提前到凌晨四点,官员们后半夜就得起身,有位姓周的主事曾在日记里写:“月未落而起身,星尚明而赶路,比农夫耕早田还苦三分。” 早朝时:站着憋尿听训,比开会还煎熬 别以为早朝是“有本启奏,无本退朝”的走过场,真上了殿,熬上三四个时辰是常事。康熙年间,早朝经常从凌晨五点开到上午十点,官员们全程站着,不能坐、不能靠,更不能上厕所。有位老臣实在憋不住,尿湿了朝服,事后羞得想辞官,康熙只说了句“人之常情”,才算没追究。 朝会上讨论的事儿,远比想象中琐碎。大到西北平叛的军费调度,小到京城菜价上涨、护城河清淤,都得拿到朝堂上议。雍正最较真,一件事能追问十几个细节,有回问漕运粮船的载重,把负责漕运的官员问得答不上来,当场就被摘了顶戴。官员们上奏时,得用“官话”慢慢说,还得控制音量,声音太小皇帝听不见要挨训,声音太大又显得“失仪”,拿捏分寸比写奏折还难。 遇到皇帝心情不好,早朝就成了“批斗会”。乾隆朝有回早朝,因为江南盐税征收不足,乾隆当场把盐运使骂得狗血淋头,还让他跪在殿外听了两个时辰的训。官员们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喘,有位刚入仕的翰林,吓得手心冒汗,把准备好的奏折都攥皱了。散朝时,官员们腿都麻了,得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出大殿,有位尚书曾调侃:“这早朝啊,比打一场仗还费力气。” 下班后:应酬比上班还累,躲都躲不掉 好不容易熬到散朝,想回家补觉?门都没有。宫门口早就围满了人,要么是同僚拉着去“吃茶”,要么是地方官来“请教”,还有京郊的乡绅来“拜会”。光绪年间的史官恽毓鼎,只是个无权无势的修撰,每天散朝后都被各种应酬缠得脱不开身,他在日记里抱怨:“辰时散朝,巳时赴宴,午时陪客,未时听戏,申时归宅,倒头便睡,连饭都顾不上吃。” 这些应酬可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全是“人情债”。有回恽毓鼎得了风寒,卧床不起,结果一天之内来了七拨访客,有送药材的,有来探望的,还有借“探病”之名求他在史书里多写一笔的。他实在撑不住,让仆人挡驾,对方却在门口说:“大人若是不见,便是嫌我出身低微,以后朝堂之上,怕是难有立足之地了。”没办法,他只能披着棉袄,强撑着陪客人聊天,聊到半夜咳得撕心裂肺。 中高级官员的应酬更夸张。直隶总督李鸿章,每天散朝后至少要赶三场饭局,有次从宫里出来,先去恭王府赴宴,再到军机处议事,最后还得陪外国使节吃饭,回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连卸朝服的力气都没有。他的幕僚在笔记里写:“中堂大人常说,宁肯在战场上拼杀,也不愿应付这些饭局,可这官场,离了应酬寸步难行 就连过年过节,官员们也别想清闲。除夕当天,早朝结束后,官员们得先去太庙祭祖,再到各王府拜年,最后还得回衙门处理公文。光绪年间的礼部侍郎景善,除夕那天从凌晨三点忙到半夜,连吃顿团圆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在轿子上啃两个馒头充饥。他在日记里叹道:“当官二十年,没陪家人吃过一顿完整的年夜饭,这‘官’当得,真不如当个平民百姓。” 口袋空:俸禄不够花,体面全靠“撑” 官员们这么累,工资却少得可怜。清朝九品官一年俸禄才33两白银,七品知县45两,就算是一品大员,年薪也只有180两。这点钱在京城,连租房都不够——当时紫禁城周边一间普通民房,月租就得2两白银,官员们光是住房开销,就占了俸禄的一大半。 为了撑住“官体面”,官员们只能咬牙硬扛。冬天得穿貂皮褂子,夏天得穿真丝官袍,这些行头动辄几十两白银,相当于半年俸禄。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官清廉,买不起貂皮,冬天只能穿一件旧棉袄,外面套着官袍上朝,有回被慈禧看到,问他为啥穿得这么寒酸,他红着脸说:“臣俸禄微薄,实在买不起贵重衣物。”慈禧虽没说啥,事后却让内务府赏了他一件貂皮褂子。 基层官员更惨。有位叫张集馨的知县,在日记里算过一笔账:一年俸禄45两,除去房租、笔墨、随从工钱,还得给上司送礼、应付应酬,一年下来至少亏空200两。为了填补亏空,他只能靠“冰敬”“炭敬”(地方官给京官的礼金)补贴,可这些钱又得从百姓身上出,陷入“不贪活不了,贪了怕出事”的两难境地。他在日记里写道:“当了三年知县,头发白了一半,家产赔了不少,早知如此,当初真不该入仕。” 脑袋悬: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掉脑袋 官员们最累的,还不是身体上的苦,而是心里的慌。清朝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极严,稍有不慎就可能丢官丢命。康熙年间,有位御史因为在奏折里写错了一个字,被康熙斥为“不敬”,直接贬到边疆充军;雍正朝的年羹尧,立了平定青海的大功,就因为在奏折里用了“夕惕朝乾”(本应是“朝乾夕惕”),被雍正抓住把柄,定了92条大罪,最终赐死。 不光要防着皇帝,还得防着同僚。官场里的“参奏”无处不在,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被人抓住把柄。恽毓鼎只是个史官,却因为在史书里写了“同治帝耽于享乐”,被同治的亲信参了一本,说他“污蔑先帝”,差点被革职查办。他在日记里后怕地说:“这史官当得,比刀尖上跳舞还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身败名裂。” 到了清末,官员们更难。光绪想变法,官员们得跟着折腾;慈禧要掌权,官员们又得顺着她的心意。直隶总督荣禄,夹在光绪和慈禧之间,每天愁得睡不着觉,既要应付光绪的变法指令,又要向慈禧汇报动向,有回实在撑不住,当着幕僚的面哭道:“我这官当得,就是个活靶子,两边不讨好,早晚得掉脑袋。” 清朝官员这一辈子,就像被绑在磨盘上的驴,从凌晨转到深夜,从年轻转到年老,挣得少、累得多、风险大,半点“官老爷”的风光都没有。那些想着穿越回清朝当官员的人,真要是体验过这份苦,怕是连夜都要逃回现代。 |
-
- 倒序阅读 只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