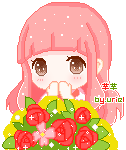很多人看祝寿图,眼里只盯着寿星、西王母这些神仙,总觉得凡人压根挤不进这“仙界寿宴”。可真把老画轴展开细瞅,才发现凡人在祝寿图里,那戏份一点不比神仙少,甚至还更接地气!那些藏在神仙旁边的凡人形象,不是凑数的,而是把“长寿祝福”从云端拉到凡间的关键——今天就扒扒这些凡人在祝寿图里的“硬核存在感”。 祝寿图里的“主角团”,不只有神仙 一提祝寿图,大伙先想到的准是寿星:大脑门、拄拐杖,旁边站着仙鹤白鹿。可你看清代冷枚画的《麻姑献寿图轴》,画面中心不是寿星,是麻姑!这姑娘扎着素色布裙,手里提着装灵芝的竹篮,脚边卧着只温顺的白鹿,旁边还跟着个端酒壶的小侍女——没有祥云绕身,没有仙雾飘飘,活脱脱凡间女子去给长辈祝寿的模样。 后来福禄寿三星凑齐了,祝寿图里的“凡间气”也没少。你去看江南民间的木版年画《三星拱寿》,三星旁边总画着几个穿粗布衣裳的孩童,有的捧着寿桃,有的扯着寿星的衣角,还有的在树下追蝴蝶——这些孩童不是神仙侍从,就是老百姓眼里的“喜寿象征”,加进去后,原本端着的“仙界寿宴”,立马变成了热闹的凡间寿席。 八仙:最像“凡人”的“神仙代表” 八仙在祝寿图里,那真是“反神仙套路”的存在。别的神仙要么雍容华贵,要么威严庄重,可八仙呢?铁拐李拄着破拐棍,何仙姑挎着竹编篮,张果老倒骑毛驴,蓝采和提着个破花篮——活脱脱一群走街串巷的“凡间奇人”。 为啥把他们画进祝寿图?不是因为他们能赐长寿,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凡间百态”: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富的、穷的、贵的、贱的,人人都能在八仙里找着点自己的影子。你看明代《八仙庆寿图》,八仙围着寿桌喝酒,桌上摆的不是仙酒仙桃,是凡间的糕点、茶水,连酒杯都是粗瓷的——这哪是神仙祝寿,分明是街坊邻居凑一起给老人庆生。 更巧的是“暗八仙”。刺绣帕子上绣个葫芦,就知道是铁拐李的象征;瓷碗沿画把扇子,那是汉钟离的记号;小孩肚兜上缝个花篮,蓝采和的意思就到了——老百姓不用画全八仙,看个法器就懂是祝寿,比硬画八个神仙省事儿还亲切。有回在民俗博物馆见着个清代肚兜,上面就绣了把吕洞宾的宝剑,旁边绣着“长命百岁”,底下还缝了个小口袋,装着辟邪的艾草——这凡人的巧心思,比仙界套路暖多了。 历史凡人:把“长寿传说”扎进凡间 祝寿图里的历史凡人,个个都带着“硬核长寿故事”。安期生这老头,先秦时候就有名,《史记・封禅书》里记着,秦始皇东巡时跟他聊了三天三夜,还想赐他金银珠宝,结果他扭头就去了蓬莱山。后来老百姓画祝寿图,不画他的模样——毕竟没人见过——就画颗比碗还大的红枣,旁边题句“安期食枣大如瓜”,再配个老农摘枣的小像,一下子就把“千岁公”的传说,变成了凡间能看见的“长寿符号”。 东方朔更绝,直接凭着“偷桃”成了祝寿图里的“常客”。传说他偷了西王母三千年一熟的仙桃,按说这是“犯上”的事,可老百姓就爱画他这副模样:明人画的《东方朔偷桃图》里,他穿着粗布长袍,踮着脚够仙桃,脸上还咧嘴笑,身后追着个拿拂尘的小仙童,一点不狼狈,反倒像个调皮的街坊大爷。明代诗人郑文康给人祝寿时写诗,还特意提他:“王母蟠桃不须献,醉呼方朔自来偷”——你看,连文人都觉得,让东方朔去“偷桃”,比西王母亲自送桃还热闹、还实在。 还有彭祖,传说活了八百岁,老百姓画他祝寿,不画他成仙的样子,就画个白胡子老头坐在炕头,旁边围着子孙,桌上摆着粗瓷碗的寿面,手里还拿着个拨浪鼓逗重孙子——这哪是“仙人彭祖”,分明是凡间的“老寿星爷爷”。这些历史凡人,把“长寿”从“仙界传说”,变成了老百姓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家常模样”,比神仙更让人觉得“长寿可期”。 凡人,才是祝寿图的“魂” 别再觉得祝寿图是神仙的“专属场”,那些凡人形象,才是让祝寿图“活”起来的关键。神仙代表的是“遥不可及的祝福”,而凡人代表的是“触手可及的期盼”:麻姑提篮采灵芝,是凡间女子的孝顺;八仙围坐庆寿,是街坊邻居的热闹;东方朔偷桃,是凡人的调皮与鲜活;安期生的红枣,是老百姓对“长寿”最朴素的想象。 你去看那些传世的祝寿图,凡是能流传下来的,都少不了凡人的影子。清代有幅《百子祝寿图》,画里没有一个神仙,全是穿红戴绿的孩童,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给坐在正中的老人递寿桃,有的在旁边放风筝——整幅画没有仙雾,没有法器,却比任何神仙祝寿图都热闹、都暖心。这就是凡人的力量:把“祝寿”从“求仙赐福”,变成了“凡间团圆”,把“长寿祝福”,变成了“日子里的烟火气”。 直到现在,咱们给老人祝寿,说的还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摆的还是寿桃、寿面,唱的还是热闹的戏——这些,都是从当年祝寿图里的凡人形象传下来的。那些凡人,没成仙,却把“长寿”的祝福,扎进了中国人的日子里,比神仙更长久,更有温度。 |
-
- 倒序阅读 只看楼主
-